
《失聲畫眉》(1990年,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出版)這部長篇小說,是「第四次自立晚報百萬小說徵文獎」(1990年)得主。作者凌煙,本名莊淑楨(1965-),嘉義縣東石鄉人。大量呈現女女愛慾的《失聲畫眉》是台灣同志文學史上第一部獲得重要文學獎肯定的作品(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於次年──1991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一名的肯定)。在文學獎仍然對台灣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的那個年代,《失》獲獎一事對於關心同志文學的人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失》得獎之前,同志題裁的作品就連發表都有顧忌了(寫作者和編輯台各自心中都有「小警總」),更別說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享受文學獎的光環。

《失》呈現了「民國七十五年左右,『大家樂』賭風襲捲台灣中下層社會最烈的時候」(季季語)。在南部走唱的某歌仔戲班為了滿足看客兼大家樂賭客的要求,開始在野台上表演脫衣舞。戲班成員雖然超時工作,卻仍有力氣、有需求跟班內班外的同性或異性發生關係。書中參與女同性戀的班內班外角色有好幾個,固然特別搶眼;但書中有些女性跟男性維持婚姻體制外的情慾,也值得注意。說《失》是同志小說並不誇張,但《失》的異性戀情節和同性戀情節是平行發展的,並不該將《失》簡化為「只描寫女同性戀」的作品。持平而論,《失》呈現了一夫一妻婚姻格律之外的各種「下流」(而非「中產」)情慾,事涉同異男女。書中角色是(被社會主流認定的)下流人,他們沉浸於下流的情愛色慾──她們並非有錢有閒,並不能奢求在咖啡廳一對一浪漫約會,也不可能找個舒服的飯店與情人過夜。她們不可能等到安身立命之後(等不到那一天的)再談戀愛。戲班內外,台上台下,都是不得已的違建。
1992年,江浪(鄭勝夫)將《失》改編導演為電影《失聲畫眉》,由陸一蟬等人演出。這部片不叫好也不叫座,常見的批評之一是此片呈現女性愛慾的手法粗糙。這部片成為一個被各界(含同志)冷落的尷尬資產(它是資產卻沒人緣)。但這部片在2012年──下片20年之後──重登新聞版面。LS TIME電影台在2012年2月25日播出電影《失聲畫眉》,片中出現女子間親吻舌吻特寫、同性戀暗示,被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違反「節目分級辦法」。 同志社團的嚴正抗議,認為NCC歧視同志的公然歧視 ;NCC回覆,表示並無歧視同志之意,純是因為電視台違反節目分級的標準而開罰。官方依法行事,民間因為疏忽法規而吃虧。但長久以來,在國內國外,官方(含軍警、學校)歧視或打壓同志的方式往往不是直接用「處罰同性戀之名」對同性戀開鍘,而總是有辦法迂迴地、利用看起來「完全不歧視,甚至不提及同性戀」的法規來找同志麻煩(如,1950年代的法令罰了妓女但沒罰男同性戀,但警方用罰妓女的條文來罰男同性戀)。但我在此暫時無意討論NCC的是非(另有場合),而想要點出電影版《失聲畫眉》復出江湖的意義:官方覺得它下流不堪,民間覺得它是可貴資產。但雙方的看法並不衝突,合而觀之正好就是這部片的全貌:下流不堪但可貴的資產。
這部片再怎麼背離了小說原著,卻也誤打誤撞點出了小說原著的要義:書中的人事物本來就是下流的、不堪的(我在此並無意將這兩個詞當作貶辭)。這部片看起來絕不清爽感淨,但小說原著本來就在陳述讓人(中產的讀者?)坐立不安的、不得已的齷齪感。
小說附錄的決審記錄就顯示了「同性戀值得被寫,但同性戀本身好苦」的態度。
「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著稱之處,其一是它是台灣第一個高額獎金文學獎(百萬),其二是它的評審過程波折多。這個獎從1982年開辦,辦了第四屆、歷經八年之後,在前三屆都從缺的情況下,才終於把獎頒給凌煙的作品。值得留意的是,文學獎評審們── 季季、姚一葦、李喬、施淑女(施淑)、葉石濤──全都注意到《失》中的女同性戀,而且大多給予肯定。季說,「我看過的小說中,(《失》是)描寫女同性戀者寫得最好的。」姚說,「這(《失》中世界)可以說是個畸形的世界,其中又以對女同性戀的描述稱得上是一絕。在我讀過的作品中,尚未看到任何作者寫女同性戀寫到這種層面,不管國內或國外的作品,這個層面是其他作者所沒有觸及過的……」言下之意,季和姚在1990年之前,也看了不少描寫女同性戀的小說(不知他們所說的國內作品是哪一些?)。
以上兩位的重點是,《失》在描寫女同性戀方面超越了其他寫女同性戀的小說。另外兩位評審則看重「歌仔戲團與同性戀」的因果關係。
施淑說,「這作品有其可貴處,如季季所提的歌仔戲團中的同性戀問題,那種由於演戲而產生的假鳳虛鸞的情境,歌仔戲團被摒除於台灣正統文化之外,使她們在情感生活上不得不走上那種道路……」李喬說,「前面提到的(其他評審先前提到的)女同性戀的層面,非常自然……這篇同性戀並非源於遺傳因素,也不失源於成長史的性倒錯,而是扭曲畸型的大環境所塑造出來的。」這兩位在讚賞《失》描繪同性戀的技藝時,不忘對「同性戀本身」(而不是描繪同性戀的「技藝」)抱憾。這種為同性戀感到遺憾的態度在當今仍然常見,在1990年當時更是幾乎理所當然了。我更留意的是,這兩位認為:歌仔戲團在台灣被邊緣化是因,假鳳虛鸞是果──如果歌仔戲團沒有這麼破落,就不致於孳生女同性戀。這種因果關係的說法應該會遭受不少讀者質疑,但我想指出:這種因果關係的說法剛好把歌仔戲團和女同性戀捆綁為「命運共同體」,形同聲明女同性戀是台灣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容忽視的,不能推稱是城市教壞台灣核心的鄉村,也不能諉過給外國。如果沒有描寫女同性戀,歌仔戲團的描寫就少了一塊重要拼圖。
長期關心同志小說(如,林懷民小說)的葉石濤則指出,「在這麼一個舊式封建社會中(指歌仔戲班),除了它本身有的問題之外,還發生了新社會引進的墮落問題,如為錢脫衣、賣命及同性戀等等。封建的舊道德和新倫常之間所引發的矛盾(指前述現象)……」葉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跟另外四位評審不同;他認為同性戀是「新社會、新倫常」帶來的,言下之意是,要不然台灣舊社會才不會有同性戀。他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偏離他閱讀林懷民的讀法:同性戀是西方社會帶來的,對於台灣來說是新鮮事。葉的說法經不起考驗──《失》並沒有描寫新社會或新倫常;脫衣舞和同性戀都是舊社會既有的成份,不能推托給舊社會之外的世界。但我的重點倒不是在計較葉的對錯,而是在於點出葉對於台灣舊社會的想像:葉想像的舊台灣是沒有色情的,沒有同性戀的,也就是說,被淨化過的。
從自立晚報文學獎決審團、《失》電影版團隊一直到NCC事件,都在協商一回事:「這麼下流的同性戀」和「這麼純良的台灣」怎麼能夠交織在一起。以2012年的後見之明,我認為有些事實該大方承認:台灣從古到今本來就有下流的一面不可否認;下流的人事物是歷史、經濟、人慾等等因素造成的結果,沒有必要加以道德批判;同志的歷史,和台灣的歷史一樣,本來就有許多讓人尷尬的陰暗面,但唯有呈認這些尷尬才可能增加歷史的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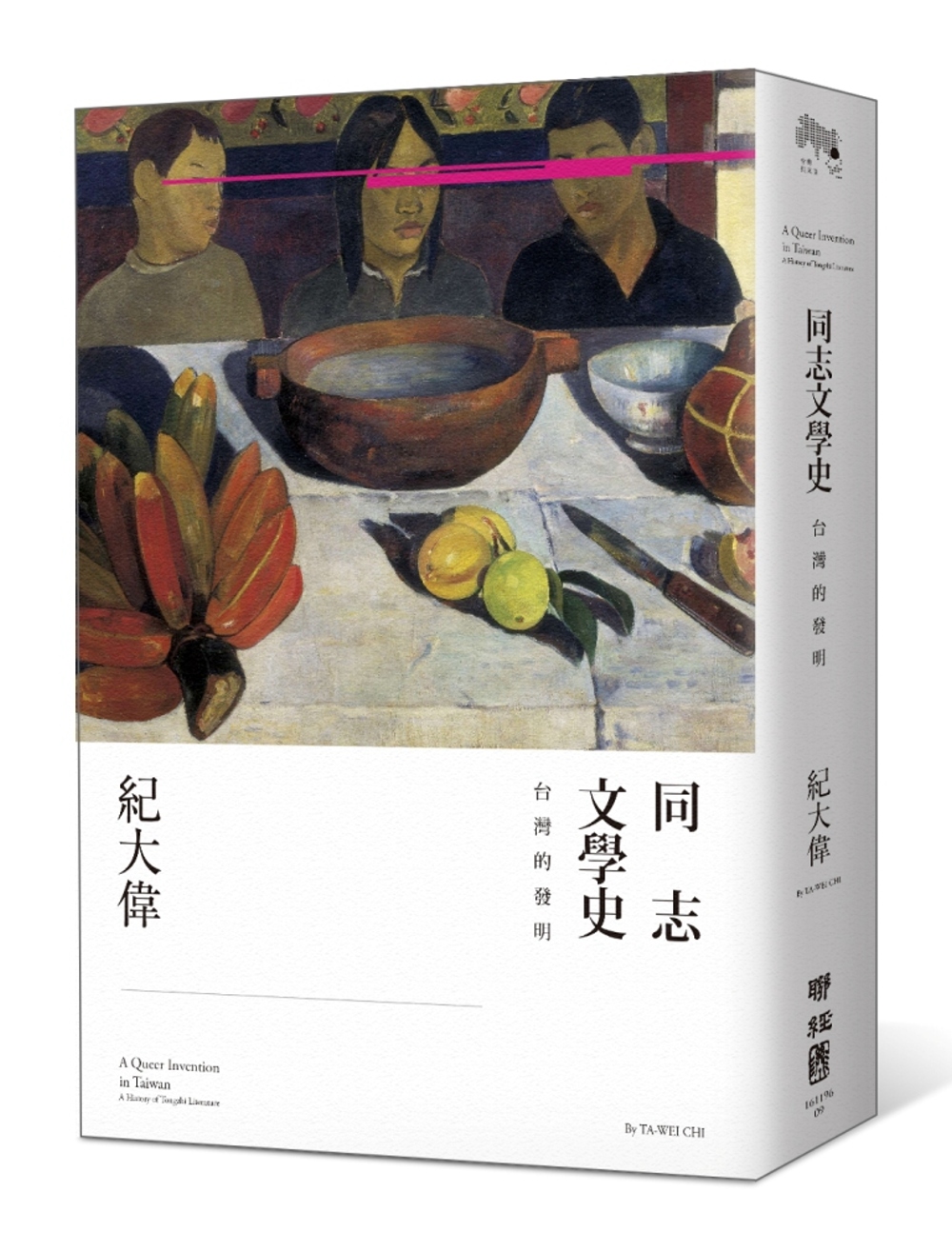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