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特輯
我喜歡從邊陲出發∣【紙上的秘密航道】總編輯線上短講_八旗文化_富察延賀
作者:富察延賀 / 2022-07-18 瀏覽次數(2468)
這個標題存在著無盡的誘惑和致命的風險。因為你一旦提及邊陲,心裡已經安置了一個中心。誰是邊陲,以及誰的邊陲?是一個永恆的辯證。而跳出由漢字編織而成的天朝中心知識體系的約束,從它眼中的邊陲出發會看到什麼?乃是一件非常充滿了樂趣和挑戰的工作。其結果自然是:邊陲成為中心,中心變成窪地。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絲綢之路一詞雖然是德國人的發明,但這四個漢字已經被今天的中國人詮釋為漢唐盛世意象。回到中古真實的歷史裡,我們不無錯愕地看到,中國(這個詞指的是它的地理和文化意義,既非民族,也不是政治實體)只不過是代工的世界工廠。大航海時代之前的國際貿易路線上,主宰者、定價權、通用貨幣、商業語言,都不是唐人,而是粟特人。長安城裡的胡商薩保,不過就是北京城內的外國商會。而粟特人,簡單粗暴的來比喻,大約就類似今天的美國人。如果當時的中國出現了閉關鎖國的政治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比如趙宋政權時代,那麼從絲綢之路運送到中國而來的技術、資金和意識形態就被契丹人和女真人所接管。森安孝夫的《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以紮實的史料和學術功力描述了這個現象;而這個現象其實是中國史的常態。森安孝夫筆下的唐帝國,因為異己而開放,因為野蠻才自由,其實與平野聰筆下的清帝國一樣,都以自己的獨特形式『混迷』了不同時代的『中國』(《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今天的我們之所以感受不到,不過是因為以漢字記載、以大一統為意識形態的史料中,混迷的一面被遮蔽和清洗掉了。
《中國窪地》
在草原游牧民和海洋貿易民族看來,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片邊陲窪地。它處在黃河中下遊的冲積平原上,高地民族從山西高原上俯瞰,對這種低窪的地貌一目了然(《中國窪地》)。漢高祖的白登山之圍或明英宗的土木堡之變都是從低地逆襲而失敗的案例。從粟特人和阿拉伯人的視角,他們主持的遠東國際貿易線的盡頭是揚州;一如從英國人和歐洲人的視角,他們主持的遠東國際貿易路線的盡頭是上海。
《木蘭與麒麟》
迷信漢字史料的人往往會忽略或忘記人民日報裡濃重的意識形態,但語言學家和考古學者對此頗有警覺,也無情犀利地點出某些事實。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大膽做出論證,無論是木蘭詩,還是李白和白居易,抑或十二生肖,甚至是政治制度,這些貌似很『中國』的東西,來源都指向波斯-伊朗文化。中古時代的西化和20世紀的西化並無本質不同,只是名稱有異,曰胡化。前者循著絲綢之路、騎著馬和駱駝而至東土,後者沿著太平洋波濤,以船堅砲利的形式抵達『中國』。二者都不會是和平的,折戟沉沙鐵未銷,理想主義者看到的所謂和平和中國主義者宣傳的中國人自古愛好和平,不過是磨洗過和改寫過的歷史。如果草原是另外一種形態的海洋,騎射則是另外一種形態的船堅砲利。
《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我其實很想問李世民或康熙,他們心目中的中心和邊陲各自是什麼?在唐代文獻裡處處可見、赫赫有名的『隴右』(隴山之西),即今日貧窮荒涼的甘肅,是李世民的邊陲還是中心?康熙和乾隆念茲在茲的滿洲,即今日人口外移、經濟衰退的東北,是他們的邊陲還是中心?在《皇帝的家書》裡,當康熙在蒙古高原星漢燦爛的夜晚,用滿文給北京的皇太子寫信時,他欣然於高原上的北極星和北京的位置並不相同。蒙古高原是他的邊陲嗎?當康熙和他的母親騎著馬南巡到繁華的蘇杭時,漢人江南是他的邊陲嗎?
當時的他們並無今天意義上的中心和邊陲觀念,但今天的我們反而可笑地用這組概念解讀歷史——包括『我喜歡從邊陲出發』這個標題,都是為了回應這種20世紀的國族歷史敘述中被強化的虛擬框架。我推想,未來某個世代的讀者,當他們用『我喜歡從邊陲出發』這句話時,他的意思是和玄奘一樣,是從中國出發。
《流動的邊疆》
然而現在我們還做不到。對於漢字世界可否擺脫中心和邊陲的糾纏,我非常悲觀。而我們目前能夠做的,就是繼續從所謂的『邊陲』出發,就八旗的出版方向而言,新的邊陲是『西南夷』(也就是『東南亞』)。它和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滿洲這些『內亞』族群一樣,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如果《流動的邊疆》是前菜,已經讓我們意識到雲南在歷史上的中心角色,正在編輯的《關鍵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則是一道豐厚的東南亞大餐,即將上菜。
作者介紹
富察延賀
八旗文化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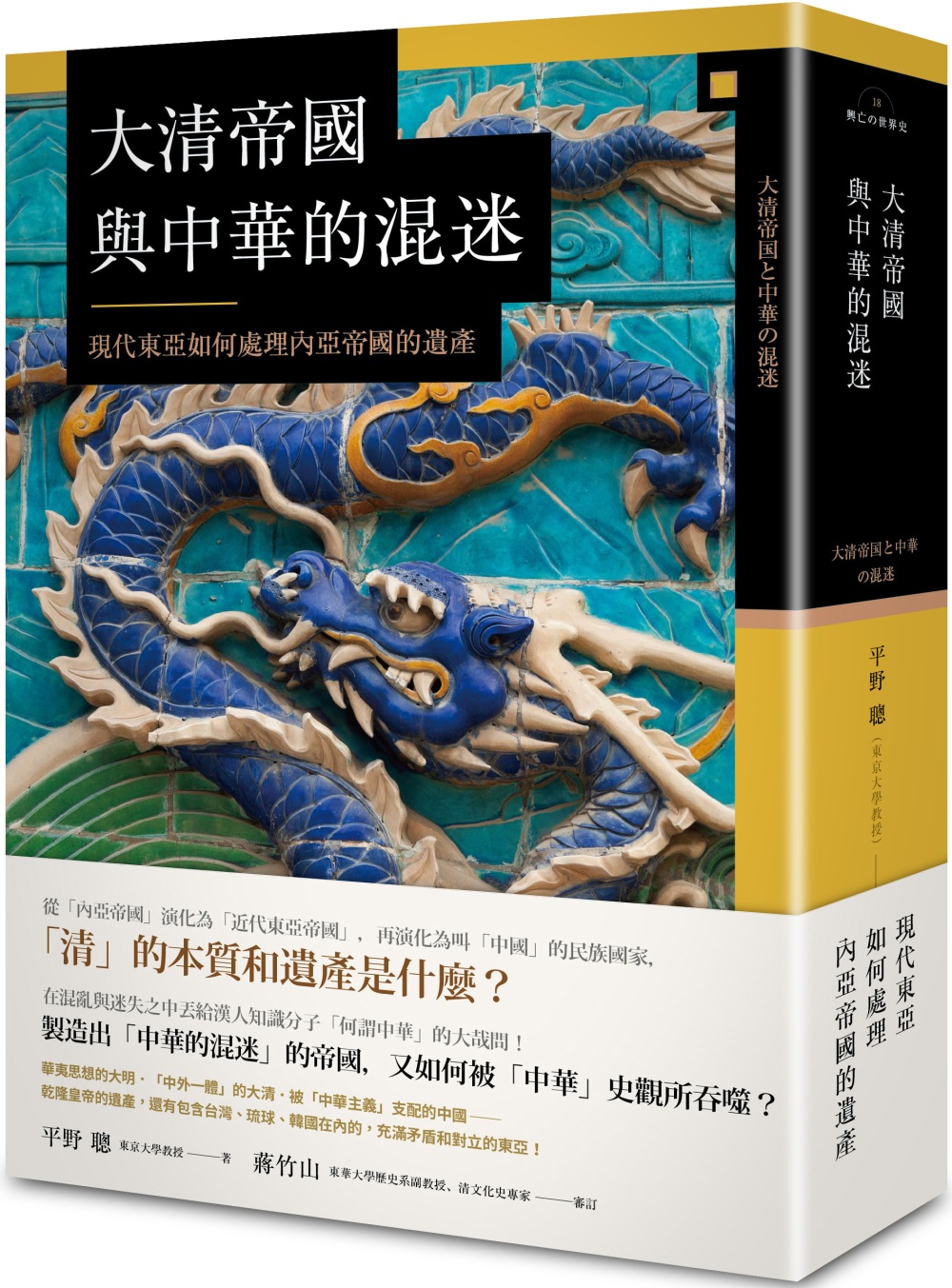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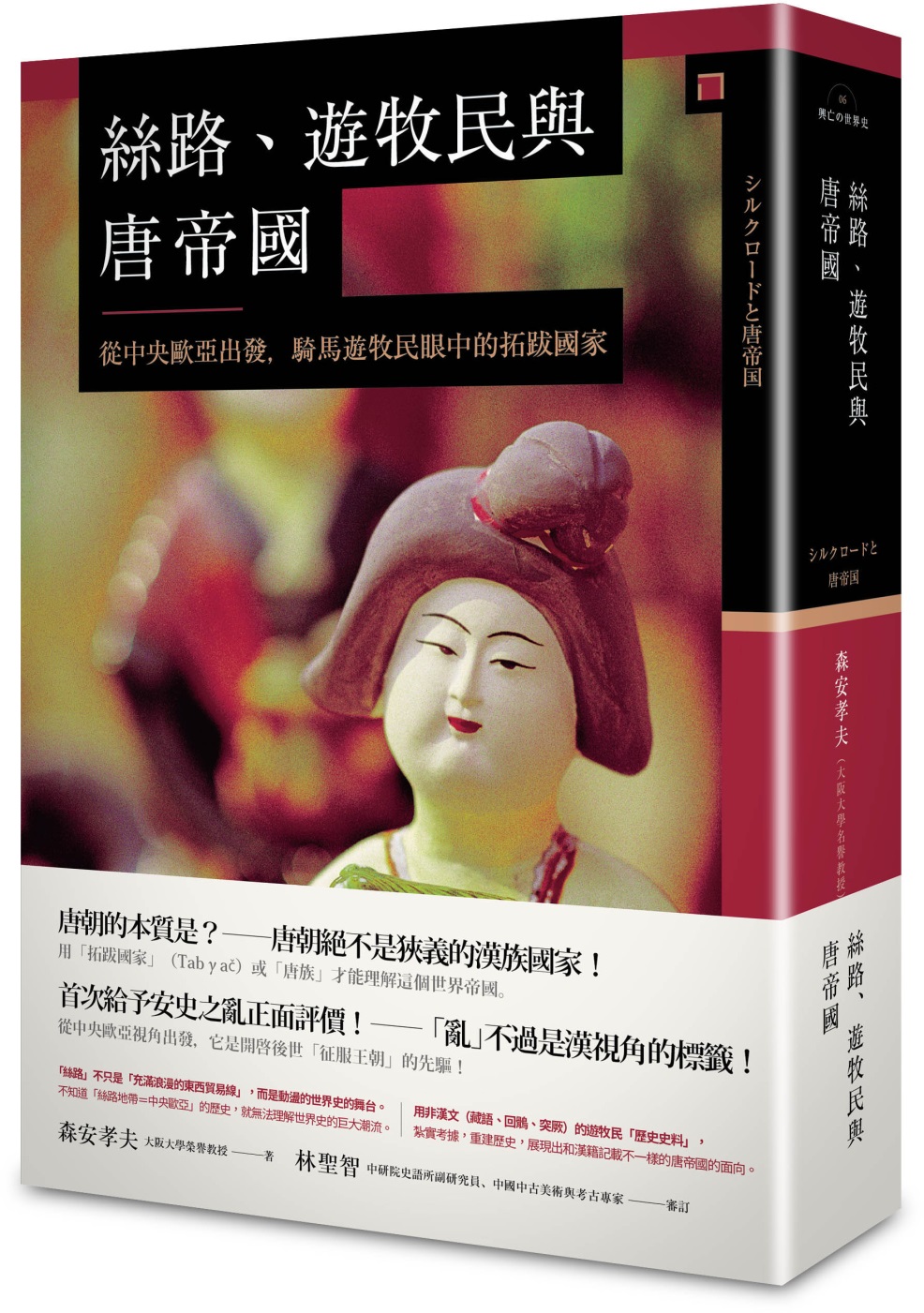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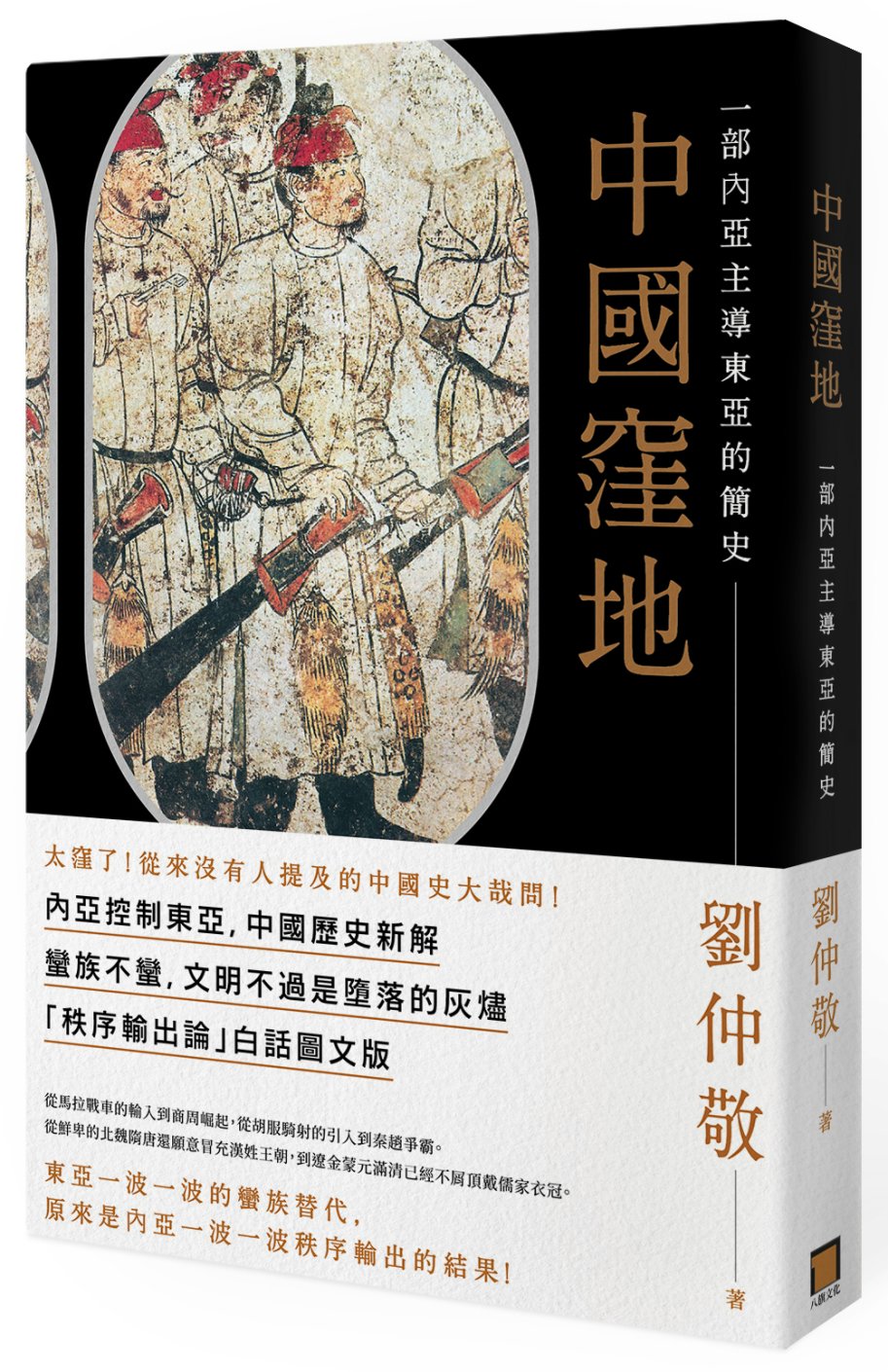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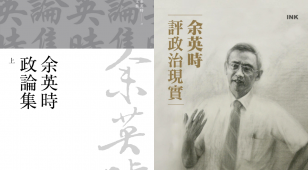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