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熱愛獨立音樂的文藝中年,就我個人的聆聽史,生祥樂隊作詞家鍾永豐,一直是私心崇拜的超級「搖滾英雄」。可是且慢,人家明明就是民謠詩人!但從另一角度,在搖滾名人堂眾多長髮披肩的吉他英雄,誰不是憂鬱破表、憤怒頂天?然而因為搖滾樂是張揚「個性」的聲音文類,在所有渾身帶刺的抗議者裡頭,鍾永豐僅僅訴諸溫柔便足以道盡憂鬱與憤怒,這豈非「逆風於叛逆」的更大叛逆?
先不說〈菊花夜行軍〉、〈古錐仔〉、〈欺我庄〉這些讓人悲愴沸騰的經典作品,搖滾詩人令我最佩服的,是不抗議的時候比誰都搖滾,好比〈分捱跈〉裡那個童言稚語百般撒嬌、硬要跟著哥哥去抓魚游泳的農庄小女孩口吻;還有〈阿欽選鄉長〉尤其出格,低傳真大聲公取代貝斯音牆、造勢鞭炮力壓搖擺鼓點──原來被地方派系宰制的「民主政治」,其競選現場可以讓鄉人耳馳目眩、彷彿嗑藥!
對現實可以嚴肅批判,也可以置入括號「歡喜讚嘆」,見山又是山的歌詞,才是十成真金的寫作功力。鍾永豐每每在不盡美好的世界聽出聲音烏托邦,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文化革命比這更基進、更前衛了。
打開鍾永豐的散文集《菊花如何夜行軍》,就像進入他作品的生命現場、看見歌詞背後的故事──不過我要提醒,讀者也需要動員理智,跟詩人一同思考「現代」民謠的聲學方法論,還有田野中的「傷心人類學」筆記怎樣化成動人詩篇。
書中〈行旅Bob Dylan〉是史才史識兼具的長篇樂評,鍾永豐說,西方搖滾樂發展初期就從黑人藍調裡「偷取」了「呼喚與響應」(Call and Response,又稱「對唱」):其一,民間文化遺產原本沒有版權觀念,恭請諸方大德自行取用、歡迎推廣流傳助印。其二,搖滾和民謠都是高度公共性的聲音文類,歌曲能穿透肺腑,是因為聽者的共鳴來自大眾政治意識的改造──人民的音樂不只要讓身體律動,更要讓社群在時代中「運動」。
在90年代反美濃水庫階段的青年鍾永豐,每日做菜煮飯吆喝夥伴共食,才發現「革命就是請客吃飯」,餐桌上方能建立夥伴情感,而非僅靠抽象的社運理念為號召。他在洗手做羹湯之間,體悟了客家菜主食副食系統與農村唇齒相依、大家族婦女得要透過飲食交換來滋養姐妹情誼,多年後刺激了《野蓮出庄》專輯裡頭「鄉土菜餚」的親切主題。
至於中年鍾永豐,暫別江湖卻不忘草莽,在水利局任內,他看見過度頻仍的「治水計畫」比江河還氾濫,反而破壞水澤生態。還有「重劃」後的整齊農田,少了畸零公有地,驕陽下勞動的農民從此失去田埂邊隨處可見的樹蔭,因而感慨寫下《種樹》。
而從政途中都市寓居,鍾永豐聽外省二代說起隔海鄉愁的「黃昏憂鬱症」:原來落日時分和「家」有這樣的聯繫!那麼,客語中給天光定位的「臨暗、暮麻、斷暗、暗晡」等等說法,顯然是自然經濟勞動中,農民安排一日時程的古老智慧、母語也從來都是勞動的棲地,於是有了《臨暗》。
當然,本書還記錄了本來留在「搖滾音樂史B面」的傳奇相遇時刻。
〈許國隆先生〉這篇,飢渴嗜讀帝俄前後寫實小說、卻不肯好好應付前途無量土木系課堂的大學生,在火車噪音轟隆不絕的唱片行裡,碰見了一位「用食指與中指,劈哩啪啦地翻唱片」的高人大哥。中南美國民樂派有沒有收?那這張實驗爵士呢?高人冷不防考起素未謀面的年輕人。一番攀談,大學生興奮跟著前輩回家,從傍晚聊到凌晨,鍾永豐才抱著一大疊左翼前衛詩歌、搖滾古典精品走下狹小木梯。兩人很快成為忘年之交,這位前輩人稱「苦桑」,是後來在台南開設大名鼎鼎的「惟因唱片行」老闆許國隆。
另一次宿命相見,那必然是〈歌手林生祥〉。1994年,還未中年的愛鄉協進會組織者鍾永豐,某個秋日被重機怒吼吵醒,跨下野狼125的斯文來客,是留長髮的淡江音樂才子林生祥。初識印象是,年輕歌者確有才情,但還沒有超越校園民歌和英美龐克。誰知道兩年後,兩個美濃子弟在故鄉重逢,喝酒澆灌友誼,運動者就拉著音樂人「過庄尋聊」,旋即又面對摧毀上游水源的政府開發計畫,最後他們土法造出了《我等就來唱山歌》這顆「文化原子彈」。
本土搖滾樂迷不可忘記這兩個指標性的時刻:1984年,年長十一歲的許國隆攀談鍾永豐,三年後政府開放洋菸進口。1994年,年長七歲的鍾永豐初見林生祥,這時台灣菸葉種植面積比起全盛時期已經砍半。菸農子弟鍾永豐生命中最重要的兩次邂逅,背後既有故鄉沒落的酸楚,同時也勾勒出一條台灣聲響文化如何從天際重重墜落土地的隕星軌道。
這也是為什麼,較年長的那一位,看見飛揚風發的後來者,沒有明說的淺淺不以為然竟如此相似。許國隆對「文青」的鍾永豐說:「讀這個,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詩集!」鍾永豐則在心底吐槽「玩團」的林生祥:「還在Pink Floyd?什麼時候了,龐克音樂都快散場了!」搖滾的耳朵、「垮掉一代」的心,涓滴注滿了民謠的筆。繞路蜿蜒,這便是戰後台灣「後殖民歲月」所代表的文化史意義。
事實上,1960年代以後,所有被美援文化、全球資本市場所磁吸的台灣知識分子都有一樣的徬徨:「先進國家」的音樂和詩歌、甚至政經制度,那樣的美麗,卻不是我們熟悉滋味。
從寫給自己聽的仿冒式西方搖滾,到寫給「人們」聽的客家民謠,赤腳走上回家的路,途中雖不能說死蔭幽谷,恐怕也荊棘遍布──成熟以後的詩人,終於從求新變奇的現代主義,回到了民歌傳統的形式主義。黃蝶谷邊的山歌、八音,其實與搖滾源頭藍調音樂精神相通:村人口中高歌的,正是交流情感與意見的「公共領域」!所以詩人接棒現代「民謠」,要留下一道清脆真摯聲音,回應農村漁港、生態土地、勞動底層。難怪鍾永豐寫出了台灣當代歌曲裡極有意境的口白〈嗷!(ㄠˋ)〉。沒有浮誇文字,農民一聲吆喝,老牛低吟回應,「聲音」不落言詮,純然的厚重詩意。
二十世紀初期,人類學家背著笨重錄音器材進入初民部落錄下市場講價、牲口鳴叫,保留雜訊和噪音才會有脈絡性的社會肌理,這是「田野錄音」。民謠音樂不是人類學,還是不免匠心獨運的藝術性重構,但是意圖回到「充滿雜質卻生機勃勃」野地的心情,倒是同歸殊途。
身為讀者,身為樂迷,讓我再說說與鍾永豐老師「初識」的那個下午吧。大學社辦裡的一個陰雨日子,來自美濃的副社長,啪嚓一聲關掉了皇后合唱團華麗炫砲的〈Bohemian Rhapsody〉。「來聽聽這個!」接著狹窄畫室響起了《菊花夜行軍》。嗩吶悲涼、鐵牛哭泣,還有移民新娘「國語」咬字貌合神離。「真有趣啊!」我開心地說,其實當時根本不懂。後來研究所唸了台灣文學,那幾年也是生平第一次離家,第一次知道思念父母,才終於有了一絲半點「本土關懷」。有個晚上把剛剛發片的《臨暗》專輯聽了四五遍,淚流滿面,突然驚訝想起,我不是早就「聽過」〈風神125〉的歌唱?
毋使問爾子弟做麼該愛歸來呀(不必問您的子弟為何要跑回來呀)
毋使問爾子弟做麼該愛歸來呀(不必問您的子弟為何要跑回來呀)
怎是會走歸來呀(為什麼會跑回來呀)
原來,在文化與土地斷裂的漫漫歷史裡,我這都市小孩也和前輩一樣──直到第二次相逢,才懂得緩緩回首故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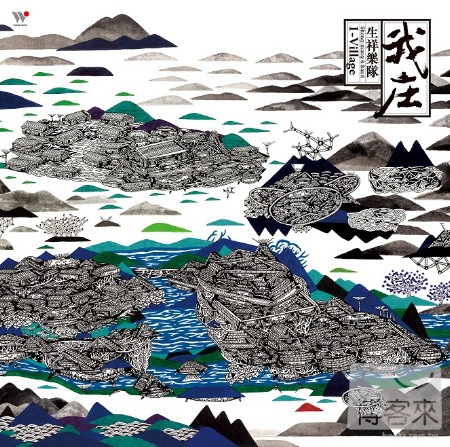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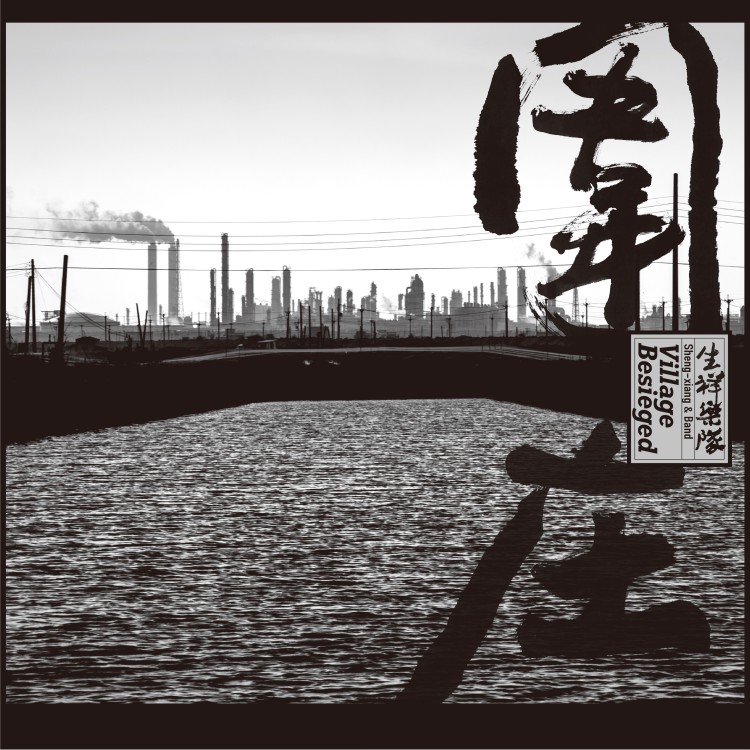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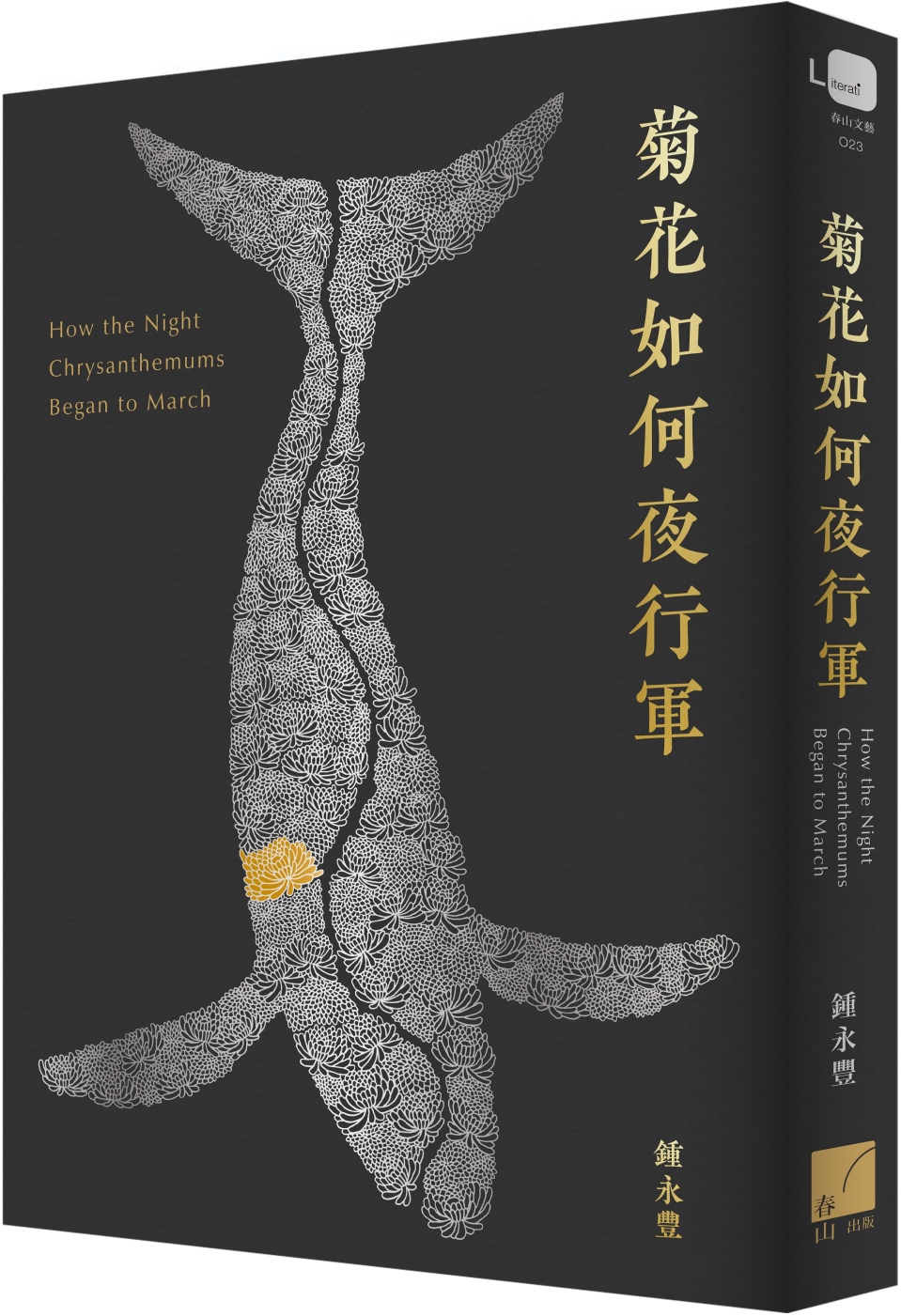

 生祥樂隊/ 《種樹》專輯
生祥樂隊/ 《種樹》專輯 生祥與瓦窯坑3/ 《臨暗》專輯
生祥與瓦窯坑3/ 《臨暗》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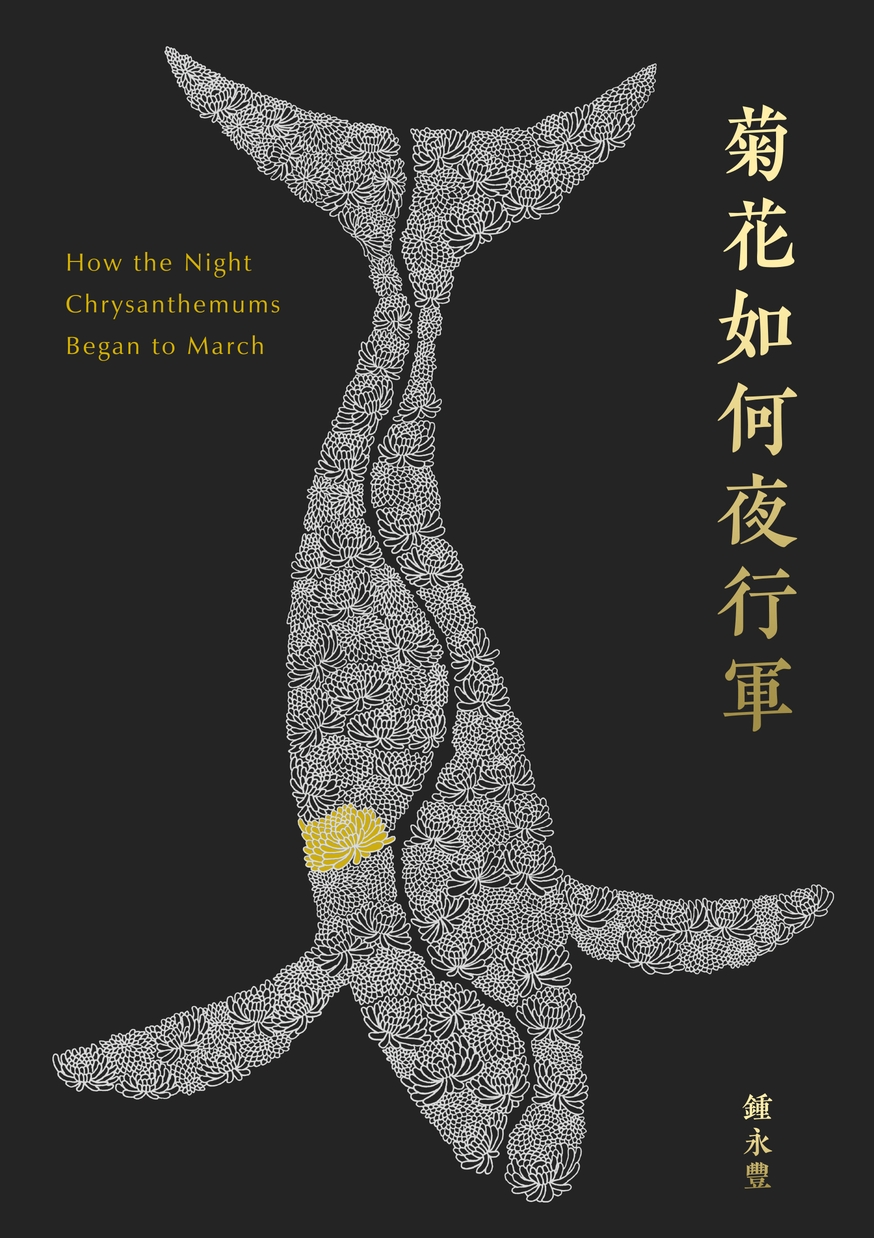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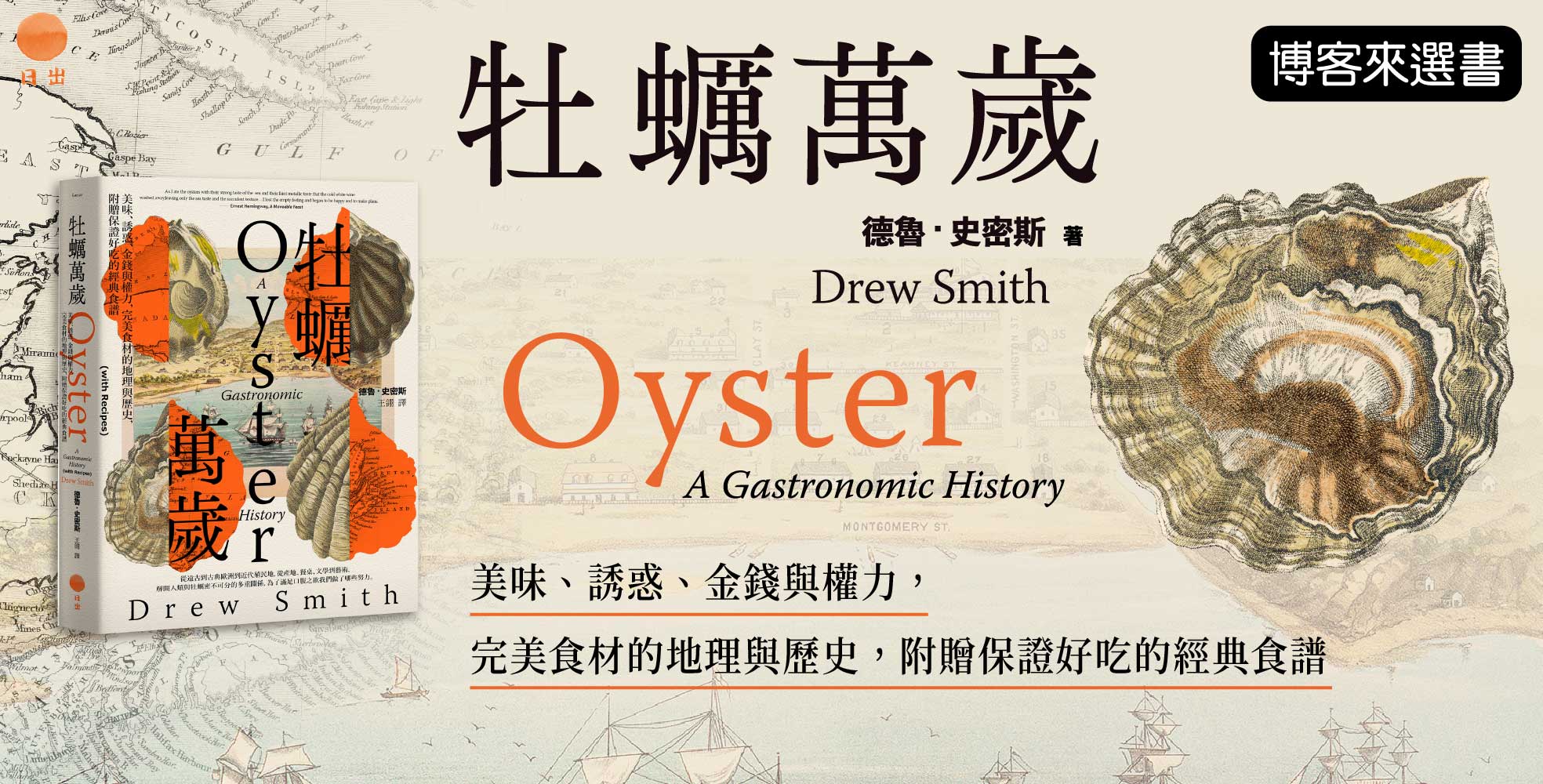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