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中,我待在雜誌社的那幾年,曾有一度向玠安邀稿,他屬於那種人情派的作者,那篇邀的稿子,若非關於李歐納.柯恩,便是關於巴布.狄倫,都是他熟稔的歌手與詩人,但玠安一度二度三度地推辭,最終卻真的寫了那篇稿子。他的原因說是我邀稿的心意打動了他。
能在工作上邀到他的稿子,自然是感覺成就不凡的,畢竟,他很難邀,訊息來回裡,除了工作層次上的往返,還含著作者與編輯情感層面上的再三確認。不過,在《問候薛西弗斯》這本散文集中,我見到了更多更多的、另一個陳玠安──一名流浪者,一位寫字者,以及,一個聆聽者。
薛西弗斯推動的宿命之石,在陳玠安的文字裡,成為一個一個日子的漥坎,拿捏好身段,似乎一蹲身,便能輕盈跳躍而過。但我們能夠去想像:相隔九年,將近三千多個坎,這麼大量的日子裡,究竟需要多少多少次的蹲捺躍越,才能夠教少年長為大人,教天真成為世故。
然而,每一抬沉重的步行,為何表面可以看似是輕盈的穿越,我猜度,那是因為,書寫者的心思,仍然是那名初上繁華台北城、無懼世事多炎涼的少年。與玠安隸屬於同一世代的我,邊讀《問候薛西弗斯》邊深深地自慚,自己在音樂和文學上啟蒙得多麼遲緩──他文字中躍躍然彷彿演奏於行間上的那些歌手,大多是我獨自一人在深夜抽菸寫稿時、電腦中一再重播的名字:Coldplay、PinkFloyd、Leonard Cohen、Bob Dylan、Tom Waits……至於黑膠,往往也是看了封面喜歡便買下,而完全不顧手邊根本沒有唱片機;包括在永康街古物市集翻得的根本不識姓名的冷門專輯,以及在誠品衝著折扣而買下的Louis Armstrong以及Nina Simon,膠膜仍包裹得好好地嵌在廚房牆上,佐著電影印刷海報充當耳朵的風景,是僅僅可供個人獨享的一點懷舊。
至於爵士小酒吧和祕密唱片行的造訪機率,亦遠遠及不上我去菜市場或二手古著店的頻率。就連咖啡,也是很晚很晚才上了癮。那些欲再訪而不可得的、屬於陳玠安的溫州街感傷之歌,於我大略是師大永康街的515咖啡,疫情期間收了店面,那些縮著脖子窩在針織毛衣裡、頂著冬天的冷風面向大敞的玻璃窗、捧著燙手的黑咖啡瑟瑟地點一隻菸的記憶不可重溫之。以及,永和水源街的自由溫室某一日大筆裁切了原本寬敞如自家陽台的、幾可漫步的吸菸空間,那原本可供我早晨一人獨占的木長桌菸灰缸被囚入牆內,僅賸下一小平方裡一隻皮沙發一小張矮桌可持菸踞之……我也體悟到了,某種永不能夠再被重譯的沉默的傷心,在每一段分別後,在每一回相聚時,那總被我們和友人一度再度地提起,提起了終究得放下。
 (圖片來源/pixta)
(圖片來源/pixta)
世界愈來愈快愈轉愈急,使我們被迫承受諸多地盛大且頻繁的失去,以及那伴隨著失去而頓時間活潑起來的記憶與追悼:卡帶、電話卡、BB.Call、大哥大、躡著手腳拆封一張CD的降神儀式般的喜悅時刻……當萬事萬物還沒有啟動全面智慧網絡的年頭,甚麼都還是古老的緩慢的手工藝,包括愛和友情。在《問候薛西弗斯》裡頭,這些足堪被追念被思索被復刻的感受與情分,也被如鮮地完整保留了下來,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懷念起來,那些久遠久遠以前、僅僅需要毋須言說的默契就從不會有人遲到的日子。況且,在那樣的日子裡,充滿了真摯的問候與約定:被紀念過的事物從不輕易地被拋棄,已然離開原地的人從不輕易地被忘記。
而今,我們駐足凝看,李歐納.柯恩已披著他那知名的藍雨衣(Famous Blue Raincoat)走得有些遙遠,任憑我們如何使力,也再追趕不上他那西裝優雅且道盡滄桑的身影。但我們還能透過閱讀陳玠安,在他清淡而深重的文字裡,在他不疾不徐的敘述中,追隨語言的穿越術,尋回一個溫柔纏綿的告別手勢,聽熟一首老歌娉婷繚繞的尾音。
一首歌,一張桌,一杯咖啡,一台舊筆電,皆是歷歷的時代的餘韻,且一曲歇罷一杯再滿地,未曾捻下過生存與愛的暫停鍵。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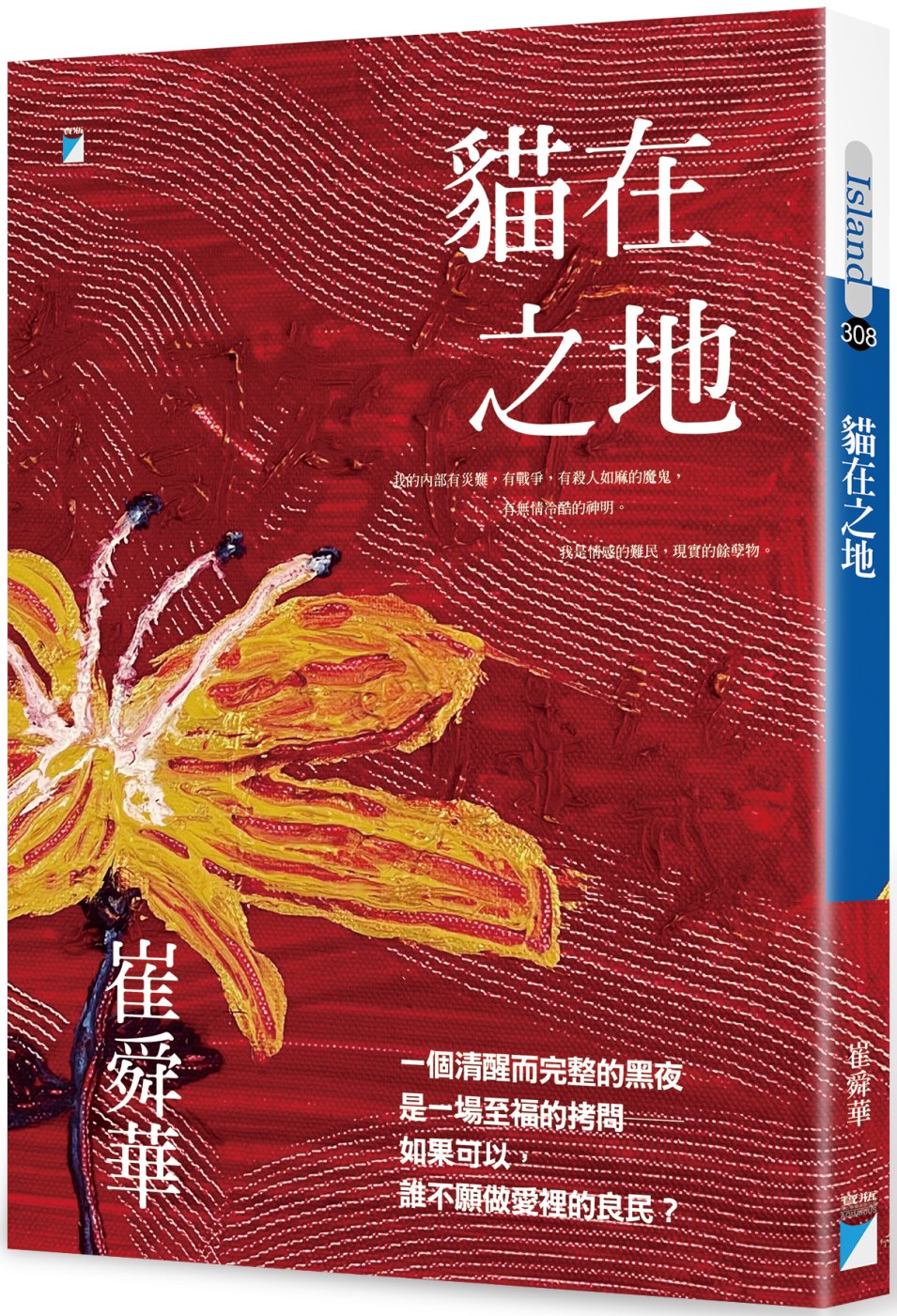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