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級警戒已經超過一個月,這也代表我有一個多月沒有進電影院。沒有出國的日子,我習慣每周去一次電影院,跟著光影遁入不同的世界。我總是挑早場電影,當外頭的陽光火熱亮白,把自己浸泡在黑黑冷冷的戲院,立刻脫離當下的現實。況且,早場電影往往只有三隻小貓光顧,比較不會因為聽見有人吃東西發出塑膠袋揉擰的聲音而反射性地緊握拳頭。不過自從去年疫情爆發以來,看電影的人變少了,不用特別挑早場,我有好幾次都是一人包場。
對我來說,去電影院看電影有如搭一趟短程的國際航班。短短的兩個小時內,不能接電話、不能滑手機,外界的訊息全然切斷,只能沉浸或認命地坐在位置上。那是純粹且迷人的小宇宙。
自從5月15日進入三級警戒後,電影院關閉,城市裡的人自發性的居家防疫,能不出門就不出門。照理說看片這種事靠著影音平台就可以打發,但是在家看電影畢竟跟在電影院不同,眼前雖是大螢幕,但手上總要滑個小螢幕,貓還會過來踩踩肚子。有時候,電影看到一半會想到應該把冰箱裡的肉拿出來解凍,否則等下無法煮雞湯……影片的時間軸正常的走,但我腦裡思考的軸線卻千頭萬緒,任何風吹草動都可以讓自以為的「與世隔絕」瞬間崩壞。
居家上班或居家隔離都無法與世隔絕,網路把我們的敏感神經從之前朝九晚五的上班時間變成24小時。總是有新的訊息敲過來、有新的網購慾望想下單,偶爾會看看一些厲害餐廳的外賣外送菜色,但總在最後看到大量塑膠包裝而決定還是自己下廚……日子在道德感和罪惡感間拉扯。
難免要出門,通勤的時候會跟戴著護目鏡、手套、全身包緊緊的人擦肩而過;起初覺得城市的街景與人物好有科幻電影感,但多看幾次就見怪不怪,科幻成為日常。不曉得我們是愈活愈前衛還是愈活愈倒退,前衛到無需人與人的接觸世界就兀自運轉,抑或是倒退至宇宙之初人與人無法交流的原始狀態。
雖說少了許多實體的接觸,但是雲端上撞擊的力道反而不斷翻攪情緒。當聽到誰誰誰的發言就讓人氣得關電視、當知道立陶宛要捐贈疫苗並說出「熱愛自由的人應當互相幫忙」時,立刻感動的把之前去旅行的照片拿出來滑,重新把首都裡驕傲獨立的「對岸共和國」憲法條文讀一讀:
每個人都有愛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無所事事的權利/
每隻貓沒有義務要愛牠的主人,但必須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
沒有人有暴力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權利成為任何國籍的人/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自由負責/
不要投降……
 1998年愚人節成立的「對岸共和國」位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老城區。上圖是它的入口。(攝影/黃麗如)
1998年愚人節成立的「對岸共和國」位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老城區。上圖是它的入口。(攝影/黃麗如)
 遊客在憲法牆前拍照留念。(攝影/黃麗如)
遊客在憲法牆前拍照留念。(攝影/黃麗如)

對岸共和國內的小書店與房舍。(攝影/黃麗如)
思緒跟著世界的動靜起舞,時間也跟著全球的作息而轉動。雖然無法出國、甚至多半宅在家,但並不覺得被「困」在台灣。六月的法網讓我每個夜晚都曬著巴黎的紅土豔陽;緊接著是我最愛的「美洲盃足球賽」,早上五點跟八點各一場球賽,看著梅西、阿奎羅、馬丁尼茲、蘇亞雷斯在南美土地上奔跑的樣子猶如在清晨打下強心針。與美洲盃同一時間的焦點足球賽則是「歐洲國家盃」,台灣轉播時間是半夜十二點一場、凌晨三點一場……有時侯看完三點場的歐國盃,還可以接上凌晨五點的美洲盃,歐洲大陸跟南美大陸時間無縫接軌,也跟台灣島嶼的時間呵成一氣、盃盃相連至我的酒杯。
在足球賽前,我是廢人一枚。猶記得上星期六我一路從晚上十點的法國對匈牙利,看到德國對葡萄牙,再接三點的波蘭對西班牙……一路以波爾多、綠酒和伏特加佐賽。我很清楚,不管我現在有沒有在台灣,我都會在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以相同的儀式看著電視轉播,隨著進球與否大喜大悲。就在此刻,溫布頓也要登場了,當台灣被疫情苦惱而喊著要紓困、百業蕭條時,世界體壇賽事的密集猶如在防疫後的煙火,分裂的場景讓人情緒錯亂。我在台灣,還在上班,但又好像沒在台灣,下班後可以看球賽看到天亮,自以為在歐洲或是南美。看完球賽,再調回台灣時間繼續上班,不得不佩服自己已進階成為時間管理大師。
歐國盃、美洲盃、溫布頓在7/11或7/12進入決賽,多麼希望看完決賽後就可以宣布三級警戒降級。奇妙的7/12設定,不禁懷疑起訂下這個日子的人是否也是個運動賽事迷,硬要把警戒拉長至頂尖賽事全部結束那天。靠世界大賽維生的運動酒吧在這一波注定只能關門大吉,沒有群聚舉杯歡呼的可能。
老實說,最近球賽太密集,加上在不同時區舉辦,久違的時差感時常湧現。早上五點起來看智利跟阿根廷踢球,轉播員說著這是多麼美好的午後……黃崇凱小說《新寶島》裡的「大交換」情節在此時讀來格外真實。我在哪裡?等一下要在里約喝著SKOL配炸肉丸(Coxinha)嗎?還是一覺醒來,就在小說設定的古巴哈瓦那,那就去打一劑古巴引以為傲的疫苗吧(感覺像抽古巴雪茄般輕鬆)!在這個奇異的時刻,還有什麼不奇怪?
作者簡介
個人部落格:享樂遊牧民族
Fb:享樂遊牧民族
※本篇文章由作者個人創作授權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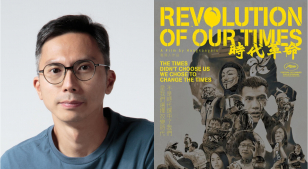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