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荒原》的故事,從記者馬汀.史卡斯頓來到旱溪鎮,準備做一則無傷大雅的「旱溪鎮大屠殺一週年回顧專題報導」開始。這個小鎮在去年此時,發生了一場血腥的「星期天大屠殺」。牧師冷靜且冷血地射殺了五人後,被當地警察槍殺身亡。
乍看之下不過是又一則悲劇,然而當馬汀開始遇到曾身歷其境的小鎮居民,讀者便能感覺到,事情似乎不像報紙頭條那麼簡明易懂。
理應痛恨殘暴牧師的小鎮居民,卻略帶猶疑地說:其實,他像是聖人。
馬汀不敢置信的追問,「但他是冷血謀殺五個男人的兇手啊。」這五個男人,就他所知,沒有犯罪紀錄,可能稱不上品行優良,但絕非罪該致死。
「我知道,我在場。」鎮民說。
也許其他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馬汀訪問了射殺牧師的警員,也訪問了鎮上受害者的遺孀。出乎意料地,他們儘管無意否認牧師犯下的謀殺案不可饒恕,卻也異口同聲地說,他真的是個好人──
不是說好人便不會殺人。然而好人殺人,通常是有理由的。在這個案子中,調查指向牧師係因被揭發戀童癖後,憤而行兇。可悲的是,在當今世界,牧師與戀童擺在一起,幾乎是沒有人會懷疑的組合。對此同樣深信不疑的馬汀,在小鎮盤桓數日後,卻憑藉著優秀調查記者的嗅覺,認為此一理論頗有蹊蹺。馬汀於是決心抓住這個機會鹹魚翻身,重返榮耀。他的採訪進行得極為順利,也似乎即將揭開謀殺案背後隱藏的祕密。然而此時,荒地突如其來的大火,竟燒出兩具不為人知的謀殺案屍體。這兩具被確認為一年前失蹤遊客的屍體,徹底打亂了馬汀的步調──牧師屠殺案是否與此案有關?他的證人真的可信嗎?此案的兇手又是誰呢?
讀《烈火荒原》,很難不想到之前珍.哈珀(Jane Harper)拿到以金匕首獎等大獎的得獎作《大旱》。理由也很簡單:他們都是澳洲人,筆下的兩部作品均與澳洲的「大旱災」(Big Dry)有關。他們都被旱災所觸動。
澳洲近年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旱,便是1996年到2012年間長達16年的旱災了。由於橫跨千禧年,因此這次的旱災也被稱為「千禧旱災」(Millennium drought)。就在澳洲政府好不容易宣布大旱災結束時,澳洲東部的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州部分區域卻戲劇化地再度陷入乾旱。到了2014年2月,昆士蘭州80%、新南威爾斯州62%處於嚴重乾旱狀態。許多放牧者不得不轉移陣地或射殺牲畜,因為他們已無法應對惡化的水資源供應。
加上先前的16年,那是多麼長的一段時間啊。這段時間內並非一滴雨都沒有,然而雨水卻遠遠未達到過去的標準。《烈火荒原》的故事背景,便是設置在這個在千禧旱災後仍持續乾旱的地區。小說中提到的墨瑞河(Murray River),是澳大利亞最長的河流,也正是此地的母親河。小說中主要的兩個背景設置在臨墨瑞河的貝林頓鎮,以及無水的旱溪鎮,顯然不無對比之意──當貝林頓鎮尚且無虞時,旱溪鎮卻因長年的旱災而破敗傾頹。水是生命。失去了水的旱溪鎮,正逐漸死去。旱溪鎮的一切悲劇都起因於旱災,於是謎題的解法也不難,只要跟著水走──只要馬汀在這乾涸的土地上,還能找到任何一滴水的話。
 澳洲最長的河流墨瑞河。(圖片來源/wiki)
澳洲最長的河流墨瑞河。(圖片來源/wiki)
讀《烈火荒原》,於我而言是一趟非常享受的旅程。儘管在閱讀的過程中時常覺得燥熱不已、口乾欲裂,然而這或許也體現了作者克里斯.漢沃(Chris Hammer)的寫作功力。任職記者超過三十年的漢沃,下筆力道頗為精準。儘管小說後半,事件陸續勃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發撲朔迷離,氣氛也逐漸緊繃,情緒愈發高昂,卻將之梳理得有條不紊,並未失去一開場的節奏。以至於當我看完全書,竟很難相信這麼多事都是在十日之內發生的。
本作是典型的「陌生人來到小鎮,揭發小鎮罪惡」類型的作品。然而與其他類似作品不同的地方,在於漢沃相當漂亮地演繹了所謂的「小鎮罪惡」。儘管面臨乾旱,加上設備不通,使得此地頗有孤島氛圍,但鎮民畢竟是21世紀現代澳洲人,不怎麼可能形成像是昆恩《然後在第八天》裡那樣與世隔絕,自有一套信仰與處世體系的封閉小鎮,更遑論共同發起邪惡陰謀。他們只是像普通人般地生活──而正正是「像普通人般地生活」造就了旱溪鎮遭遇的悲劇。
另一方面,漢沃的記者身分,也使得他得以精準描繪媒體與從業人員的樣態。小說中,與主角馬汀有瑜亮情節的報社王牌記者德佛,既是馬汀完全看不順眼,卻不得不承認其實力的記者類型,也是他在歷經意外的囚禁事件後,已然被迫拋棄的自我。《烈火荒原》因而不僅僅是對真相的追尋,也是對自我的探究──報導的目的與報導的倫理,是一場永恆、卻絕對有一方勝出的比賽。
巧的是,當我讀完本書時,台灣苦盼已久的梅雨也終於落下。
路那(推理評論家)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小說嗜讀者,評論散見各處。合著有《圖解台灣史》、《現代日本的形成》。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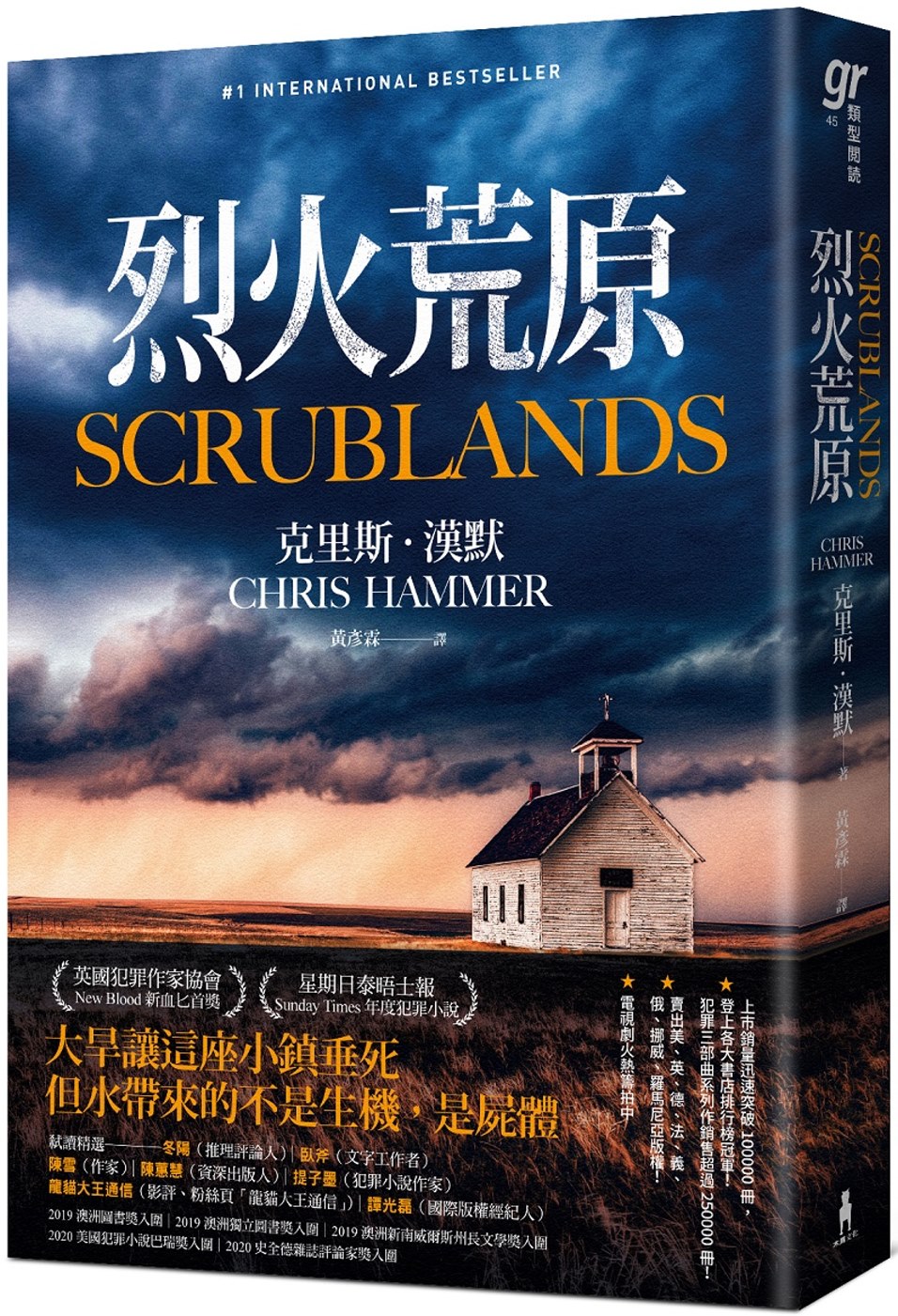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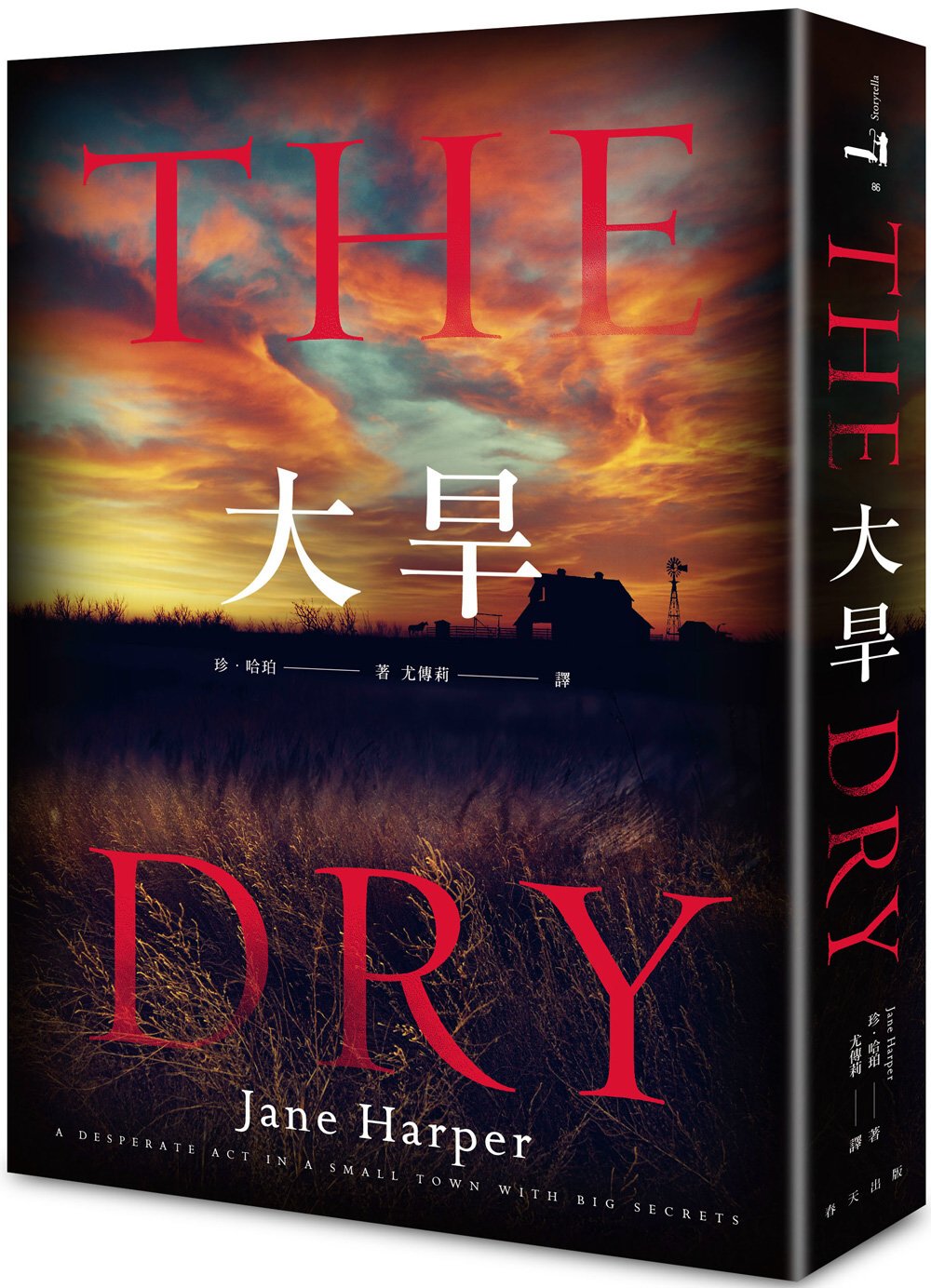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