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謔、嘲諷、機智或俏皮話——姑且稱之為花招的語言,感覺總是歐美拿手得多。我有個日本朋友,在不苟言笑的環境中成長,有次有個陌生人對她說的話華麗了些,她就驚為天人——她對言語的表演如此沒有免疫力,一使我擔心她轉身就被拐去賣,二使我全盤重新思考「加料說話」的意義。「裝飾」,一方面總與「鋪張浪費」有關,另方面也連結到「鄭重其事」——收受方會有盈餘感很自然,盈餘,可以別名為「情趣」、「風雅」、或「幽默」,就如音樂或藝術,這些快感奢侈品是生存優勢的產物,顯示使用者身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
胡說八道亦有道
因為,推理小說家不但不是孔夫子的信徒,筆下偵探神尾武史更是一舉打破一般人引為共識的對話默契:他信口開河,他無中生有——他說話絕不是為了循規蹈矩,或道德積分。
不過,武史不是只把語言從實用性中解放出來,唬爛王揭露的更多——如同「盜亦有道」,他是「胡說八道亦有道」。一般推理小說中,偵探也會使用語言陷阱來套情報或驗真偽,不過,那常是偶ㄧ為之或臨門一腳,武史天花亂墜與百無禁忌的程度,令這種常態為之改觀。
對他來說,只有策略是重要的。一分鐘後他會坦承話是編的,十分鐘後就會解釋騙的意義,但在開口瞬間,策略才是他的母語,語言反而不是——語言可以純粹只作為策略嗎?不管讀者是否同意,武史確實以他的顛顛倒倒,映照出日常語言太過沈睡與馴服的一面。語言資源應該包括語言策略的多樣化,我們甚至應該教導各種樣態的「說謊編造能力」,以使人們更了解「語言是怎麼回事」。這真的通常太被忽視了。——這也是魔術的價值。不少創作者都回顧過受魔術震動的童年往事,我認為那遠非單純的軼事,而涉及對「驚嘆」這種感情的肯認。武史的其中一個身分就是魔術師,這個設定除了可能與東野創作觀的「夫子自道」有關,也恰如其份地活化了推理的形式——小說與讀者的關係,必須保持在「既動腦又驚嘆」的狀態中。
寫到這裡,希望讀者不會誤以為《迷宮裡的魔術師》讀起來會像語言學或哲學講義——東野一向承襲克里斯蒂化繁為簡的特長,使故事讀來一派輕鬆,節奏明快。不少日本後疫情時代浮現的問題都被寫進去了:觀光相關產業的倒閉潮與在宅工作導致的夫妻關係破裂等——但並不給人趕流行的應景之感,處理沈穩。雖然有當下性的元素,小說讓我很驚訝的一點,反倒是某種復古情調。
老師也會遇見兇手嗎?
武史的哥哥——小鎮上的老師,幾乎令我想起«砂之器»裡的退休後開雜貨店的老派刑警——本職之外,彷彿兼任里長與社工,這種既良知又褓姆的調停工作,竟然並不因為學生出社會停止,反而橫亙一生。舉凡事業難題到婚姻困境,老師依舊不辭辛勞。現在還有這樣的人物嗎?我不時驚奇。都說教師的生活最單純,但從教過的學生將成三教九流來看,能把教師所在,視為社會眾多漩渦的交錯點,不能不說,相當慧眼獨具。
眾多學生都「深受老師照顧」,串起故事的「老師的女兒」真世,與父親老師卻不那麼親近。就如「傅培梅在家從不下廚」——許多人都以為身為「愛的勞動者」如老師或心理師的親人,想必三百六十五天陽光普照,就像名廚子女一定口福日日。這種誤判剛好構成了這宗犯罪最後一塊嵌合板,讀者不妨留意其中幽微巧妙。
那些花招可以教我們的事「愛的職人」在外春風化雨後也會倦勤。我就見過比一般人都要寂寞許多的教育者子女——當然這並非無情也離遺棄甚遠。但教育者的子女較無淘氣的自由這點,小說寫得確實入木三分。魔術師偵探武史的出現,與其說調查犯罪,還不如說也是為憨厚的真世創造一個「第二父母」。這是把「愛的教育」藏在「耍花招的教育」中,胡鬧之中,不無深意。
近尾聲時,東野的惡癖還是犯了,出現「靜香絕對不會背叛大雄」等論調,給人「又把女人當獎品」的膩感,好在是微小發作,不至於結構性地惹人厭。就當是無趣的小贈品好了。(嘆)小說還有些其他推理常出現的元素值得一提,「作文簿之亂」(書寫卻埋下了什麼)或「結婚前夕(就是會發生謀殺案)」——前者與«沈默小提琴»,後者與宮部美幸的«誰?»相參照,也會很有意思。
作者簡介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散文《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OKAPI專訪:「我不願意說一些雞湯與金句,告訴你如何做人。」──專訪張亦絢《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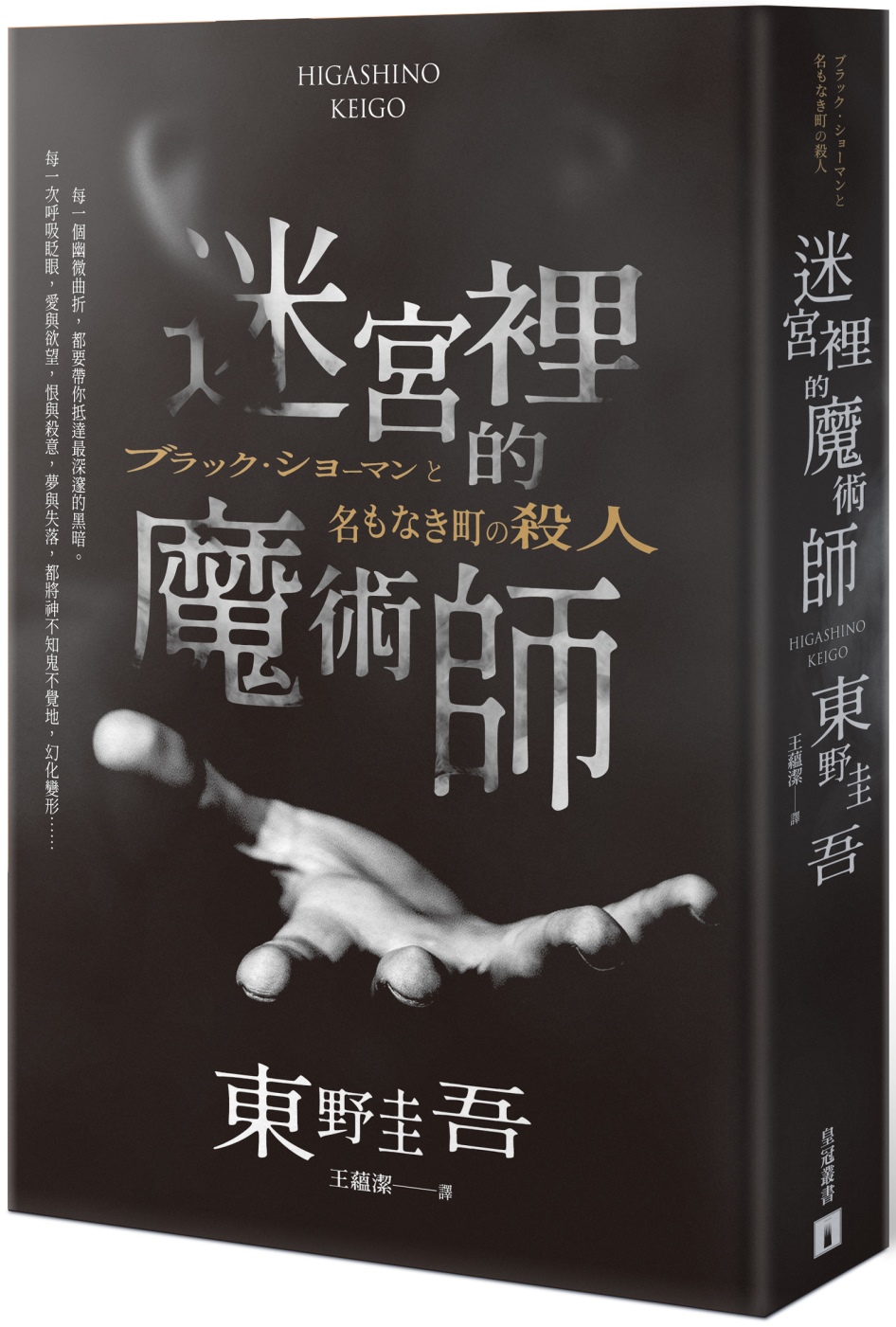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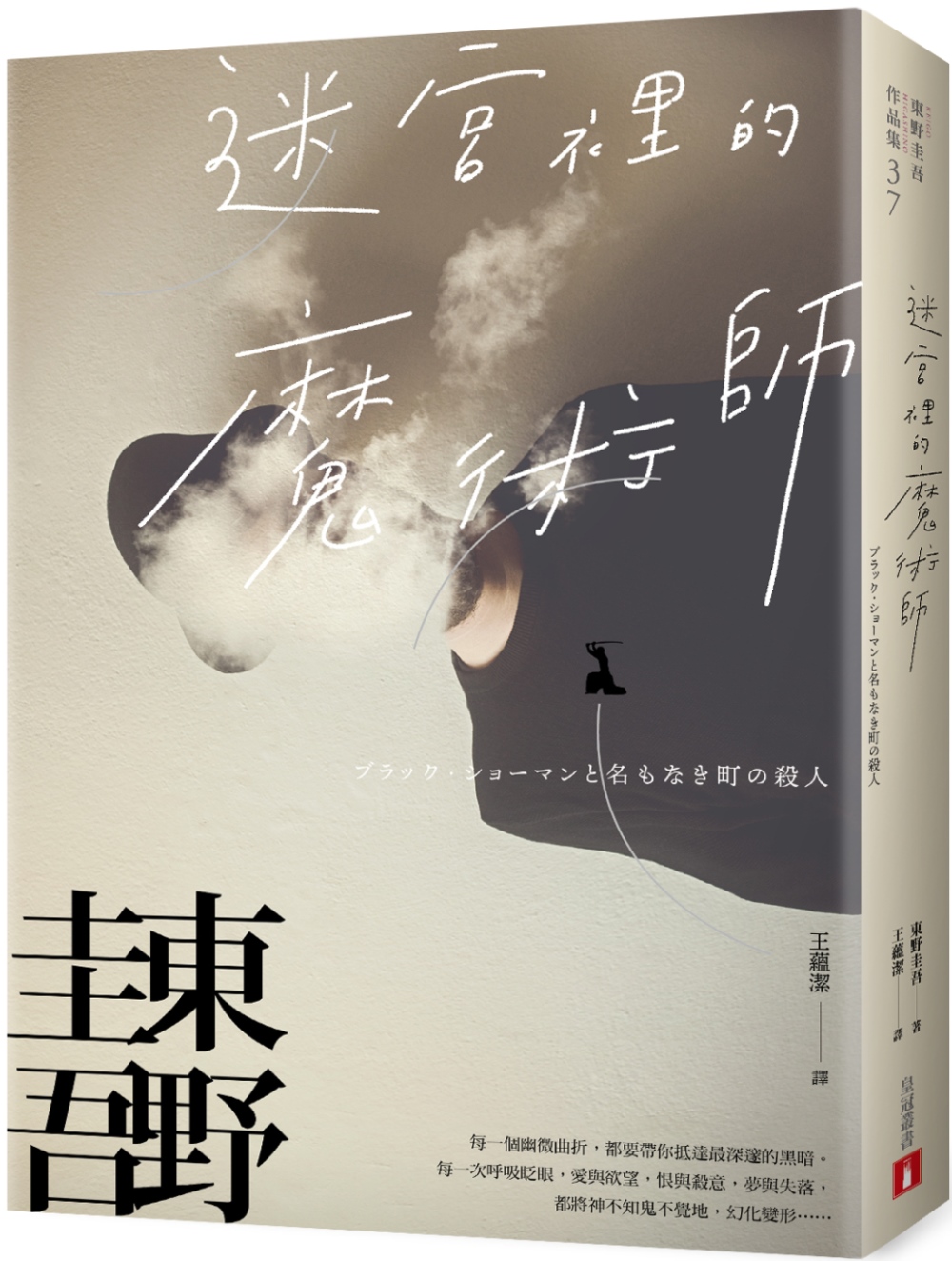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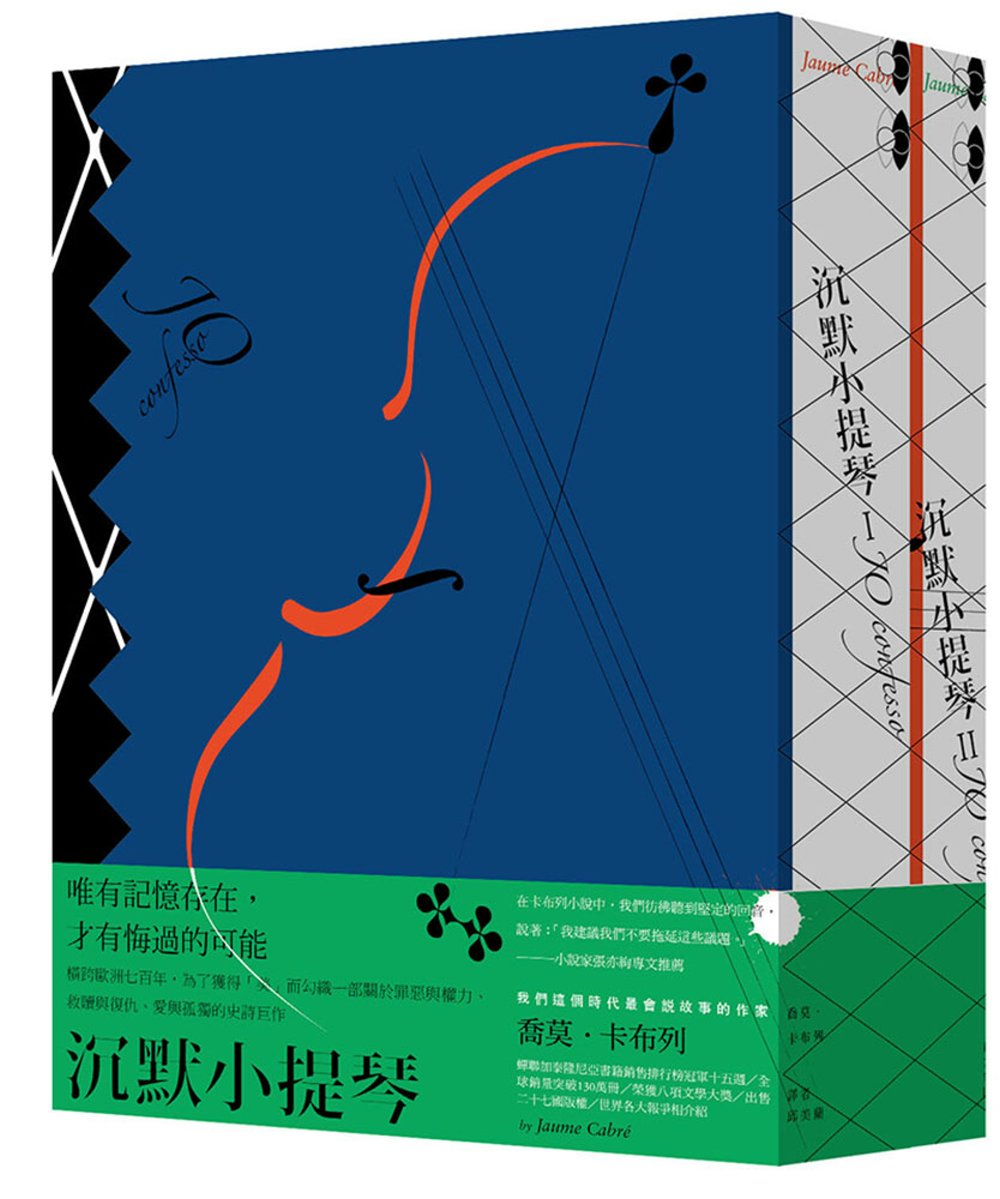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