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作家/潘柏霖獨家開箱文
我常常覺得所有人的創傷都是從童年陰影來的這種說法太便宜了。
基本上,首先是你根本不能從現在的情況,倒推回去過去發生的事情,試圖從其中找到決定性證據,某條岔路,某個選擇,因此導致你現在從原本的那條路,走到現在這條路去。當然,或許是因為童年的某支霜淇淋你還沒吃到就掉到地板上,你的父母不願意替你再買一隻,而造成你長大後的厭食暴食自我;或許是因為曾經在某個下午,你的父母出門忘記告訴你,而你在陽台看著樓下的街景等待他們回來等待到哭了出來,而導致你如今對愛人的難以信任。當然,有可能——但我想,那就只是試圖拿一個部分正確的答案,去解決一個根本太過複雜的大問題,是拿著幾乎已經快要不黏的OK蹦,去貼你不斷流血還沒癒合的傷口。
《接棒家族》中有段我很喜歡的對話,大致上是這樣進行的:父親要和女主角說明母親為什麼不在了以及母親究竟是去了哪裡,父親說等到妳長大之後才能知道,而當父親終於解釋母親究竟去哪裡了之後,女主角的想法是,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趕快長大、趕快變聰明,但也許一直當一個小孩比較好。
但後來女主角還是成長了,繼續長大,變得更聰明,雖然會懷疑自己的身世,但也沒有那麼悲傷,故事的語調原則上維持著這樣的方式,很平常地告訴你一些很悲傷的事情,因為以很平常的口吻和語調去講述,而讓這些悲傷乍看之下好像沒有那麼悲傷,一些很難過的東西就是透過這樣像是小蟲咬似地不斷進入觀眾的體內,最後莫名其妙就住在觀眾體內,長成很大很難受但一時之間好像又還是哭不出來的怪異情緒。
這本小說餵食悲傷給觀眾的方式比較像是冰塊裡面加了碎玻璃,讀者在被某些溫暖開朗的敘述和親情的感動之下,忽然就吃下了那些殘忍現實的玻璃,一時之間不知道自己的痛是來自於那些太過溫暖的情懷,或者那些太過凶殘的現實。但無論是多麼殘忍的現實,女主角都仍然活了下來,她長大了,她理解更多痛苦的現實,她還是繼續前進,沒有放棄。就像她自己說的,「不可能每天都像現在這麼快樂,總有一天,會遇到必須笑著才能撐過去的事」,我在想,或許那就是這本小說的重點:撐過去。
我其實沒有很想知道這些觀念,角色的歷程是不是童年因素造成的,想要努力活下來,在痛苦中仍然能感覺到幸福,不斷跌倒,但不斷爬起來,這有多少東西是因為童年的缺損,或者像是這本小說想說的,成長過程中接收到不同家人,但豐沛的愛而造成的。我只知道,他們就是長成這樣了,他們就是活了下來。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愛是好的愛,什麼樣的家庭是好的家庭,客觀現實的好是否對單一個體是真的好,如果內部有充沛的愛但客觀現實條件無以為繼,孩童會幸福快樂嗎。每個人都想要幸福,但幸福是什麼,怎樣的狀況才是幸福,而我們在淒慘悲傷的世界中,我們要怎麼撥開雲霧,看過悲傷,也還能記住快樂,記住活下來的必要。
我想或許這本書可以提供一些暗示,像是,我們不應該只是鼓勵追逐夢想的人,我們應該鼓勵那些被現實擊敗,絕望而放棄夢想,終於平凡,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悲傷,接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幸的人。
他們還是活了下來,很努力去愛,也很努力被愛。 潘柏霖/20200814

獨家試讀內容!故事由此開始↓↓↓↓↓
傷腦筋。我完全沒有任何不幸。真希望自己有什麼煩惱或是困難,但一時完全想不到。每次都這樣,所以面對這種狀況,內心就充滿歉意。
「老師很欣賞妳的開朗,但如果不把困難或是煩惱說出來,別人就無法瞭解。」
坐在對面的向井老師對我說。
這是二年級最後一次升學面談,我和班導師面對面坐在講桌前的課桌旁。平時總覺得教室很小,但只剩下兩個人時,就覺得很寬敞。
我沒有什麼困難,也沒有任何煩惱。正在思考該怎麼回答時,老師說:
「森宮同學,妳不用說妳不想說的事,但老師想瞭解妳的家庭狀況,嗯?」
「森宮……,對,我是森宮。」
老師叫我「森宮」之後,聽到我重複了自己的姓氏,露出了訝異的表情。她是不是覺得我還無法適應自己的姓氏?
「啊,不是啦,因為同學和周遭的人都叫我優子,所以叫我姓氏時,腦筋一下子轉不過來。」
我告訴老師真正的理由後,老師輕輕點了點頭,「喔,是啊,優子是個好名字。」
我活了十七年,深深體會到優子雖然是個很常見的平凡名字,但還真是個好名字。不光是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聽起來更舒服,「優子」最大的優點,就是無論和任何姓氏都很搭。
我剛出生時叫水戶優子。之後曾經改名為田中優子、泉之原優子,現在則是森宮優子。因為為我取名字的人並不在身邊,所以不知道當初是基於怎樣的想法取了這個名字,但優子無論和很長的姓氏或是很短的姓氏,聽起來很厲害的姓氏,還是很簡單的姓氏都很搭。
「森宮同學,妳經歷了各種不同的經驗,但人如其名,妳真的是一個溫柔的孩子。」
「喔……」
雖然我的姓氏改了很多次,但並沒有經歷什麼了不起的經驗,而且也不會特別溫柔,但向井老師平時很少稱讚學生,既然她這麼說,我就只能道謝:「謝謝老師。」
「但我總覺得妳有點美中不足,在某些方面不知道該說是不夠坦誠,還是讓人覺得有點距離。」
「喔……」
「如果妳有什麼想法,願不願意說出來?這就是老師輔導的意義。」
「對、對啊。」
到目前為止,不止一個老師對我說:有什麼事都可以說出來。不光是班導師,保健室的老師,還有學校心理輔導老師都經常這麼對我說。老師都在等待我向他們傾訴煩惱。我需要的是煩惱、煩惱。老師都熱情地向我張開雙手,但我沒有任何煩惱,真的很對不起他們。我應該要有一、兩樁悲慘的事,才能夠對付這種場面。雖然我很想編一個煩惱應付一下,但聰明的向井老師一定會馬上識破。如果要說我有什麼煩惱,就是遇到眼前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只是每天過平凡的生活,但好像辜負了老師的期待,讓我抬不起頭。我明明不覺得自己有勉強或是逞強,但只是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就會引起老師的關心。只是過平凡的生活也好像是罪過,這才是我的不幸。→→→更多內文請看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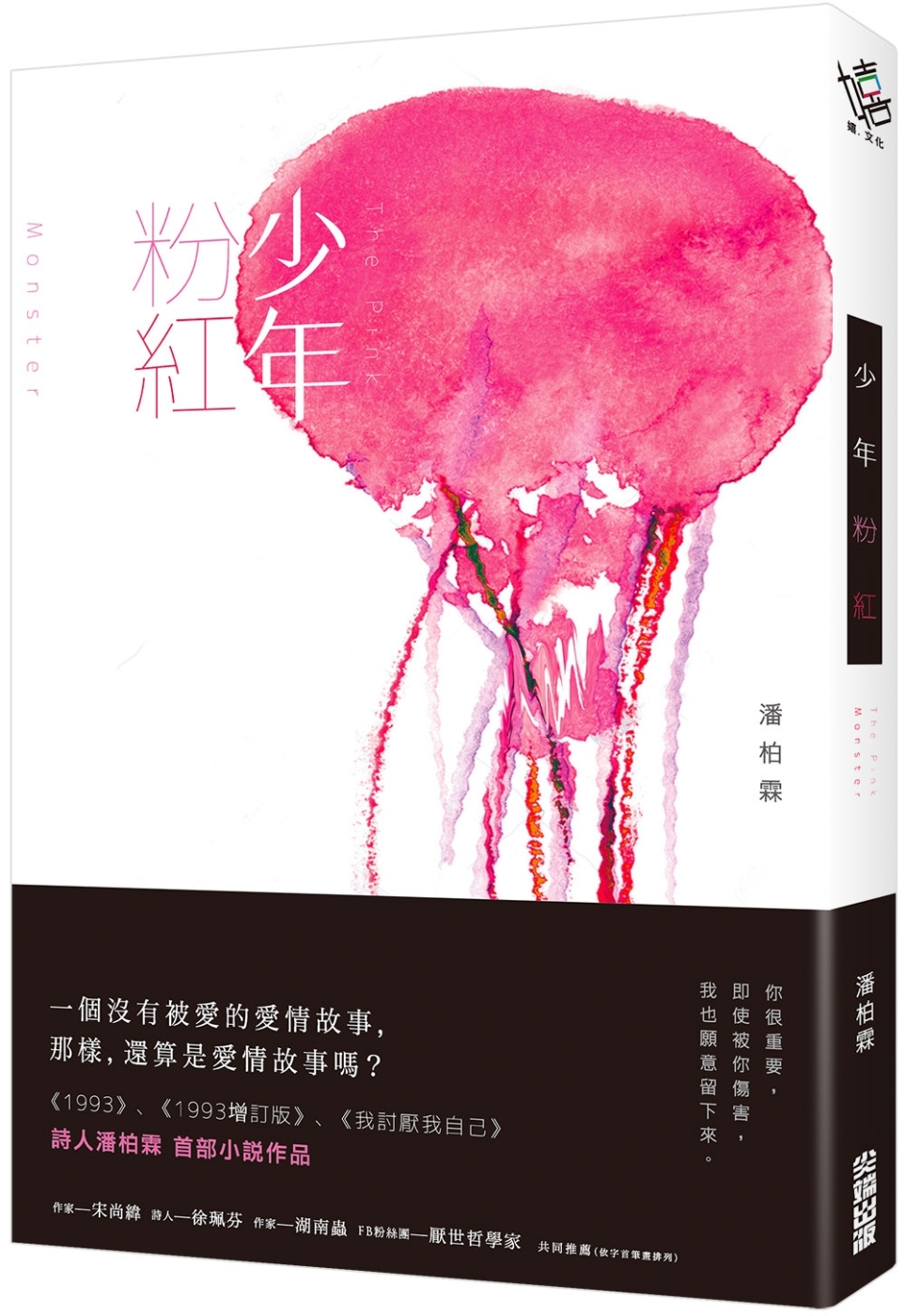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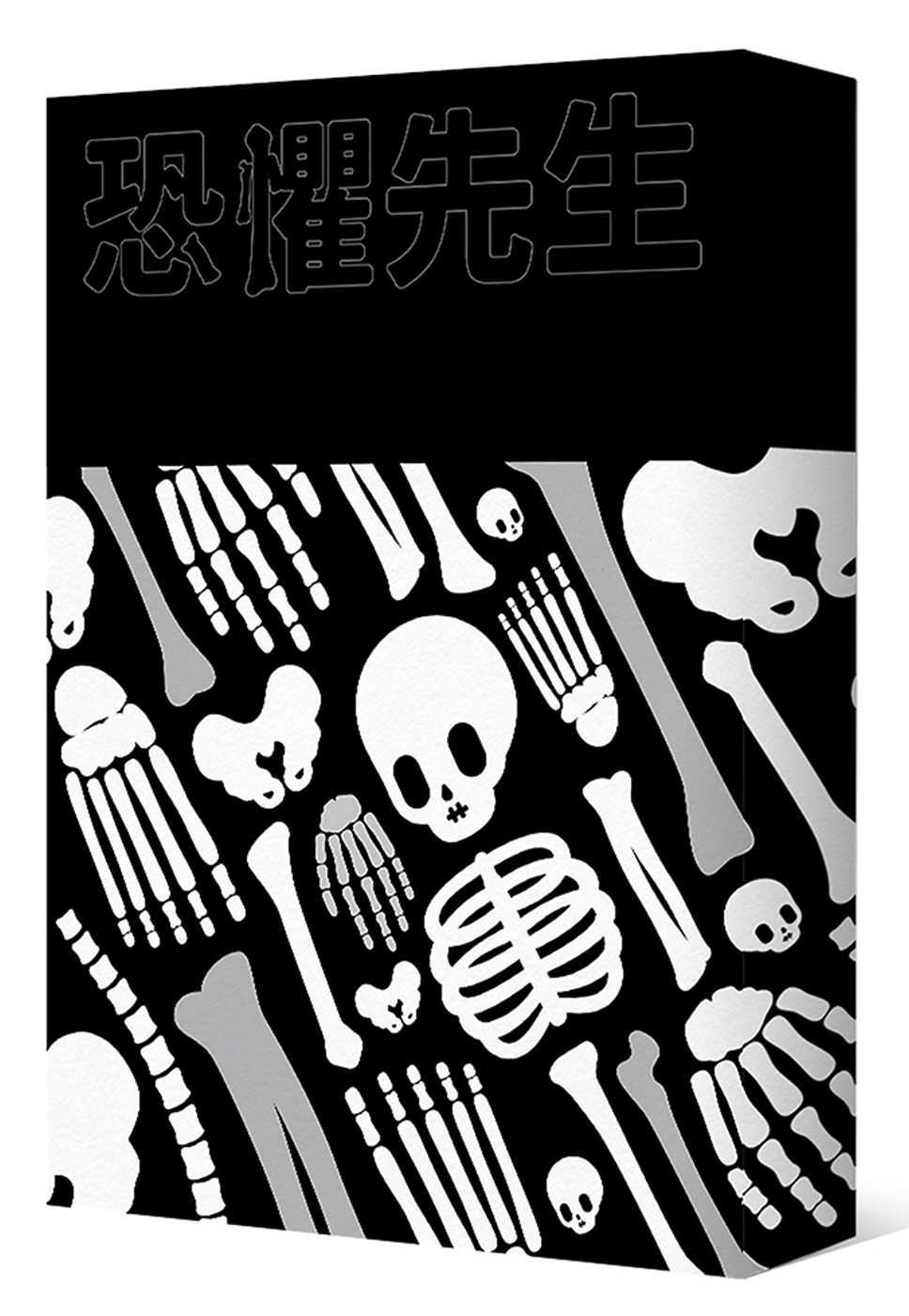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