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為全國唯一高中職奇幻文學獎,至今已經邁入第十一屆。由國立彰化高中圖書館承辦,施振榮實驗與創作基金、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協辦。本屆徵文主題希望參賽者從台灣歷史人物、台灣現代人物、台灣神話、台灣傳說、台灣歷史事件等,選擇其一為奇幻創作的對象或題材,鼓勵高中職青年學生,創作饒有台灣風格的奇幻文學。本屆刊登之貳獎作品為台中文華高中林宜臻以作家鍾理和為本發展的奇幻歷程,而叁獎為國立中興高中洪嫚均以日治時代音樂家、文學家交織的優秀作品。頒獎典禮於2019年12月24日舉行,將邀請決審委員蒞臨與參賽同學對話與交流,詳情請至http://www.chsh.chc.edu.tw/
青春大作家 ╳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 ╳貳獎:生命之花

書桌前的男人一手持筆,伏在案上神情痛苦。
咳聲與喘氣聲交織夾雜成一片密不透風的網,空氣中似乎都能嗅到那股兒躁躁擾擾的病氣。八月的天,他卻抖得如同寒冬臘月,雖如此狼狽,捏著筆的手卻仍然用力到骨節透著青白。
———
鍾台妹一踏入屋內,就見到了坐在書桌前,斜倚著牆半瞇著眼的丈夫。
「別只顧著寫,也要注意休息呀。」她動了動還泛著酸意的肩膀,走上前去整理散落一書桌的稿紙,看了看,又發現多了不少處修改的痕跡。心底無聲嘆息一聲,知道他為了寫作又不顧身體了。「去床上瞇著吧,這樣對身體不好。」
頓了頓,又道:「我知道你喜歡寫,但你最近老是睡不好……這樣下去哪受的住?」
鍾理和以拳頭抵唇暗咳了幾聲,緩緩睜開眼睛坐直身體,在書桌了一隅抽出了一封信,信紙邊緣不太平整,是閱者摩挲的痕跡,摺痕處因為多次翻閱而起了毛邊。好友鍾肇政在《聯合報》副刊連載小說<魯冰花>之時寄來此信,充滿躍躍欲試地道出了「一起長期占據這版面」的雄心壯志,希望在<魯冰花>連載完之前他能寫好新的中篇小說接續連載。
他自然是心動的。打從多年前確診結核病了之後,就沒有發生多少還能燃起他心中激情的事物;非但如此,噩耗倒是一樣樣接著來,次子立民與母親的相繼去世、龐大的醫療費用、妻子一天比一天還明顯的倦容……這都成了他心中揮散不去的陰霾。
現在有這麼一個難得的機遇,怎能放過?
他的手指在信紙邊緣來回滑動,看著好友略顯隨意的字跡,心中也慢慢泛起一些蕩氣迴腸的想望。深吸一口氣壓住那些亟欲造反的念頭,他將信沿著原來的摺痕收好,放入信封,重新收回書桌角落。
微抿著唇,鍾理和看著妻子皺起的眉間,安撫地笑了笑。
「沒事,你別擔心。這會落日正好,我去外頭走走吧。」
「也好。」鍾台妹順手將整理好的稿紙整齊置於桌面,用重物壓著,隨後向廚房走去。「別太晚啊,飯等等就好了。」
鍾理和應了一聲,稍微活動了下筋骨,站起身緩緩朝外頭走去。
外頭的夕陽比他想像的更美,像一顆有故事的琥珀石。又是霸道的地把天地萬物都染上自己藏不住的橙紅心事,卻又是小心翼翼地含住本應如同正午時分的澎湃熱情,只餘一點含蓄的餘溫。昨夜下了一場雨,因此今日的天氣不至於悶熱,拂面的清風來得恰是時候,就算有什麼煩惱,也都在這一股股南風下暫且忘卻。
三三兩兩的莊稼人扛著農具相偕回家,鍾理和走在小道上,一步步走得雖慢,卻專注無比。他喜歡這樣平凡又充滿生命力的午後。看著路邊那花、那雀、那雲、那夕日,每處都似蘊滿了靈感。
行經一片農田,忽然有人叫住了他。鍾理和停下腳步,眼神尋向聲音來處,很快便發現了那個自田中央走來的身影。「啊,進發伯,下午好。」
「哎,我和你一道走吧。」進發伯走過來,經過一整天的農務,他的臉曬得黑紅黑紅的,斗大的汗滴順著鼻梁滑落。「我剛好要去你們附近的阿勇家拿個東西。」
兩個人並肩走在路上,鍾理和好奇追問了一句,「拿東西?」
「是啊,就那把舊鋤頭。跟了我好幾年啦,一直捨不得換新的,前幾日阿勇他們家說是臨時壞了鋤頭,就來跟我借兩日。」
進發伯像是想到了什麼,嘖嘖兩聲,搖了搖頭。「說也奇怪,我這兩日雖然是用新的鋤頭,用起來居然還沒有舊的那把趁手。想說阿勇家有新鋤頭了,我還是把舊鋤頭拿回來的好,不然幹活都沒勁啦!」
「可不是?」鍾理和也笑了笑,「這東西用順手了,就換不得啦!」
「哈哈哈,對,就是這個理兒!」
他們一路上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說說笑笑的,在夕陽沒入地平線大半之時,兩人在岔路處分手,各自行走。
----
昨夜鍾理和又沒睡成,聽了一晚上的風雨聲。
夜深人靜時,總是特別多愁善感。也不知道是陽光給與了我們勇氣面對不足,還是月光太過蠱惑人心,使白晝那些藏得好好的情緒無處可躲,只能一樣樣明明白白攤在心中直視,甚至放大、扭曲。總之昨夜他心中轉過千百思緒,竟是又被擾的夜不能寐。捱到下半夜,才終於是迷迷糊糊的休息了會。
說是休息了會,其實有沒有入睡連他自己也不能肯定。只覺眼前閃過許多畫面,甚麼都來不及想,再睜眼時,不過也才過去了一兩個小時。
他就這樣睜著眼睛愣愣地望著天花板。
他無意將昨夜又失眠這件事告訴他的妻--儘管他知道平妹也不是一無所知,但她要煩惱的事已經夠多了,能少一樣是一樣吧。
躺在床上,感受身體壓在床板上的重量,鍾理和其實並不喜歡躺著,這讓他清晰的意識到自己在命運面前的無能為力。比起這個,他更喜歡坐在書桌前握著筆,沉浸在筆下的想像。
於是他順著念頭起身洗漱,打點好了自己之後在書桌前坐下,翻出昨夜妻收好的原稿,提起筆,目光望向遠方,思緒沉浸在故事中,看起來像是超然於物外,世間再無事物能分去他的注意力。筆再次落下。
忽然那剎,異變陡生。
突如其來急速墜落的失重感扼住了他的咽喉,他發不出任何聲音,腦袋什麼都來不及想,只有本能的恐懼控制住了他的四肢。可能過了一分鐘,也可能只過了一秒鐘,他沒有如所想的直接砸到地上,反而在接近地面的時候速度竟奇異地緩了下來,平緩地落地。
直到接觸到泥土,全身的細胞才如大夢初醒般,開始一個不落地反應過來,緊縮的胃、痙攣的手指、涔涔的冷汗。他伏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只覺剛死了一回都不見得有這麼刺激。
鍾理和想過很多種死法,病死、餓死、窮死,唯獨未曾考慮過從天而降摔死這件事。前幾項他自認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無論那天何時來臨都不是太意外,但摔死……他苦中作樂地想,世上哪有幾人體會過那般感覺,況且自己好歹也是保住了一條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等到身體緩過來以後,他站起身來,拍拍身上的泥塵,開始思考這究竟是哪裡。前一秒他還在家中,怎麼下一秒就到了這個地方?
想了想也不知道要怎麼證明自己不在夢中,但若要說是在夢中,那怎麼會出現這種他平生未曾經歷的失重感?況且,這種真實感簡直不像是夢啊!一花一草都清晰可辨,夢中世界會如此細緻嗎?
鍾理和原是不信神的,然而遭逢此變故,怕是也無人敢保證世上真無神佛。手上的筆是他唯一自家中帶來的物什,他仔細地放進懷中收好,若不能立即找到回家的路,也只能看著筆睹物思情了罷。他這麼突然地消失,也不知家裡人可會擔憂?
嘆了口氣,他強迫自己打起精神,弄清情況才是當務之急。左右張望了一下,這是一片林子,無論往哪個方向看都只能看見綠油油的花草樹,都是一些之前看過的植物,一切看起來都十分正常,然而怪就怪在,周圍竟無處不虛浮著紅色的格線!
鍾理和遲疑著伸出手,嘗試著去觸碰,卻發現那些格線根本沒有實體,手划過卻直接穿透過去。他心下驚懼,不敢再有動作,也不知紅線有什麼作用。正當他煩惱著要如何走出林子之時,說來倒巧,一個男子的身影自眼前快速逼近,腰一彎就靈活地縮到他身旁那道石縫中藏起身影。
「哎呀!」他還一頭霧水地看著男子之時,男子倒是一臉恨鐵不成鋼的表情,將他拖拽到石縫中一同藏身。「你怎麼還傻站在那兒呢?」
也不等鍾理和回話,他自顧自地說了起來:「外面警察在巡呢!被發現是想要來偷砍木頭的可都討不了好。」
一番話說得鍾理和又是驚又是疑。驚的是原來此處也有類似倚賴盜木維生的人家,疑的是……「你既沒帶著木頭,又怕什麼?難道他還能禁止你進山閒晃不成!」
那男人愣了半晌,一拍腦袋。「唉唷,說得也是!」
男人自石縫中走了出來,整整衣衫,帶著鍾理和從從容容地自附近一條山道下山。
「哎,多虧了你啊,我腦子不是特別好使,要不是你聰明,我們可真就白躲了一場。」
男人感慨了一聲,又問道:「老哥應該不是村裡人吧?似乎沒看過你!」
鍾理和點點頭,「是啊,我不是,我在山上迷了路,正愁著不知如何下山呢。」
「看來我今天倒是碰巧做了一回好事。」男人爽朗的笑著,「我姓程,家中排行第二,村裡人都叫我程二,老哥你也這麼叫著吧!有什麼問題儘管問我程二,山下這早溪村啊,就沒有我不知道的事兒!」
「那就先謝過了。」鍾理和心下稍安了些,能走出山林,總歸是一件好事,雖還不知歸路在何方,但又離家近了些。「我叫鍾理和。」
程二一路上嘴沒停過,自村中最近的大事講到村東村長家小孫子的抓周,這麼一路停下來,鍾理和也算是對「早溪村」的風土人情有個大概的輪廓。兩人快走到山腳時,他問出他心中藏著的疑惑。「你可知道這紅格線究竟是怎麼回事嗎?」
「紅格線?」出乎他意料之外,程二瞪大眼睛看著他疑惑道:「哪裡來的紅格線?莫不是鍾老哥眼花了?」
鍾理和抬手指著紅格線,正欲解釋之際,程二卻急急壓低聲音,打斷他的話,「老哥難道能通鬼神?」
通鬼神?在半空的手滯了滯,慢慢又放了下來。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不然如何解釋這一切發生在身上的異狀?
「這事啊,就你我知道就好。」程二小小張望了四周一下,小聲說道:「村裡的人可老不喜歡這一套神神鬼鬼的說辭啦,嚷著什麼沒看過的東西做不得數哩!」
見鍾理和點頭應下,程二也順勢把這個話題揭了過去,「鍾老哥可知道到了村裡頭後要往哪個方向走?」
「高雄美濃,你可知道要往何處去?」
「我還沒走出早溪村附近這二三個村鎮過呢,也不知道外面是怎樣的,過幾天我給你找人打聽去吧!像是村北那頭的阿關哥,十天半月都在外頭討生活,知道的東西可多著。」
說著像是想到了什麼,面露喜色,右手一握拳和左手手心相擊。「哎,你說巧不巧,阿關哥正好明天回來呢。」
鍾理和愣了愣,心裡有種不協調感,越來越濃。不過現下顯然不是思考的時候,他暫時放下滿肚子的心事,專心和程二攀談起來。
又走了一段路,已經能依稀聽見稚兒的嘻鬧聲自遠處傳來。「再有三里路就到早溪村了。」程二高興得連腳步都輕快了不少,「這聲音,一定又是周家的小丫頭們又不聽話,跑進來玩嘞!老哥等我會兒,我去把小丫頭揪出來。」語畢,向聲音來源的林子一頭紮了進去,再出來時左右手各拎了一個小女孩兒。
「嘿,好你個周大丫周二丫,不是被禁足了嗎?怎麼你們還敢出現在這兒呢!」
「程二叔,求你了,千萬不要告訴我爸媽。」其中一個小女孩兒可憐兮兮地求情。「我費了老大的勁才跑出來玩一下下,這就被你揪住了,大家都不容易,何苦為難我呢。」
另一個小女孩也附和,「就是,程二叔,如果你把我們交出去,回頭還要順道聽爸媽他們幫你介紹哪家的姑娘好,你不是聽到不想聽了麼?何苦為了我們為難自己?」
程二稍微設想了下畫面,忍不住抖了抖,啐了兩句:「去,怕了你們兩個機靈鬼了,這次就算了,趕緊回家啊。要玩在村裡玩,別跑進林子裡,你們兩個自己來多危險啊。下次再被我抓到,我可是不會再幫你們瞞著你們爸媽啊。」
「知道啦,二叔再見。」「二叔再見!二叔真是個好人!」
兩個小女孩飛也似地跑走了。「溜的倒是挺快嘛。」程二看著她們自視線範圍內消失後,轉身看向鍾理和。「鍾老哥,讓你看笑話了。」
鍾理和自怔忡中回神。「哪裡的話。」兩個女孩兒雖消失在視線裡,但因方才那幕而浮現的女兒的臉,卻遲遲沒有從心裡消失。悄悄將手探進口袋,置於其中的筆已沾染上他的體溫,離了腳下熟悉的土地,離了身邊親近的人,如同在橫無邊際的大海中漂泊,不知下一步是何處,還有多久才會靠岸,握著著筆像握著浮木一般,以來自生命深處的本能抓住救贖。
「老哥今晚沒處去的話,不如來我家過個夜吧?」程二對鍾理和的心緒起伏毫無所覺,又提議道。「我孤家寡人的,也方便些。」
「那真是太感謝了。」他道,這正是眼下要緊的事,本來還不知怎麼開口,卻是不想程二居然想到了這步。「幫了我這麼多,真不知道怎麼感謝你。」
「哈哈,平日那屋只有我一人,老哥來正好添點兒人氣,要說謝啊,也是我謝老哥才對!」
程二擺著手,表示沒放在心上。見他如此表示,鍾理和默默在心底記住了程二對他的好意,不再繼續提起。
約莫過了十分鐘,終於見到了一路被一直提起的早溪村。和程二方才形容的別無二致,這是一個依著山腳而建的村落,一塊一塊的田地錯落其中,孩子們在田壠上奔跑,偶有摔一跤的,也不甚在意;女人們則提著籃子,趕著為自己家下田耕作的人送去飯食;農人則是不得不暫避毒辣的太陽,到樹蔭下吃著中飯,喝喝茶,看著田中結實的麥穗笑得滿足。
好一個避世桃花源的景象。
程二人緣極好,一路走來,不少人看到他都會笑著和他打招呼,「程二,我家狗最近生了幾隻幼崽,回頭給你拿去啊!」「程二,我家昨天剛宰了一頭豬,多了些邊角肉,你拿去吧。」「程二……」
「好咧,謝謝啊大樹伯,改天我送你幾斤雜糧。」「張伯,不用啦,你拿去吃吧,你家裡還有兩小子,正是饞嘴的時候呢。」「李伯……」程二一一應答,還順道帶著他認識了一些鄉里間熱心的叔伯。
「正國伯,阿關哥明天回來嗎?」正國伯是阿關哥的爸爸,程二在路上恰好遇見了他,便向他探聽阿關的蹤跡。
「是哩,這個月早了十天回來,也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麼。這孩子,遇到事兒就只會回家。」嘴上雖然嫌棄著,但看得出來,哪有不期待兒子歸家的父母呢。
「怎麼會,阿關哥這定是想你啦!」程二也知道,沒把話語表面上的嫌棄認真看待。「我旁邊這位鍾大哥有事想找阿關哥探聽呢!」
正國伯看了看鍾理和,乾脆地點點頭,「這樣啊,行,他回來的時候我去通知你吧。」
「那就謝謝正國伯啦!」
程二將鍾理和帶回家,他整理了一間客房出來,有床有被,然而整個房間顯得太過簡陋——可能是因為只有一個主人。「有缺什麼的話再告訴我啊。」程二也是明白他一個男人自己住,肯定有準備的不妥貼的地方。
「哪有這麼多講究,這樣就足夠了,謝謝。」
「那我出去會兒,說好了今天幫阿樹伯家幫忙的。」程二轉身又要出門。出門前又不太放心地和他說道:「把這裡當自己家,別拘著。出去在村裡走走也不錯,大家都是好人。」
「行吧,我知道了。」也許程二就是因為這副熱心腸,才有這般好人緣吧,也幸好自己遇到的是他。鍾理和想。
見到鍾理和應下,程二才放心地轉身出門。
雖然是應了程二,但鍾理和沒有打算真的出去晃晃。相反,他倚在牆邊,盯著那無處不在的紅格線出神。通鬼神並不能解釋這紅線給他的熟悉感,到底是什麼呢?必定是一個他熟悉、又不容易注意到的東西……
咚、咚,兩聲自窗戶外傳來的聲響將他嚇了一跳,思緒中斷。他開了窗戶想瞧個究竟,這一開,就看到對面人家的窗後有一個滿頭白髮、精神科矍鑠的老人,他的手上又握著一顆小石頭,抬手欲丟。
「哎呀,我以為是程二家遭小偷了,原來是客人呀。」老人家放下手中的小石頭,倚在窗邊,笑咪咪對鍾理和說。「小伙子讀過書?看起來有讀書人的氣質。」
「的確是讀過幾年。」
老人嘆到,「唉,幸福的小伙子唷。以前小時候家裡窮,從來沒指望過認字兒,現在到了這把年紀啊,現在倒是越發稀奇了起來。」
「老人家,讀書怎麼都不嫌晚的。」鍾理和勸慰了句,「一點一點認總是能學會的。」
老人哈哈大笑兩聲,「小伙子懂得倒是不少。」他自懷裡取出了一封信,遞給鍾理和。「這是我老婆過世的時候寫給我的,她認識很多很多字,大家都說她能看上不知道是修了幾輩子的福氣。」
「可我不爭氣,看不懂,村裡人認識字的又少。小伙子你既然識字,那能幫我唸唸嗎?」
他心中一軟,探出身接過那張信紙,只瞧一眼便愣住了。但他捺住心情,只一字一字地唸出信中的內容,滿足了老人不知多少年的念想。
「謝謝你啊,小伙子。」老人從鍾理和手中接過信,眼眶中隱隱約約泛著淚光。
「哪裡的話。」
他關上窗子,在心中默默感謝著老人。他想起來了。紅格線到底是什麼。
鍾理和返身坐在床沿,靜靜注視著周圍一切色彩漸漸淡去、轉白,身體湧上一陣熟悉但真實的虛弱感。這裡只剩他自己,還有那紅色格線。「果然,這是我筆下的世界啊。」
「你怎麼發現的?」
虛空中顯出一道身影。一張雌雄莫辨的臉孔給人一種感覺,好像性別、五官、美醜對他來說都不重要,他就是純粹的他。
「太巧了。」鍾理和閉上眼睛,從頭回想,慢慢梳理著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在我需要出山的時候,程二出現了;在我需要知道這裡是哪裡時,程二自動就說出口了;在我要探聽哪裡可以到美濃時,村裡可以探聽的阿關哥也『正好』回來了。我需要什麼,東西就會自動以各種形式到我手上。」
「如果說這都是巧合……那還有地方解釋不通。」
「像是,為什麼早溪村與山上的花草樹木都是我熟知的那些?還有來到這個地方之後,我就沒感受到病情對我的影響。」他握握拳頭,「可是照我來到這裡的那種摔落的驚駭來看,不可能一點反應都沒有的,怎麼可能只緩了下,就能行走如常?」
「不過,最重要的是……」抬頭看了看那虛浮的紅格線,他笑,「雖剛開始沒有意識到,但不可能認不出來的。」
「那是稿紙的格線呀!」
人影靜默半晌,走到他身前盤腿坐了下來。低垂著頭,看不清神色。「你相信世間萬物皆有靈嗎?」他道,聲音裡面只有純粹的平靜,慢慢悠悠,像是遠方的炊煙。「你有沒有那一兩次能夠感覺到物品和你心靈相通的時刻?」
鍾理和突然就想起了進發伯的那根舊鋤頭;想起了在夕陽下,進發伯無奈地笑笑,說道:說也奇怪,我這兩日雖然是用新的鋤頭,用起來居然還沒有舊的那把趁手。
「我信。」他點點頭。
「我是這樣一種存在。就是你手上那隻筆的靈,是你持續不斷的寫作給了我生命。」
「每一次的寫作、每一次的持筆,都會殘存你一部份的精魄在在作品中──唯有靈魂在其中的作品才會動人,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如今如此病弱。」
「但,你的身體已經沒辦法支撐你下一次提筆了。再一次,你就會消亡。」
「你不要再寫了。」他說,語氣帶著點懇求的意味。
「所以這是你把我帶入這裡的理由?」鍾理和問,而筆靈點頭。「對,這樣你就不會再有提筆寫作的可能了。」
「可其實,也有一部分的你是希望我繼續寫的吧。」這並不是疑問句,而是直述句。「你本來可以消除格線的存在的,這樣我就永遠猜不到真相。但為什麼你把它留下來了?」
筆靈驚詫地抬起頭,直直望入鍾理和的雙眼深處,隨後又頹喪地垂下去。「我沒有辦法。只有你寫,我才有存在的意義。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沒辦法啊……」
「我沒辦法看著你就這樣因為文學而死啊。」它有些絕望地將臉埋在雙掌中,「你給我了生命,我卻回報你死亡。」
看著此刻的筆靈,鍾理和回憶起自己曾經給好友廖清秀寫過的一封信。
「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一段時間獻給文藝,連健康也為它而毀壞了,試問我如何能甘心於此?說真心話,如果我即此而死,那麼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我是不可能不再提筆的。」就算不提筆,失去的健康也回不來,也依然還是看老天臉色,冀望它給我一條活路。他其實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想像過這一天的來臨了。這並不意外。早來,是死;遲來,也依舊是死。人生只是一條單行道罷了,他更在意的,是在死之前能不能完成他的理想。
如果要在「戒除文學苟延殘喘」與「向文藝獻上自己生命的終曲」之間做抉擇……
「倒不如,就讓我死在文學上,活在文學裡吧。」
話音一落,裂紋自角落以極快的速度向整個空間蔓延,大塊大塊的崩解成細碎的粉末,逸散在空中。鍾理和穩穩的佇立其中,表情平和看著整個小世界的崩塌。
空間的碎裂只花了短短數秒,從小世界回到現實,這次沒有墜落,也沒有不知所措。現實似乎只過去了不到一小時。但……
他已經準備好了,對於死亡這個必然的走向。
1960年,8月4日
書桌前的男人一手持筆,伏在案上神情痛苦。
咳聲與喘氣聲交織夾雜成一片密不透風的網,空氣中似乎都能嗅到那股兒躁躁擾擾的病氣。八月的天,他卻抖得如同寒冬臘月,雖如此狼狽,捏著筆的手卻仍然用力到骨節透著青白。
就像是用盡生命的最後一握。艱難,但比艱難更鮮明的,是堅定。
他咳得彷彿要把肺一起咳出來,咳著咳著,暗紅色的血絲自喉頭湧出,血色順著紙張的纖維擴散暈染,匯流到了一筆一劃刻下的字跡那淺淺的凹槽。
鮮血在稿紙上開出了一朵,永恆的生命之花。
作者簡介
林宜臻

來自臺中,身為距離學測只剩50天的學測戰士,目前最大的心願是不要成為指考戰士。
閱讀是整個人生中堅持最久的事。大家似乎都有這種當閱讀到了一定數量的時候就會產生精神空虛,開始動手寫文滿足自己的情況。我也是自給自足的其中一員,最初動筆的動機就是滿足自己。最喜歡的、也是最一開始接觸的種類是輕小說,從御我的書開始,後來一路接觸武俠、翻譯小說、推理、古文、科普文學、言情……基本上只要是中文都嗑得下去。
堅持第二久的是跆拳道,跆拳道真的很讚,有很多人說跆拳跟文學好像不沾邊,這完全就是謬論,他們倆個有個共通點就是都抒發情緒啊。跆拳道加文學才是最強的組合好嗎!心情好寫作,心情不好踢沙包,生活沒煩惱。
得獎感言
寫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各種小說,真正往外投稿也不過是最近一年的事。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到哪裡,一開始的期望甚至沒有這麼高,想說是個佳作那也很安慰了,沒想到名單公布之後,出乎意料拿了比預想中高上許多的名次。謝謝各位評審給予的肯定,今天的獲獎,給了我勇氣,知道在創作這件事上老天終究或多或少還是賞了我一口飯吃。
在學校網頁發現比賽後,便一直在關注,然而靈感搞失蹤,在截稿前三個禮拜,甚至連構思都沒有。直至某天上國文課神遊天外在想題材之時,乍然聽到「字裡行間」四個字,真是一場及時雨,剎那間浮現了關於第一版的構思──如果有個作家,被困在自己的字裡行間出不來了呢?
能擁有這次的殊榮,有很多想感謝的人。感謝班導兼國文科老師蘇嫈雱老師,除了幫我送來了靈感之外,由於寫作龜速,導致時間緊迫僅只幾個小時就要定案,老師居然願意百忙中抽空配合我修稿,使作品更完整。還有我的父母,雖然一開始他們其實有點擔心讀書與徵稿時間上的衝突,但後來尊重我的決定,還幫了我很多忙,諸如印刷、送件等等。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就算寫得出來,也不可能來的及交件。
自己的作品上有許多不足之處是顯而易見的。今天有幸拿到一張入場券,接下來,路還很長。
看更多得獎作品
1.【青春大作家X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参獎:飄渺之輩
2.【青春大作家X織錦文學獎】小說首獎:保鮮膜
3.【青春大作家X第21屆馭墨三城文學獎】小說組:貓與愛麗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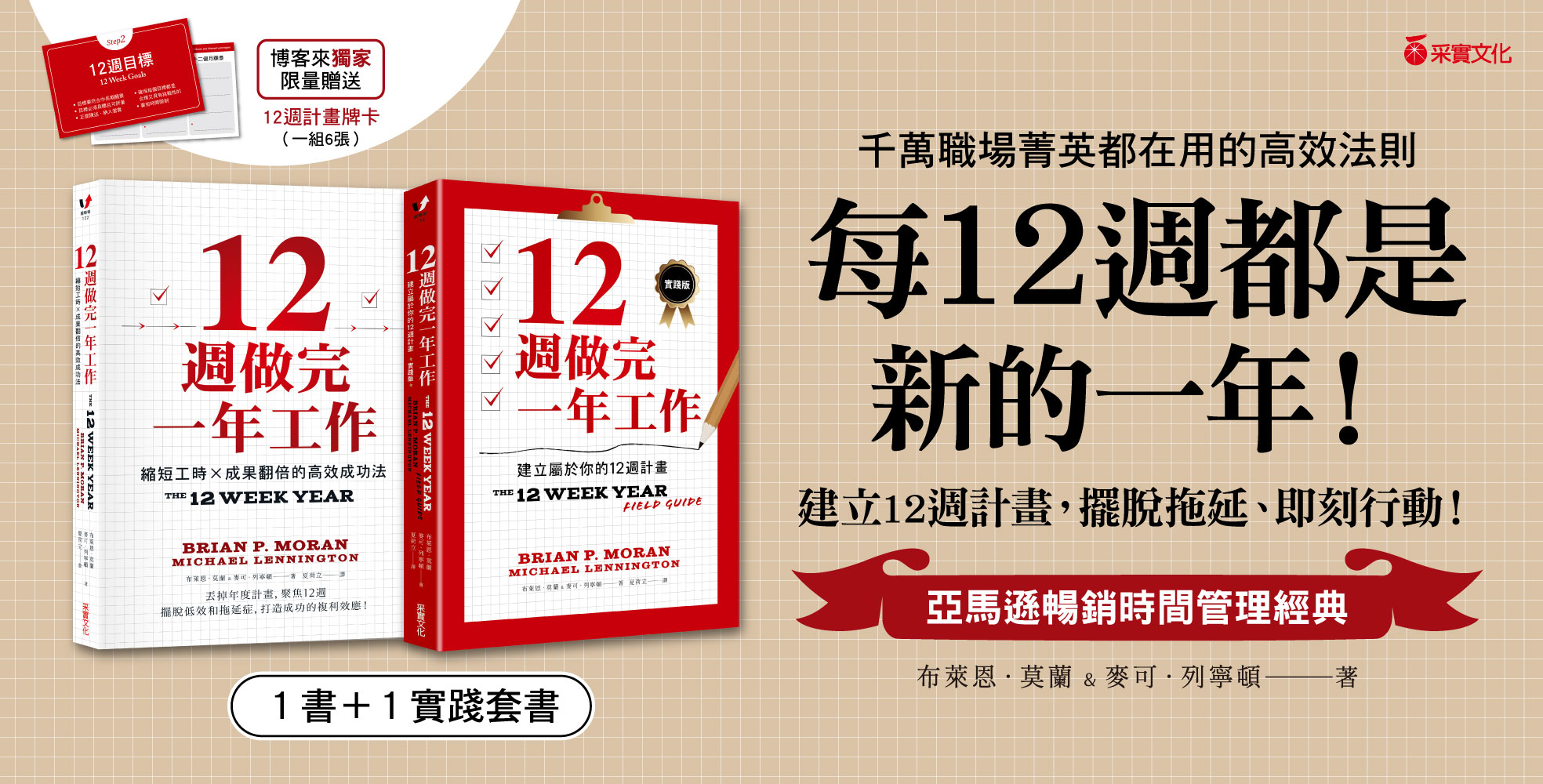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