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9臺北文學季壓軸亮點,國際華文作家系列活動,請來嚴歌苓女士,她闊別台北11年後,再度訪台,於國家圖書館安排,由重量級主持人蔡詩萍主持,並邀請另一位女性小說家平路,三人針對小說中虛構與現實的創作理念,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精采分享對談,全場近三百位讀者,一起浸潤在文學世界裡多樣化的人生苦難與甘美。會後讀者大排長隊請嚴歌苓簽名合影,讓人感受文學魅力不減,好的作品永遠會得到共鳴。
 (左)蔡詩萍、(中)平路、(右)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左)蔡詩萍、(中)平路、(右)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跨過虛構跟真實之間
嚴歌苓:
我覺得對小說家來說,能走多遠,就是看個人虛構能力能帶他走多遠,我過去講過一句話,很多藝術作品好,是依賴人們記憶的不可靠性,意思是,當我在寫童年故事時,實際上已經離真實記憶很遠了,因為隨生活閱歷,每個人的記憶在自己的提存凝鍊下,最後成為一種意象式記憶。
打個比方,文革發生時我只有七歲,當時自殺的人很多,那時我聽說一對老夫婦從樓上跳下來,我就跑去看,等我到時人已經被搬走了,只在冬青樹的泥土上砸出了兩個坑,當我經過那棟樓底下時,看見樓頂不斷飄下很多五顏六色的玻璃糖紙。那時候糖是很難買到的,我就在腦海中想像,老夫婦倆決定結束生命,坐在樓頂吃掉所能買到的所有糖,談倆人一輩子的事。在他們跳下來後的每一天,只要一有風,糖紙就從樓頂吹下來,就像蝴蝶在晚霞裡飛舞。
這件事隨著我長大,我看到的已不是恐怖與驚悚,我認為這是個「化蝶」的故事,是一對老夫婦的愛情,飄飛糖紙就是化蝶後的他們,我覺得這是他們的靈魂。所以直到現在,當我寫這段記憶時它已完全抽象了,肯定跟當時真實記憶很不一樣,我肯定已經多次編輯記憶,所以我看到的確實是讓我記憶下來的事,但在時間不斷過濾和提存凝鍊中,它成了化蝶的愛情果實。我覺得這就是虛構給我的能力吧!可以把一個恐怖事件變成美麗的愛情意象。
 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嚴歌苓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蔡詩萍:
最簡單的描述可能最寫實,直接講說死了以後的事,確實能造成很大的震撼與一定的殺傷力,但這樣的震撼到一個程度就會停止,所以,有時虛構的震撼度可能比寫實更驚人,因為它是經過某些轉折跟想像後,讓你驚覺,原來生命的苦難可以有這樣不同的層面。
若有所悟的瞬間
平路:
對我來講,寫小說是某種意義上的特權,那特權就是能進入每個角色的內在世界,但內在世界看到的真實和寫出來的內容會有很多虛線,因為是虛線,所以對小說作者來講就更有趣了。我一直相信小說如果有個精神在後面的話,那就是一個問號,事情可能跟表面所見不同,問號就是──到底你的角色在想什麼?
探討的同時,身為小說作者的你有機會去想像,進入每個人內心世界,把這些拼圖完整拼湊。如果在虛線中小說作者努力呈現的是問號,那請問真實是什麼?如果記憶不可靠,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這樣的推移中,小說家想要做的也許是「女媧補天」,試圖把真實全面鉤織,像打毛線般拆了又織,織了又拆。
這其中反映的,是我漸漸對這整件事,還有包括自己的成長與對外在世界的理解。它既虛構也真實,因為它同時把虛線中,包括自己對記憶的疑惑,與當時歷史記載的縫隙,和那些歷史記載所有的主客觀拼在一起了,使我更了解自己,而這也是文字或文學的功能吧!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許多的社會功能,但在文字神祕的連線中,它所能觸動的是讀者的內心世界,在某個時刻,讀者跟作者都「若有所悟」,這瞬間既真實也虛構,如同做夢一般,又在若有所夢的瞬間得到啟示。
這樣的啟示對我非常重要,也是支撐我,只要有一點力氣時間就願意持續寫下去的動力,因為它無窮無盡、有無限可能。身為作者,如果在某個機緣碰到讀者也在神秘連線的另一端若有所悟時,那真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平路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平路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徒勞,是小說家宿命嗎?
嚴歌苓:
儘管沒有完全感到「徒勞」,但也會覺得無力,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暗示,小說裡的人物都在暗示某種東西,我不知讀者們能接收這些「暗示」至何種程度,所以有時會想,「真有人懂嗎?」這時就會讓我感到無力。我的暗示其實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因為要講的東西在我心裡也常是混沌的,如果你知道我要寫什麼,知道訊息是什麼,那就變成說教,所以,一定得「朦朧」至某種程度才是藝術。
寫小說,是我自己還不清楚想暗示什麼,但如果對方能解讀,告訴我從故事裡看見什麼,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頓悟,會有一種「噢!原來我寫的是這啊!」而這是我必須一直寫下去的重要動力,因為我能把朦朧的創作,在讀者或評論家的欣賞下,疏通這些朦朧暗示,我覺得,這是身為小說家的一個嗨點。
平路:
小說作者當然在尋找對自己有意義的意義,對我來講,剛才提到內在啟示的部分,尋找意義對作者跟讀者的連線來說,有點像我一直在問:「有人聽見嗎?」而我聽見最能感動讀者的部分,一定跟讀者某種內在心境或過去經歷有共通處,才能在那一刻彼此「心領神會」,雖這不是直接相扣,但因文學充滿隱喻,有它模糊地帶,有連作者自身都不那麼清楚的部分,然而,就是這樣才有藝術的力量,如同深夜裡有人不斷在問:「有人聽見嗎?」然後,另一端,在某個不管隔著多遙遠的時空,另一個人若有所悟了,雙方產生感應,那感覺如同「天啟」。
如果說這是歌苓剛才提到的「嗨點」,那我覺得,這甚至是種當你知道自己寫到這麼酣暢時,並且是用全部心力,準確將心裡真正感受,透過文字媒介傳遞出去時,我相信,一定在某個時刻某個角落,就算根本不知道那個地方那個人是誰,但那一句:「有人聽見嗎?」確確實實存在。我想,這就是作者為什麼彷彿徒勞,但依然要寫下去的原因。
以閱讀開闢一條新道路
 蔡詩萍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蔡詩萍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蔡詩萍:
「有人聽見嗎?」我想是所有寫作人都期望得到的回應,現在這年代,藝術與創作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永遠拒絕貼標籤,永遠在善惡是非分明的世界裡,開出一條新路。兩位認為,為什麼要花時間讀小說呢?
嚴歌苓:
我讀小說是在讀文字,我讀很多小說是因為文字好,我把對文字的審美和文字,視為表達的重要工具,文字如果不好、不美,把文字寫得一塌糊塗,就算小說內容好看,我還是看不下去,一定要文字寫得獨到才行。每個人對文字的貢獻或文字的再造追求程度不同,但這是我最追求的,所以不謹是讀小說,我每天還要讀宋詞、唐詩等等,免除自己寫出糟糕的文字。
平路:
我覺得這年代讀小說,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我們需要更理解自己、理解別人,和所愛的人。我認為只有小說的形式才能把人心的幽微處寫得動人,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小說是一種勾織過程,透過這過程使我們知道原來理解他人有多困難,或至少知道其中的困難度,才不會覺得所有事都能一蹴可幾。當我們知道困難,也才能找到密道,找到進去的路線,才能開始試圖理解,並認知自己的理解程度其實只是皮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現實功能,如果沒有小說,我一定是個比現在的我更差的人,可能是個沒包容心跟同理心的人,而小說讓我能真正理解原來人是這樣,原來對方有其苦衷,每個人都有難處。
藉由讀小說,我讓自己每天無論跟誰相處,都能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在互動中也能更加了解自己。我發現讓我「起心動念」的後面是什麼,或原來這可能跟我的某種經歷有關。所以那些我害怕的或我擔心的事情,就有機會一一解開了,發現自己害怕或擔心的事,可能不只是表面看見,而是另有原因,因此,對我來說這是個機會,讓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比昨天更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點的人。
2019臺北文學季在「國際華文作家」嚴歌苓訪台的活動中劃上完美句點,七月號《文訊雜誌》,將有更多嚴歌苓相關延伸專訪,敬請期待。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攝影:吳景騰 資料提供:文訊雜誌 / 台北文學季
延伸閱讀
• 2019年台北文學季講座紀實—林立青X房慧真「親愛的臺北異鄉人們」
• 2019年台北文學季講座紀實—陳雪 Χ 邵祺邁「書寫同婚後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2019年台北文學季講座紀實—李偉文 Χ 吳曉樂「轉動的閱讀時光」
• 2019年台北文學季講座紀實—蘇偉貞 Χ 神小風「那些年,我們共享的租書店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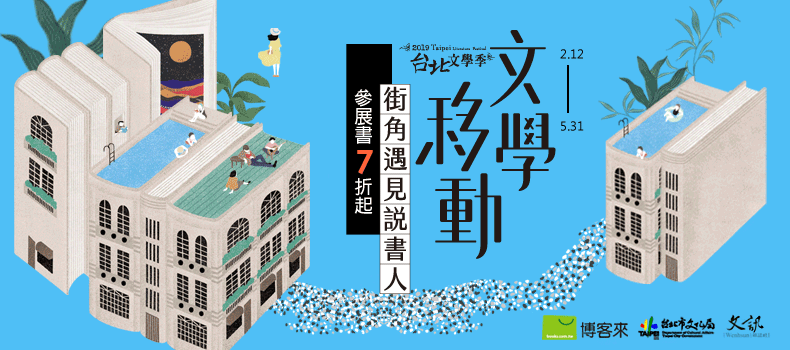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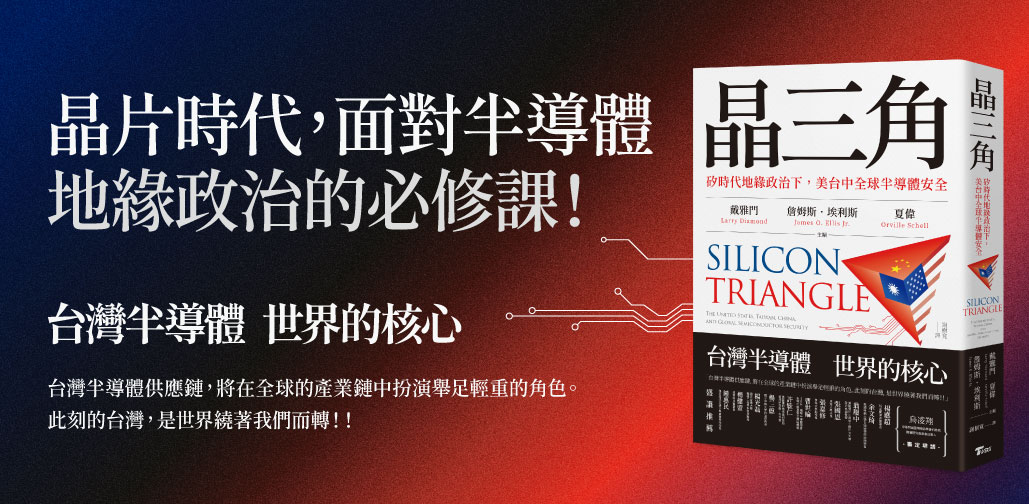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