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工作」的誕生有如一段傳奇故事。人類學界的祖師爺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初步蘭群島做研究,原本只是短期停留,卻因一戰爆發被迫留在當地,他不得不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學習語言、參與觀察。他的研究不僅走出書房,前往異地,長期在異地的生活更深化了他的研究。1922年,他以這些經歷出版的第一本書《南海舡人》成為人類學經典,「田野工作」也成為人類學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核心。
2006年,人類學者郭佩宜與社會學者王宏仁共同主編《田野的技藝》一書,他們有感於當時台灣幾乎沒有討論田野工作的本土著作,於是邀集十位學者,以「說故事」的方式檢視研究歷程,撇下說理與論述,道出自己在田野中的掙扎、焦慮、喜悅和領悟。本書推出後廣受迴響,成了學院中的教科書,也經常被引用和討論。13年後,《田野的技藝》終於再版,且換上新裝。此外,原班人馬加上新血的姊妹作《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也隨之出版,繽紛的封面插畫充分表露進入田野工作的包山入海、人與動植物們的混聲交纏。
《辶反田野》的主編之一、交大人文社會系副教授蔡晏霖笑稱,當年《田野的技藝》出版時,正在美國攻讀人類學博士的她也讀了,最受用的文章之一便是當年主編、現任職中研院民族所的郭佩宜寫的〈我不是「白人」:一個人類學家的難題〉,郭佩宜點出:所羅門群島當地住民向來稱外來者為「白人」,而且是具有政經權力優勢的外來者。那麼,身為一個「非白人」研究者,她該如何突破種種屏障在那裡進行田野?又該如何向當地人解釋自己的身分?
當時,蔡晏霖亦在苦惱田野對象,這篇文章給了她肯定的力量:當一名第三世界的學者選擇田野地時,為何不能選擇另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孰料,十多年後蔡晏霖已在學院裡執教,成為郭佩宜的同業,甚而,被成功推坑,擔任《辶反田野》的主編。
延續《田野的技藝》的說故事基調,《辶反田野》再次端出十篇人類學田野故事,與前作最大的差異是,這批在學術機構闖蕩多年的學者們已進入了新的田野階段,郭佩宜解釋,「人生在不同階段可能會對田野有不同的想像,我也好奇大家是怎麼想的,」蔡晏霖接著補充,「有了全職工作後,我們只能在零碎的時間進行田野,這給田野工作帶來很多限制和可能,也和古典人類學的範式與要求非常不同。我們都很好奇,大家如何處理這些限制和焦慮?」
《辶反田野》所收錄的文章,呈現了難以被寫進教科書的田野歷程與反思,郭佩宜說,「我們都不想因為現實的忙碌狀態,而把淺薄、快速的田野工作合理化。」他們無意捍衛如何做田野才算「正統」,核心的提問其實是:人類學的田野特質是什麼?他們發現,《辶反田野》每篇文章皆程度不一地給出答案,「我們就算只能在零碎時間進行田野工作,仍是要長期且深入地進入日常生活的縫隙,把田野本身當作目的,浸淫式地參與。我們不輕易簡化田野,也不預設田野的目的。」
書名「辶反田野」也具現了田野工作難以捉摸的動態感,拆解「返」字,「辶」有忽走忽停的流動意涵,傳達「反」與「返」的時間差或重疊交錯的可能。本書特別指出田野工作中獨特的「時間感」,蔡晏霖說,「人類學就是嘗試體會眼前不同的報導人的生命韻律,透過長時間的等待、調節與適應,覺察眼前的現象如何/為何生成。」
例如,蔡晏霖的文章便記錄她怎樣在宜蘭的小農社群進行田野工作。她以拍攝紀錄的方式,邀請田周生物(福壽螺、鴨子、狗兒)一同報導,進行一場「多物種民族誌」,她的提問是:農人與福壽螺該如何相處才算和平永續?想當然爾,她的田野對象比人類更難控制,在等待與撤守的過程中,她參透出一種違背進步與績效原則的田野時間觀,她寫道:「在此,所謂的『參與』不是某種可以被量化的時間積累或按表操課,而是田野工作者與被研究對象彼此關係的『全面化』與密實化,……人類學的田野時間既是注重『給彼此時間』的田野認識論,也是一種努力關照不同生命節奏,嘗試讓更多不同人與非人互相調適與共同繁盛的倫理觀。」

蔡晏霖與她的田野夥伴──福壽螺。(照片提供 / 蔡晏霖)

郭佩宜在所羅門群島的田野地。(照片提供 / 郭佩宜)
《辶反田野》雖是合集,成書過程並非主編收完稿件就了事,這本書從發想到出版,共經歷三次工作坊,籌備期超過一年。其中,第三次的工作坊承接了當初《田野的技藝》做法,作者們聚起來關在民宿裡,大家攤開初稿,逐一對決,進行兩天一夜的駁火討論。
郭佩宜分析這場密集討論對於成書的關鍵意義,「一是,同儕的討論與回饋,給了寫作者修改的靈感;二是,你在別人的文章裡會看見自己類似的經驗,每個文章不再只是一個單篇,而是能夠對話、互動,也讓大家一起變強;第三,這過程其實也是一種療癒,每個人在田野裡都有很多困惑、焦慮和自我質疑,因為全身投入,所以也容易受傷。大家都是同行,年紀也差不多,只要坦露一點點,對方馬上聽懂,且能接住。」
蔡晏霖也說,「我們很努力幫助彼此肯認了在田野過程中自己都沒辦法那麼肯定的價值,並探索人類學這份工作的公共意義。這是學術之路上少有的珍貴經驗。」
回到學院,《田野的技藝》與《辶反田野》雖是普及讀物,對學生而言卻是重要參照,這群本身帶著反叛性格的老師們想提供的,並非「如何做田野」的教戰手冊,而是透過親身體驗,協助正在摸索田野之路的新生代一些可能的方向。尤其,儘管這些老師從事田野工作數十年,他們的疑惑與焦慮並不比學生少。蔡晏霖說,「我們想讓學生知道,田野工作沒有SOP,也無法『標準化』。這其實是整個時代的共同焦慮──當我們認為『標準化』才能代表『品質保證』,這樣的連結讓人焦慮。」
那麼,一般讀者能從這兩本書獲得什麼呢?
蔡晏霖認為,「田野」雖然好像是一套學術方法,但已不再是人類學的專利,「對我來說,田野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生活中可以允許混亂,並容納各種雜質或噪音,學習與之共存。」郭佩宜則認為,「這兩本書的故事有趣而真誠,能讓一般讀者理解所謂『做田野』到底是什麼。」有趣的是,學者出書通常是從內挖掘智識貢獻社會,他們卻反而在這過程中收穫更多,「我在工作坊中得到對於田野的新理解:田野不只是學術工具,更應該是生活的態度與目的。」蔡晏霖說。
是以,《田野的技藝》與《辶反田野》與這兩本書寫的雖然是人類學家的日常生活,卻也隱隱提示,那也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自我照顧、照顧他者,與人或非人建立關係,友善共生。他們相信,這就是今日世界極需的力量。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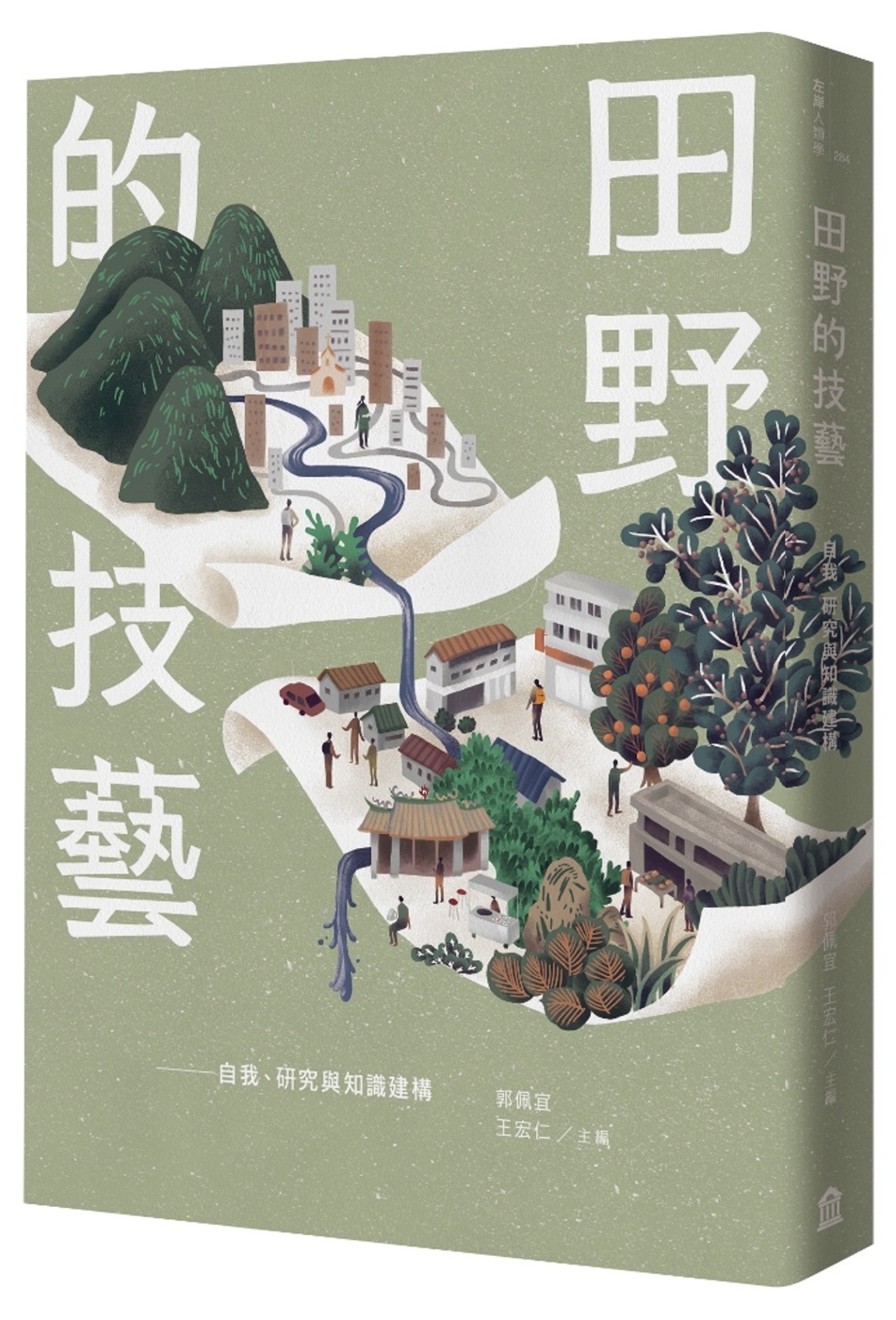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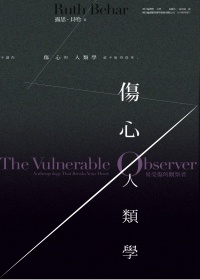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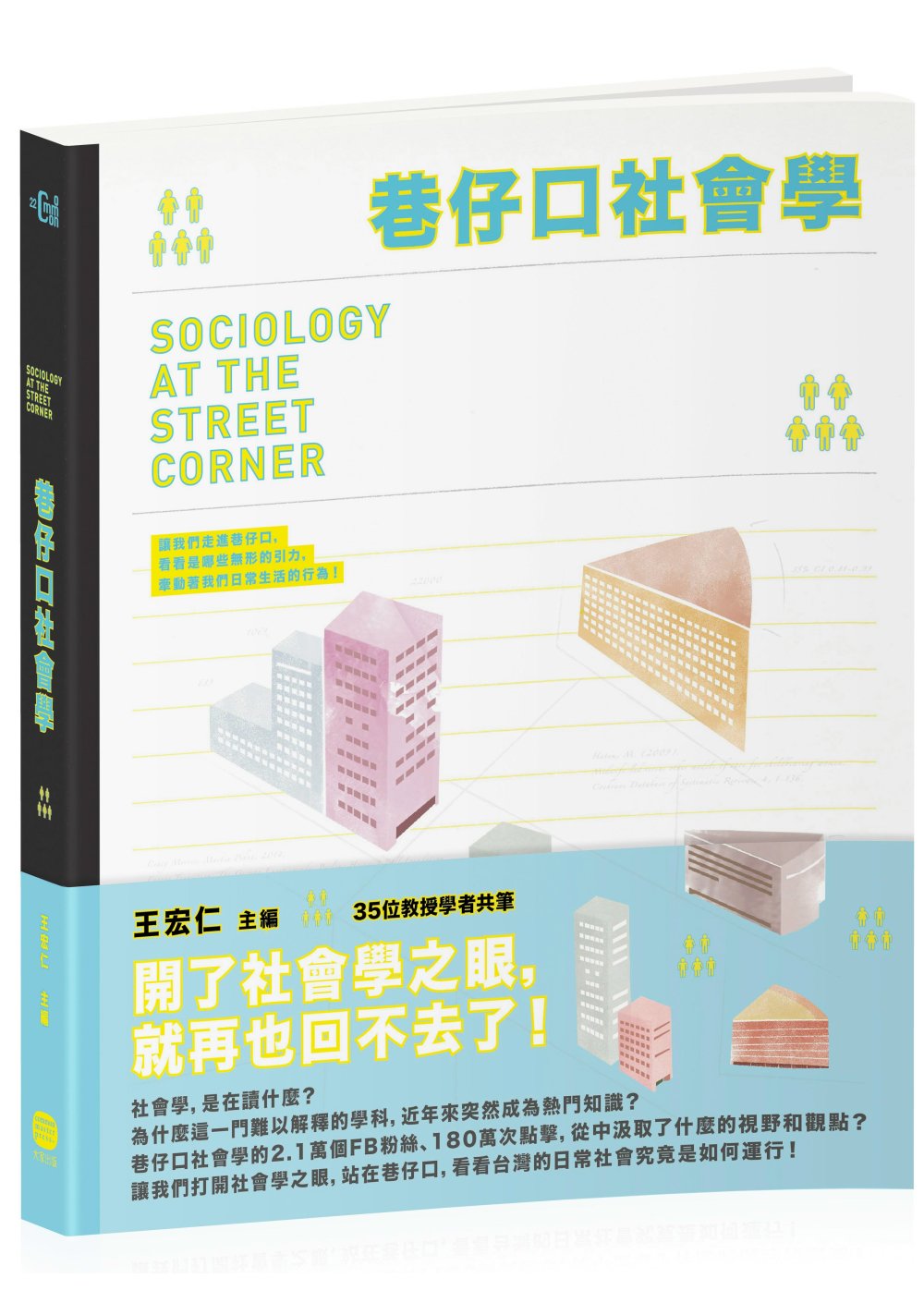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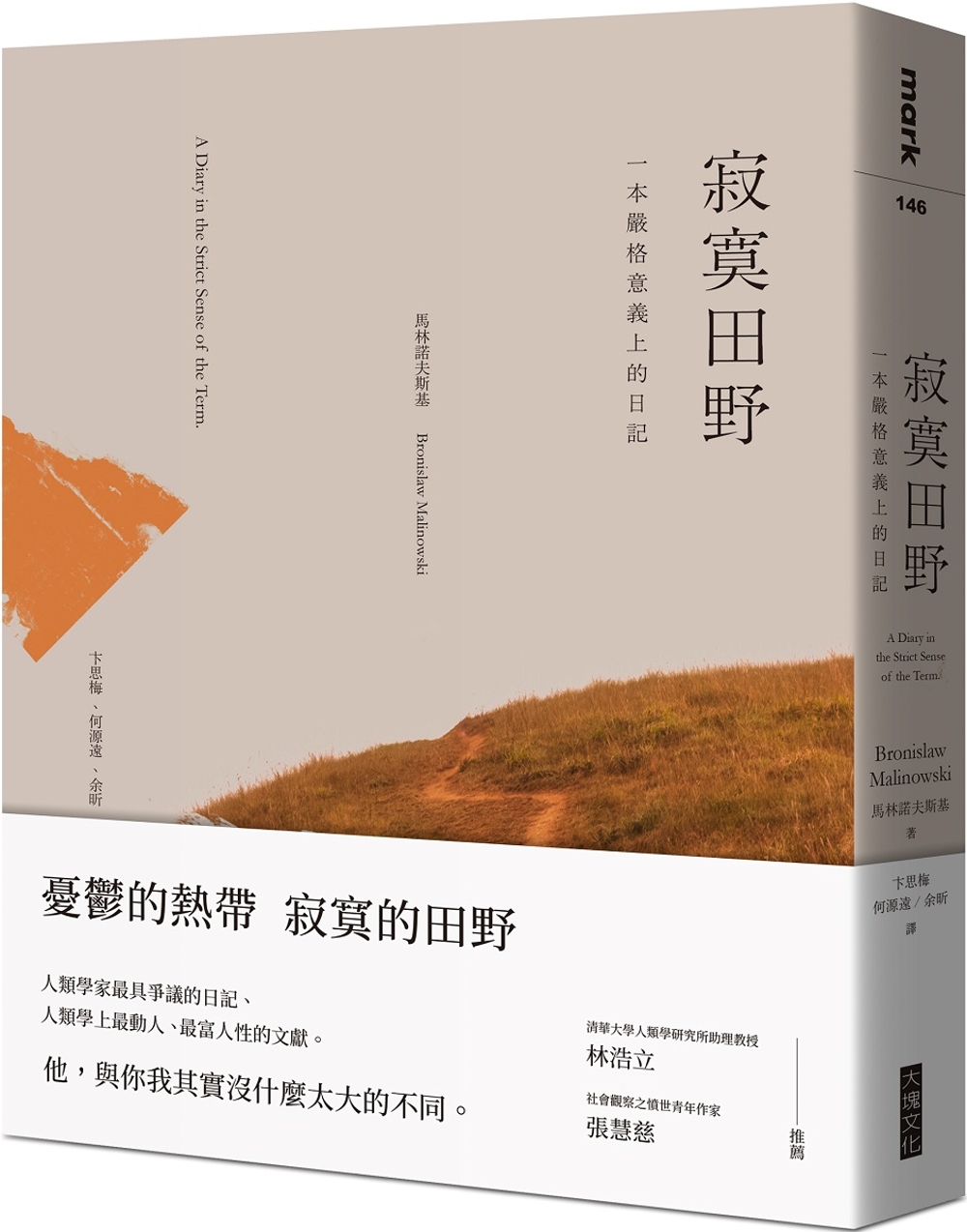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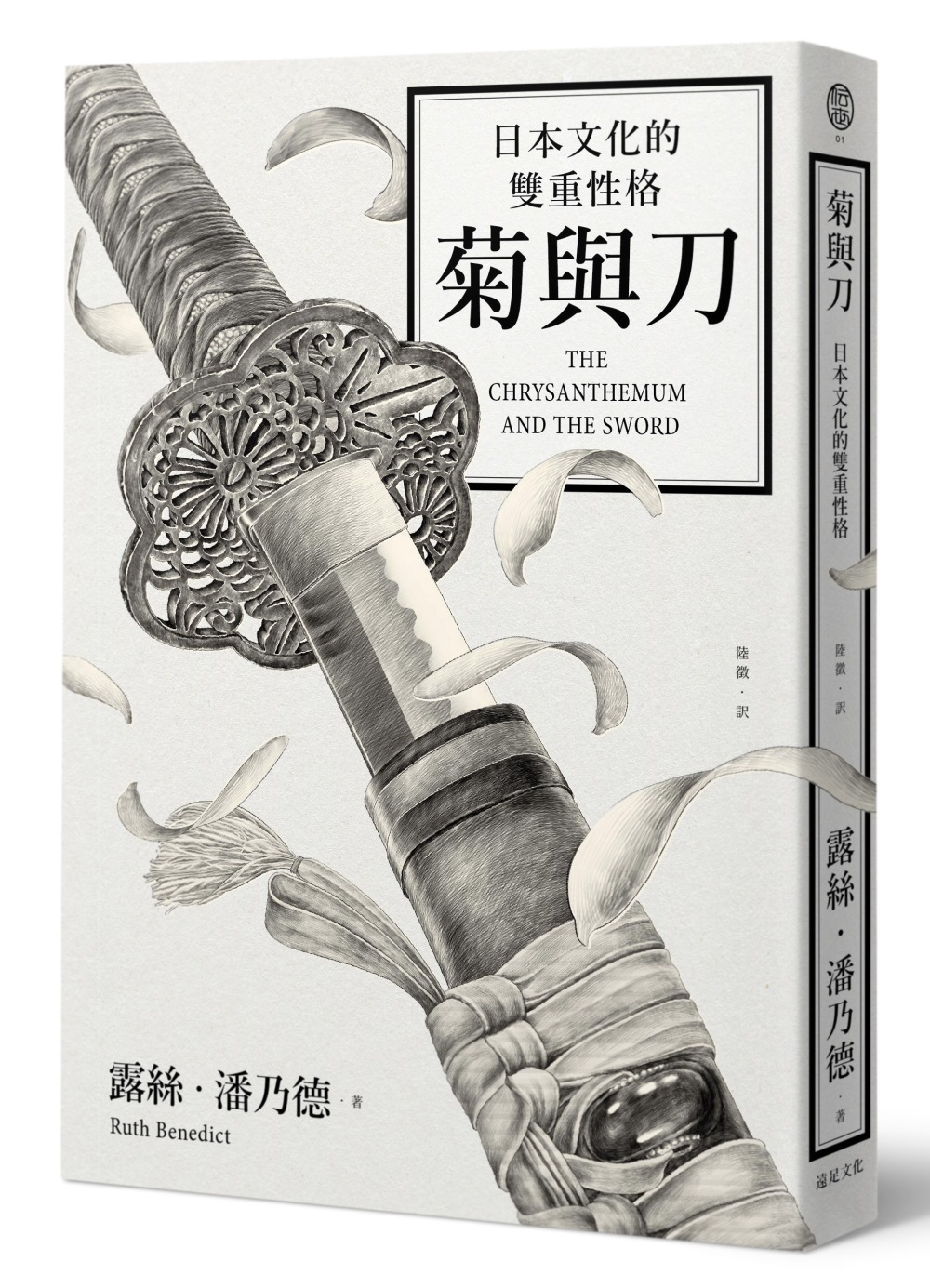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