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樂隊Far East Network 由大友良英(日本)、柳漢吉(韓國)、顏峻(中國)與袁志偉(新加坡)組成。(圖片來源 / FEN )
「聽起來彷彿從海底傳來的殺戮之歌,是機器在唱著,顫抖似的微弱呼吸。瓦爾特 P38手槍啊,手中緊緊握住的一切,都行將消逝。漂泊無定的,魯邦三世……」
——山下毅雄,《魯邦三世》動畫片尾曲
(1) 嗟嗟
「什麼,大友良英上紅白了?!」
2013年12月31日,當《小海女》特別篇登上NHK紅白歌合戰,大友良英(otomo yoshihide)身穿老派西裝頭戴招牌帽子,率領大樂隊彈著吉他伴奏,出現在畫面一角,長期關注大友前衛音樂作品的樂迷們,大概都像是劇中能年玲奈吃驚的時候一樣,喊了一聲「嗟嗟」(じぇじぇ)吧。

不過那時,我只把《小海女》當成大友良英單純的配樂打工,把變成國民音樂家看作他人生的一次意外。儘管也陷入「海女失調症候群」開始追劇,當橋本愛抱著少女偶像夢離家,出走東京失敗被發現,比起小鎮陷入一片混亂的劇情,聽著鳴叫數分鐘之久的噪音吉他,還是不禁在心裡想,「大友終於找機會飆了一把啊。」
跟大部分的日本國民相反,在前衛樂迷眼中,那個用唱盤把各種20世紀的放送內容採樣拼貼,彈奏吉他和弦邊緣的自由爵士,破開現代音樂工業製品內裡符碼的,才是熟悉的大友良英。
十幾歲時,大友良英在距離東京300公里的福島,留有學運餘燼的爵士喫茶裡,窺見了1970年代日本地下次文化水脈,聽到年長十歲的天才薩克斯風手阿部薰演出。畢業後他前往東京,拜師傳奇吉他手高柳昌行門下。
關於那段日子,大友寫道:「那時我 19 歲。政治和次文化的時代結束了,東京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的年代,所有次文化都嘗試匯入主流。來到 1980 年,爵士喫茶驟然消失,而我,一個來自鄉下的自由爵士青年,在這波變化中失去了方向感。這股迷失最後將我帶向一種截然不同的即興音樂。」
對在日本社會建制成功階梯凹下的角落找到這些音樂的人們,看著這樣的高中回憶,那樣的青春多少與自己重疊吧。而在實驗音樂場景極其薄弱、沒有多少前行者的台灣,那更像是一條線索,將我們與那激越聲音誕生的時代相連。
 Ground Zero《革命京劇》專輯
Ground Zero《革命京劇》專輯
在解散20年後,大友樂隊Ground Zero的《革命京劇》仍然是一張未被超越的唱片。從今天返顧,這張專輯有著一個更奇特的位置,一頭面對著20世紀革命的線性時間,一頭指向了事物都被壓縮扁平的21世紀媒體平面。在電腦還沒有普及的1996年,在剪下貼上還不是按兩下滑鼠之前,在臉書跟抖音還沒變成我們的生活之前,大友良英用巨量的唱片做素材,預演了我們從100年前開始的未來。
文化大革命抗日樣板戲、傳統節慶音樂、舊日香港電影、官方新聞聯播、演歌、《毛語錄》日語朗誦、現代廣告旁白、古典音樂、情色映畫呢喃細語、黃土上的民歌……,重型的工業節拍、激烈的噪音與老派的爵士交錯,把這些看似隨手拼貼的片段,全部接在一起。在那之中,20世紀的東亞史在那一瞬間整個被炸開,連同進步論的許諾自身,一同朝向時間盡頭飛去。
「新華社報導,從昨天開始,北京事態急轉直下,近幾個月來,極少數人引發的動亂,已經發展成一場反革命暴亂……」
在還沒有多餘的耳朵,去問這算不算是一首曲子之前,那裡面的荒謬,已像是飄落的繁花,把你深深拉了進去。
當堂皇的口吻,被無基質的雜訊包圍,每個偉大的段落,如同失調的收音機不斷切換,而整個樂隊不發一語,批判、惡搞、幽默、嘲諷、雜生……,形容詞變得如是貧乏,當你試著跟隨那些採樣尋找核心之處,你只發現空無一物,或者,沒有詞語可以表達的,深沉的美麗與憂傷。
(2) 嗟嗟嗟嗟
或許因為這樣,後來的幾年裡,雖然也聽聞大友去311震災後的福島辦起市民大樂隊,幫發展遲緩的孩子做音樂工作坊,受邀策劃札幌國際藝術節……,但我一直沒有仔細想過,大友這些更面向大眾的活動(包括《小海女》配樂)跟他的實驗音樂有什麼樣的聯繫?跟朋友聊起時,總開玩笑說,現在大友良英變成國民音樂家,要找他來台灣演出,恐怕請不起了。

在福島舉辦的市民大樂隊。(圖片來源 / 大友良英官網)
 《山下毅雄を斬る》專輯,封面是鐵甲人。
《山下毅雄を斬る》專輯,封面是鐵甲人。
一直到這次Far East Network(FEN)要來台灣,一邊整理大友的資料,一邊隨手放起前陣子買到1999年發行的《山下毅雄を斬る》,我才三倍驚訝地「嗟嗟嗟嗟」了起來。
原本以為,這張1960年代動畫歌曲的翻唱專輯不過是一時興起、回憶童年的遊戲之作,一聽下去卻不只是這樣。失真的吉他、工業的敲擊、祕教祭儀的吟唱、沒有人稱的電子正弦波、自由爵士的疾走與空隙、迷幻搖滾的清澈與失重……,大友的招牌「聲音」在裡面一個不缺,但一點也不會感到30年的距離,毫無違和。
當Charlie Kosei 跟伊集加代子再一次唱起,這些歌彷彿本來就長這樣。正想著大友是不是順著原曲結構重編?對照之後,才發現那時山下毅雄的曲子便已充滿今天聽來依然大膽的實驗。
山下毅雄兼具旋律上的才華及編曲的想像力,前者,讓大膽的實驗得以進行,後者,透過平移的和弦、間奏的轉調、動畫場景的聲響,將日本的五聲音階,與西方電影配樂、爵士樂、搖滾樂、香頌等等,做出巧妙的連結。
這一連結的結果,遠超出了單純的仿作。在接縫處,既渾然天成,又清楚保留了兩種音樂文化的相遇,呈現出1960年代日本社會轉型的軌跡。在更為現代的節奏與昂揚的曲式下,映照著江戶以來庶民日常的哀愁、笑聲與韌性,而昔日街道的慣習上,又不斷展開意外的奇想。
在那裡面,正如大友在歌詞內頁寫的,是童年時期吸引他一聽再聽,但直到製作這張致敬專輯時,才明白的「歌謠曲的暗面」。就這個角度來說,大友在這裡所做的,或可說是在西方流行音樂已成為日本社會一部分的今天,將山下毅雄在無意識中完成、在日後越發成熟的唱片工業下被遺忘的連結,用比「被定型的耳朵」更激進的編曲,把當年自己聽到的聲音召喚回來吧。

大友良英的演出現場(圖片來源 / wiki)
沿著那聲音,我們來到了那個討厭體育課跟社團活動的小孩身邊,看著他每天傍晚不是定在電視機前等動畫片頭曲開播,不然就是縮在房間裡聽收音機。我們也來到那個電視裝機數字等同日本全國家庭,大眾傳媒工業將要開始填滿人們眼睛和耳朵的時代。
與此同時,我們也來到時代前夜的接縫之處,在那裡,如同電視機上頭,那把大友與弟弟一起做的瓦爾特P38手槍模型,在機器顫抖的歌唱中,有多少複製而僵固的現代生活,就有多少漂泊無定行將消逝的怪盜魯邦三世、鐵甲人與流星號,而在有一天也將被複製的命運之前,它們仍然知道自己的脆弱,並在脆弱中帶給人們勇氣。
(3)嗟嗟嗟嗟嗟嗟嗟
翻讀《山下毅雄を斬る》內頁札記與製作前後的訪談對照,我終於確認了大友這些年所做的究竟是什麼,為什麼Ground Zero就此解散,不曾再重組。
跟著那聲音回到1971年的,也包括人到中年的大友良英自己。
「Ground Zero在海外受到很高的評價,演出的邀約越來越多,但是我也開始感到疲倦。那時,我用兩個唱盤做音源,不斷切換採樣,與台上的即興樂手們對尬。像是機器一樣,把一個人的記憶用到最大容量。但是到了後來,我對劇烈採樣的自己失去了興趣。」
站立在空無一物的中心,是個極為耗損的位置。那一段時間,大友發現,除了樂隊的活動,自己很難像一般人一樣跟朋友來往。在低潮中,他回頭思考自己是怎麼變成現在的自己,想起十幾歲在爵士喫茶的日子,想起國中二年級組裝的合成器,想起小學六年級組裝的收音機,然後想起更早一點,在動畫主題曲裡,跟音樂的相遇。
「這一首聽起來不是Cecil Taylor 的自由爵士嗎?那一首好像迷幻樂隊Jacks……」
帶著這些只有自己一個人發現的祕密,大友開始挖掘山下毅雄的作品,一首一首聽過,最後,在橫濱山下的家裡,找到當年的母帶時,他想:來做一張致敬專輯吧。
國外記者採訪Ground Zero時總會在最後問:你的音樂跟日本傳統文化有什麼關係?你學習禪或佛教嗎?那些歌,更像是給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起遙遠的文化體系什麼,大友其實是那個正在轉變的時代的小孩。
這樣,便可以了解他這段話:「『聆聽音樂』,如果我有所謂的原點,就是這個了。現在,我想用很小的記憶晶片來做音樂,跟身邊的人一起,聽著聲音,然後發出聲音。長年以來的努力,在樂手身上累積而成的技術等等,也可以說是記憶吧。」
在那累積而成的東西中,在各種與音樂的相遇裡,回到前衛青年,回到電視兒童,隨著《山下毅雄を斬る》的錄音工作,對大友來說,不知不覺間,歌唱、旋律與和聲,都變得可以在作曲中自由地採用。離開高柳昌行門下後,在整個1990年代沒有再彈過的吉他,也終於再次拿起。
也在這時,我才清楚發覺,儘管40年來大友良英一直用著同樣劇烈的抵抗與想像力,截擊我們被餵食過剩的定型耳朵,但是,在許多年前,以Ground Zero翻玩爵士老歌的最後一張專輯《Play Standards》和《山下毅雄を斬る》為分界,在那空無一物之處,某種旋律性的聲音,或隱或顯,已悄然地歌唱起來。
怎麼樣才能捕捉自由爵士追尋「誰也不似的聲音」時,打開的人與人的相遇?怎麼在媒體工業籠罩一切時,再現那台電視曾經帶來的嶄新地平線?在這裡面,當有一部分的答案吧。就像在這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交錯了正弦波白色噪音和反覆變奏的合成器旋律的〈Song for T.Y.〉,大友寫道:
「我試著回到自身本質的『哭泣與聲響』,在這個混合裡,向山下毅雄致敬。在CD最後fade out的地方,其實聲音並沒有結束,在那極度微小的電子音裡面,有著轟音的濁流,然後是電影配樂,然後是童謠、爵士樂、歌謠曲,在聲音的後面,它們仍然在繼續低鳴著。」
(4)嗟
在那之後,我們有了自由爵士樂隊ONJQ(Otomo's New Jazz Quintet),有了極微電子聲響組合I.S.O.,有了在各地召集普通民眾參與的市民大樂隊,有了在每天早上8點,跨過不同世代,全日本觀眾聚集在電視機前等待的《小海女》主題曲,有了不只在日本,與東亞其他國家即興樂手合作的Far East Network 以及Asian Meeting Festival(AMF,2018年9月第一次在台北舉辦)。
然後時間來到2019,FEN來台的前夕。
在更短的壓縮時間裡,大友良英將第三次踏上的這個島嶼(第一次帶著一組樂隊),也從收音機、電視、網路到手機,一步一步被媒體工業覆蓋。
1979年,台灣電視普及率達到92%。前一年國語配音的《無敵鐵金剛》剛播映完畢,《小甜甜》接棒放映,下午6點,全台灣的小學生都坐在電視機前。然後在這一年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政府控制的三個電視台,反覆播放擷取畫面,指稱抗議的黨外民眾是暴民,開出獎金50萬元的通緝懸賞公告。
也在這一年,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美軍電台 AFNT(American Forces Network Taiwan)宣告結束。這個戒嚴時期唯一不受廣播檢查制度限制的電台,在24年裡播送著告示牌排行榜,播送了爵士樂、貓王跟披頭四,在FM 100.1,來自西方流行音樂工業大量複製的產品,在這個島嶼聽起來那麼靡靡,成了體制夾縫裡的激進聲音。
「中華民國各位聽眾,祝您健康、快樂、萬事如意!」,「ICRT is on the air!」
在AFNT 轉型成 ICRT 的電台台呼響起40年後,聆聽那一年在上野車站失去方向的前衛青年帶領,和日本美軍電台同名(Far East Network=American Forces Network Japan),沿著冷戰東亞的地圖界線,與首爾(柳漢吉)、北京(顏峻)新加坡(袁志偉)三地樂手,一起組成的樂隊,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
當各種新媒體取代了我們的生活,傳統媒體被商業與政治資本買斷,內容農場充斥,填補著我們消費過剩的確幸,有意與無意的假新聞,煽動著國內政治和東亞情勢的賽局。比起40年前,冷戰體制與消費文化工業合力推動的媒體普及,在今天已變成最麻痺與壓制的型態,其間一度許諾的自由,正搖晃欲墜。
在這樣的2019年,在FEN兩台電子裝置、兩把電吉他構築的河流裡,伴隨低鳴的雜訊與時而浮現的旋律,在錯頻電台顫動的呼吸之間,或許,你將會聽到曾經為之深深激動,曾經每天等在機器前面的什麼吧。
然後,當你在現場的空氣中,窺見了那些聲音裡頭閃現的想像力,你也會驚訝又熟悉地想起自己站在街口的理由,喊出「嗟」的一聲,在困惑與焦慮中,再一次對著擁擠而帶著溫度的日常與真實,大步向前走去。彷彿很多年前看著電視的錯覺,自己也是那個漂泊無定的,魯邦三世。
林易澄
嘉義人。歷史工作者。
曾為《破週報》、《放映週報》、《Gigs》、《號外》等刊物撰稿。
【FEN Taiwan Tour 2019 】
1/19 17:00 座談:顏峻 + 大友良英
台北 當代藝術中心 TCAC|免費入場
1/20 19:00 FEN with Poor Squirrel + Somanana Rain
高雄 武德殿 Butokuden
1/22 20:00 FEN with 誠意重 + 小劉 + 賴士超
台中 玩劇島小劇場 Little Play
1/23 19:30 FEN with Dino + Jyun-Ao Caesar
台北 The Wall Livehouse



 NHK日劇 小海女電視原聲帶 / 大友良英
NHK日劇 小海女電視原聲帶 / 大友良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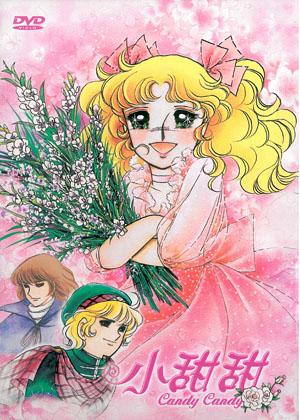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