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母LETTER:童偉格專輯》的延伸專題為「致新世界」,源起於童偉格作品經常凝視臺灣做為新興國家,在現代生活中最徹底失敗的鄉村地區。如何給予苦難與終將消逝的一切以人性的答覆,可能就是文學家的不同之處。換言之,死亡會在這樣的凝視中重新思索出人的條件。這也是特別使用瑞士象徵派畫家勃克林(Arnold Böcklin)畫作《死之島》(Isle of the Dead)的原因:家園即便是死之島,也是船上之人唯一前往的方向。
「新世界」當然是一個危險字眼,充滿現代性下歷史與權力的相對性,這個詞彙或許意味著當時文明眼中的新(甚至是蠻荒)國度,或者是某個地區經歷革命或體制的巨大質變。人類在18至20世紀,以現代性為核心,製造出許多「新世界」,它們在經歷傷痕累累的帝國殖民或掠奪後誕生,各自因受到壓迫的殊異歷史而形成不同的苦難與衝突,百餘年來逐步在不同政權中走向現代(資本主義)之路的臺灣,也是如此。
專題擇選「基列三部曲」、《行過地獄之路》、《二手時代》、《極樂之邦》與《美傷》等五本文學作品,呈現美國、澳洲、前蘇聯、印度與印尼這五個國度面臨的深刻難題。透過這些書評,我們將理解種族壓迫、戰爭、極權與屠殺等這些人類無法終止的悲劇,文學家企圖以人性校準歷史時鐘的努力。
墓地的盛宴
有
什麼
它不能衝破的呢?
世界已去,我只有扛著你。
──保羅.策蘭,〈火紅的,大天穹〉
當我在2017年首次來到印度時,並不知曉這就是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生活了將近60年的大地。我當然也不曉得,她將在這年發表第二部小說《極樂之邦》,與她上一本小說《微物之神》相隔了20年的歲月。
在當時的旅途裡,我在腦海中隨身攜帶過往閱讀的印度文學著作:歐洲知識分子赫塞寫於戰間期、探尋「歐洲所缺乏的東西」的《流浪者之歌》(1922);遠藤周作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深河》(1993)───書中的恆河就如同《流浪者之歌》中的「諸事之河」接納了生與死、神聖與汙穢、殘酷與慈悲;出生在千里達的印度裔作家奈波爾首次回到「原鄉」印度的作品《幽黯國度》(1964)───印度是令他感到羞恥的第三世界與舊世界,然而他仍在目睹印度的古老習俗衰亡時感到莫名的感傷。此時,印度已不是赫塞或遠藤筆下尋找新世界的隱喻或外衣,而是身為「後殖民旅人」的奈波爾始終辯證「抵達之謎」的母土。
回到臺灣後,我才讀到洛伊的《極樂之邦》。她在奈波爾首次來到印度的前一年出生,而她開始寫作小說的90年代,同時也是許多邊界瓦解與重組的時代:隨著冷戰終結,二戰後以「防堵共產」為核心建立的區域研究,在氣候變遷的環境意識下重新整合;同樣藉由「防堵共產」為邏輯所支撐的第三世界,也不再只是充斥著異文化情懷,又被戰後民族主義斷開政治連結的後殖民國家。相反的,氣候變遷、能源競爭與非正式的遷徙活動要求一種與建立民族國家時截然不同的歷史,使得它們在區域整合的進程中成為牽動國際政治的重要角色。
1999年,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攝影師貝瑞(Ian Berry)在古吉拉特邦的村落中拍下洛伊的身影。這一系列記錄「反水壩抗議」的相片呈現的是與《深河》截然不同的河流───當無數抗爭的人民面臨被水壩集水區滅頂的威脅時,人們早已無法從自然中得到慰藉。而在其中一張格外寧靜的相片裡,洛伊就緊鄰著納爾默達河,側臉朝向景框外的遠方。不需要仰望天際的禱詞,也不再有低垂眼瞼的憐憫,她就像個歷盡滄桑卻永遠處於青春期的青年,以平視的眼神傳達永不言敗的宣言。

(圖片來源 / magnumphotos)
閱讀《極樂之邦》時,我時常想起那既不祈求祝禱,也不抱怨自憐的平視目光,它穿透的是足以抵抗虛無的平實肯定:洛伊對一切她反對、厭惡、同情、尊崇的事物說「是」。她所談論的印度不單是豁免於「西方現代性所招致的災難」的東方國度;也不只是後殖民情結中辯證「抵達」與否、無家乃至於無歷史的心靈疏離;更不僅是與後殖民民族主義緊密相關的第三世界。她用嚴肅卻幽默的文字、剔除抱怨與內在糾葛的開放口吻,回應她對於當下世界浩繁而深邃的理解:這是一個在尺度之間穿梭的世界、區域劃分不斷重組的世界、豐饒自然早已成為鄉愁的世界、當代全球化之下既新穎又古老的世界。
這完全要看你的心
2017年9月,過去擔任古吉拉特邦首長、現今做為印度總理的莫迪正式啟用那系列照片中人們所抗議的薩達爾薩羅瓦水壩。在《極樂之邦》裡,這位主張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總理被洛伊稱為「古吉拉特邦的最愛」,而在他當選總理前,小說主要角色之一安竺在一場由印度教右翼團體策劃的屠殺中倖存,倖存原因不過是因為這些劊子手渴望好運───如果殺死做為「海吉拉」(Hijra,南亞地區對變性人或跨性別者的稱呼)的安竺,會替他們招來厄運。
洛伊在第一章章首引用了土耳其作家辛克美的詩行:「我是說,這完全要看你的心……」而她確實在敘述海吉拉時,將焦點放在「內心的戰爭」。那是一句令人屏息的精確描述:海吉拉的所有問題都在內心,這使得「印巴之戰也在我們心中開打」。
在往後的敘述中,發生在內心的印巴之戰不再為海吉拉獨有,而是廣布在所有人心中的戰爭。藉由這些極度邊緣的人們,洛伊道出普遍存在於眾人心中的掙扎。然而洛伊從不強調這些角色的「邊緣」,「邊緣」因此掙脫了「固著政治身分」的枷鎖,成為每個人都曾擁有、流動的片刻狀態(或永恆狀態)。如此一來,穿梭在文字間、不容忽視的政治性(politics)也毫無痕跡地融入人們的生命中,使這些角色擁有詩(poetic)那般的生命基底,而不是一則淺薄的政治隱喻。
詩意來自於洛伊確實與小說中的角色一同生活───不,我幾乎願意相信這些角色真實地活在世界上。當我閱讀著洛伊筆下的每個角色,浮現在腦海的總是她與這些人們交談的畫面:在街談巷弄中、在即將淹沒村落的水壩集水區旁、在印度毛派生活的潮溼森林內……她以平視的眼神,不卑不亢地聆聽人們的話語聲。
當一個角色真實地活在世界上,他/她還能完美合適於架構完整的故事嗎?為了知道原因,除了談論這本小說,我還得談論洛伊的寫作,無論是虛構寫作,還是她從事了20年之久的非虛構寫作。在書末的致謝名單中,洛伊向我提供了一點線索。她將一位耳熟能詳的作家列在第一位:「伯格(John Berger),他不但幫我起頭,也等我寫完。」
2007年,洛伊向外界透露正在創作一部小說;2011年,她在《獨立報》的採訪中提到一年半前與這位英國作家的見面。約翰.伯格要她把正進行的小說朗誦出聲,隨後告訴她:「妳得回到德里,完成這本書。」然而當洛伊回到德里,她在門縫底下收到以電腦繕打的匿名信。信來自丹達卡倫亞森林中的毛派游擊隊,他們邀請洛伊來與他們交談。洛伊選擇放下創作,前往位於印度中部的叢林,並在返回德里時,在《衛報》發表了一系列非虛構文章〈持槍的甘地〉。事實上,在《微物之神》與《極樂之邦》相隔的20年間,洛伊發表了多本非虛構著作與文章,以此回應介入現實時需要迫切發聲的問題。
我總以為,那些渴望自由創作,也對迎面而來的現實災厄感到焦慮的寫作者,勢必明白介入現實時在自己內心開打的戰爭───如同《極樂之邦》中所寫「要滋養好文學,可接受的鮮血量是多少?」的戰爭。然而,我不能確切地說:洛伊在虛構與非虛構寫作間、在介入現實與創作小說間,真有這麼一場印巴之戰。洛伊曾在《紐約時報》的專訪說:「有些人往往說我(繼《微物之神》之後)不再寫作,彷彿我寫的非虛構文章都不是寫作。」這句話放在整篇報導的開頭,堅毅地好似她不曾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劃下戰壕;而她介入現實時的篤定姿態,也彷若她內心不曾有戰爭開打。
翻閱《極樂之邦》時,我發覺那些在她介入現實時必須篤定剔除的內在動搖,都在小說裡存活了下來。在內心開打的印巴之戰不斷找上她,只是她不與這場內在戰爭正面對決,而是透過書寫「不正面對決」的小說,撐起一個「讓內心的印巴之戰平息」的可依靠之地。在小說中,洛伊也為人物打造了這樣的可依靠之地:即便無盡的外在衝突從未平息,這些人物同樣以「不正面對決」的方式面對外在或內在的衝突,藉此撫平了內心的印巴之戰,使得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易於承受。
正面對決與否的張力,在書中一段辯證「使人軟弱的自憐」與「遵循敵人邏輯才能為尊嚴而戰」的對話中顯露無遺:
對我們來說,最難的是什麼,你知道嗎?……就是可憐……我們很容易自憐自傷……要擁有尊嚴,只有一個方法,也就是反擊……我們不得不去除自身的複雜、我們的分歧……變得愚蠢……就像我們面對的軍隊。占領行動最糟的就是這點……如果我們成功了……我們將獲得救贖……在我們勝利之後……就會變成我們的報應。先是自由。接下來是虛無。就是這樣的模式。
《極樂之邦》中的人物甚少採取軍隊那般「正面對決」的抵抗,他們在苦難跟前分心、將眼神瞥向他處、掂起腳尖逃跑,即便有人被迫選擇了軍隊般的「正面對決」,他們依舊走在自由與虛無的鋼索上,抵抗虛無的全面壓制。
我以為,洛伊之所以能透過非虛構寫作與無數迫切的議題「正面對決」,同時又能在虛構創作時,不帶自溺與怨懟地書寫人物的詩性生命(而不至於成為去除複雜與分歧的軍隊),並不只是因為「這完全要看你的心」,更因為她透過「不正面對決」的虛構創作,在介入現實並歷盡滄桑之餘,仍能保有孩童般的純真、信任與愛。這些在小說中存活下來的物事,撐起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不是慘澹陰暗的無望未來,也不是充斥樂觀主義的繁榮景象,而是在悲劇意識中生成的——脫困求存的希望。
另一個世界:生死門縫間的盛宴
在安竺因為屠殺而來到墓地,並建立「天堂旅社」的30年前,小說的另一條故事線圍繞著四位大學生:蒂洛、賈森、穆沙與納嘉。那年是被賈森稱為「誰能忘記這一年?」的1984年,英迪拉.甘地總理被刺殺不久後,又發生了博帕爾公司毒氣外洩事件。這兩個舉世注目的事件掩蓋了一則喀什米爾人被處以吊刑的新聞,直到蒂洛與走上革命道路的穆沙在多年後重逢時,小說才揭露了這則被印度當局視為喀什米爾動亂徵兆的新聞。1984年的當下,來自喀什米爾的穆沙在聽聞這則新聞後,對蒂洛說:
對我來說,歷史是從今天開始的。
即使蒂洛不明白話中的意義,仍記得其中的力量。我以為,那意義不甚明瞭卻力道猶存的物事,回應的確實是歐威爾在1949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在這本書所描述的未來世界中,由「老大哥」嚴密控管的大洋國有四個政府部門:負責謊言的「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負責酷刑的「仁愛部」(The Ministry of Love)、負責戰爭的「和平部」(The Ministry of Peace)和負責貧困的「富庶部」(The Ministry of Plenty)。基於「雙重思想」(Doublethink)原則,這四個部門負責的業務是部門名稱的反面,如同最高權力組織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歐威爾將這個未來的極權世界訂立在1984年,宛若在這一年後歷史便結束了:往後的人們都將如此過活,時間中不再有後來,也就不會有可能性的未來。而我以為,洛伊藉由穆沙之口說出的話語「歷史是從今天開始」,顯現了她在《極樂之邦》提供的另一個世界:「一九八四」之後的世界。過往歐威爾認為的終極未來,此時成為《極樂之邦》的歷史起點。而《極樂之邦》英文書名「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也呼應《一九八四》的部門名稱「The Ministry of -」。然而,這不意味著「極樂之邦」也遵循了「雙重思想」原則並成為「負責苦難的極樂部門」,相反的,我認為洛伊正嘗試以此翻轉「雙重思想」的負面意涵。
「一九八四年後的另一個世界」不只是「極樂之邦」,也是安竺在屠殺後所抵達的墓地。在小說倒數第三章〈極樂之邦〉裡,這塊聚集了歷盡滄桑之人的墓地,呈現了既矛盾又依賴的景象:小說中的人們在生與死交界的墓地上相遇、生活、舉辦喪禮與婚禮、迎接新生與死亡。這些看似對立的事物在墓地中緊緊交纏,使得墓地既是相連之地,也是使內心的對立與戰爭平息的可依靠之地。因此,「極樂之邦」所傳遞的絕非「雙重思想」中「負責苦難的極樂部門」,而是那些支離破碎、無以名狀、無法化約成結構的物事得以倖存的處所,如同那句在故事起頭便預言了整部小說的話語:
我是盛宴(mehfil),我是人群。你可以說我是每一個人,我是一切,或說我什麼也不是。所有人都邀請了,還有遺漏嗎?
2002年9月,洛伊在911事件週年後,以「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樣的肯定語氣,替一場名為Come September的演講作結。不同於《一九八四》的結尾停留在主角對於老大哥的終極熱愛與臣服,在洛伊對所有事物說「是」的無限肯定裡(如同那張河畔照片),她在小說結尾與人們一同受邀至生死門縫間的盛宴、那朝向我們走來的另一個世界:
墓地那些歷經滄桑的天使守護著歷盡滄桑的人,為她偷偷開啟兩個世界之間的門。……她因而洞視生者和死者的靈魂水乳交融,就像參加同一場派對的賓客。
我想大膽臆測洛伊以「一九八四年」與「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回應歐威爾的用意。如果說《一九八四》是歐威爾───生於英屬印度的他在殖民地緬甸度過年輕歲月───做為殖民帝國官員的自我省察與警惕,因而在意識到西方現代性所招致的災難後,所創作出「停下歷史」的無望之作;那麼戰後在印度本土成長的洛伊,則試圖在《極樂之邦》中提供「啟動歷史」的希望。這個重新啟動的歷史鐘擺所創造的弧線空間,就是後殖民國度面對當代全球化的可能未來:縱使印度仍深受殖民遺緒所影響,也確實身處後殖民的心理糾葛與政經依賴中,然而,在這個「現代性」早已招致反噬的全球化時代,印度有機會比現代性起源的西方更易於───藉由探向豐饒而纏繞的歷史寶藏───掙脫現代性的束縛,驕傲地做為「印度自身」。
因此,那塊在盛宴中打造的墓地,雖然看似回到過去的原始部族社會,卻絕非走入倒轉的時空隧道。洛伊以她對母土的愛、對當代人們生存條件的領悟,追尋著允許另一種身分認同存在的「極樂之邦」:在既新穎又古老的當代全球化處境下,印度將不再是依附於殖民時期的後殖民國家、附著於第一與第二世界的第三世界,或僅能依循戰後民族主義建立的民族國家;做為「印度自身」,它能夠向過去的歷史階段汲取水源,融合不同歷史實踐,成為新的再創造。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Akh daleela wann(講故事給我聽)
───《極樂之邦》中婕冰小姐一世的墓誌銘
《極樂之邦》做為一本令我折服的小說,不僅是因為洛伊以扎實的非虛構基底,藉由虛構創作呈現了當代印度,也不只是她以肯定的意願提供有別於《一九八四》的另一個世界「墓地的盛宴」,我認為她更藉由這本小說向世界提問:在這個支離破碎的當代世界,我們還能怎麼說故事給孩子聽?
書中有三個說故事的場景:安竺向領養的女兒贊娜述說「刪除所有的折磨和不幸」的故事,如此一來,安竺在說故事時也「變成一個比較簡單、快樂的人」;與安竺的美好童話故事不同,穆沙的女兒婕冰小姐不停要求父親「講故事給我聽」(Akh daleela wann)。她指的故事不是美好的童話故事,而是「真實故事」。在婕冰小姐因為受到喀什米爾衝突波及而去世後,決心走上革命道路的穆沙,在轉往地下活動的前夕替婕冰小姐寫信。這封使人落淚的信是這樣開頭的:
你要我講真實的故事給你聽,但我再不知道什麼是真實了。從前的真實故事,也就是我過去說的那些,你無法忍受的那些,現在聽起來就像愚蠢的童話故事。
轉往地下活動的9個月後,穆沙與來到喀什米爾的蒂洛見面。蒂洛隨後來到婕冰小姐埋葬的烈士墓園,而刻印在婕冰小姐墓碑上的小字,正是Akh daleela wann。18年後,蒂洛在一場抗議中抱回一名棄嬰,來到安竺在墓地建造的天堂旅社。她將過往在喀什米爾衝突中死去的婕冰小姐喚作「一世」,將甫降生的棄嬰取作「二世」,這樣的稱呼使她們有了血緣的連結,然而是否真有血緣關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橫越了生死邊際的意願:
那寶寶是婕冰小姐回來了,不是回到她身邊,而是重回人世。……開心草原已經隕落,但婕冰小姐來了。
此時,婕冰小姐不再是做為個體死去的婕冰小姐一世,而是所有死於喀什米爾衝突的集體死者;而做為個體降生的婕冰小姐二世,也不只是擁有無限可能性的新生命,她更延續了集體死者的渴望。表面上的血緣提供了愛的合理性,使人們對個體新生命的愛,成為承擔起集體死者的「歷史意識」。這樣由歷史性的悲劇意識而生的愛意與希望,使小說中的人們內在的印巴之戰平息,也使人們有勇氣以「不正面對決」的方式抵抗龐大的體制。
小說裡的第三個說故事場景,發生在穆沙與蒂洛的最後一次會面。在墓地的天堂旅社裡,蒂洛告訴穆沙自己死後將刻在墓碑上的詩句:
要如何訴說一個支離破碎的故事?
就是慢慢地變成每一個人吧。
不是。
是慢慢地融入一切。
在那場名為Come September的演講中,洛伊引述伯格的小說《G》中的話語:「不再有一個故事能被當作單一故事那樣被訴說。」並以此指出當代寫作者的處境:寫作者絕非主動收集故事的人,而是故事主動顯露它自身、故事篤定要求被訴說。因此,當代不再有單一而架構完整的故事,而只允許支離破碎的故事。要講述支離破碎的故事,慢慢地變成每一個人並不足夠,還必須慢慢地融入一切。
如此一來,這些看似沒有解答的疑問───在這個支離破碎的當代,我們如何說故事給孩子聽?怎麼告訴孩子這個複雜而悲傷,卻迷人而美麗的世界?我們要說一個刪除不幸的美好故事,還是真實的殘酷故事?我們是否給得起美好故事?又或者,我們還有真實故事可以講嗎?───對於洛伊來說,或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這些疑問要求的不是解答,而是永無止境的實踐意願:寫作者繼續書寫故事、繼續藉由故事承擔無數死者記憶的意願。
2017年初,伯格以90歲高齡辭世,而洛伊也終究在伯格生前完成了這本他叮嚀她完成的小說。我想起伯格曾以辛克美的詩行命名的散文〈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他在文章探問已然離世的辛克美:「我想問你,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生存的這個時代。」而在文末,伯格以辛克美一首名為〈雨中〉(Under the Rain)的詩回應了這則探問。這首詩的結尾如此迷人又不失力道:
如果我是話語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在洛伊生存的、支離破碎的當代印度,洛伊也成為了話語,她輕柔訴說的愛不曾休止。我始終記得那句做為小說結尾,卻啟動另一個世界的話語,正是這樣書寫的:
……無論如何終會否極泰來,這是一定的。
因為鄔黛雅.婕冰小姐來了。
───因為唯有透過希望與悲傷緊密纏繞、生者與死者水乳交融,才能輕柔訴說的另一個世界來了。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童偉格專輯》)
羅苡珊
1996年生。關注離散的人群、自然與社會的關係、全球化及後殖民處境。期許自己緊挨地面、持守知識、睜眼凝視,從個體生命路徑中追索出豐饒交錯的結構網絡。
延伸閱讀
1.【書評】陳思宏:以哀愁、碎片、屍體編織而成的當代印度敘事錦緞──讀《極樂之邦》
2.【致新世界|書評】房慧真:美麗是種傷──讀《美傷》
3.【致新世界|書評】辜炳達 :《行過地獄之路》與野蠻詩學
4.【書評】吳曉樂:當你要征服什麼,至少要理解對方的語言──讀《毒木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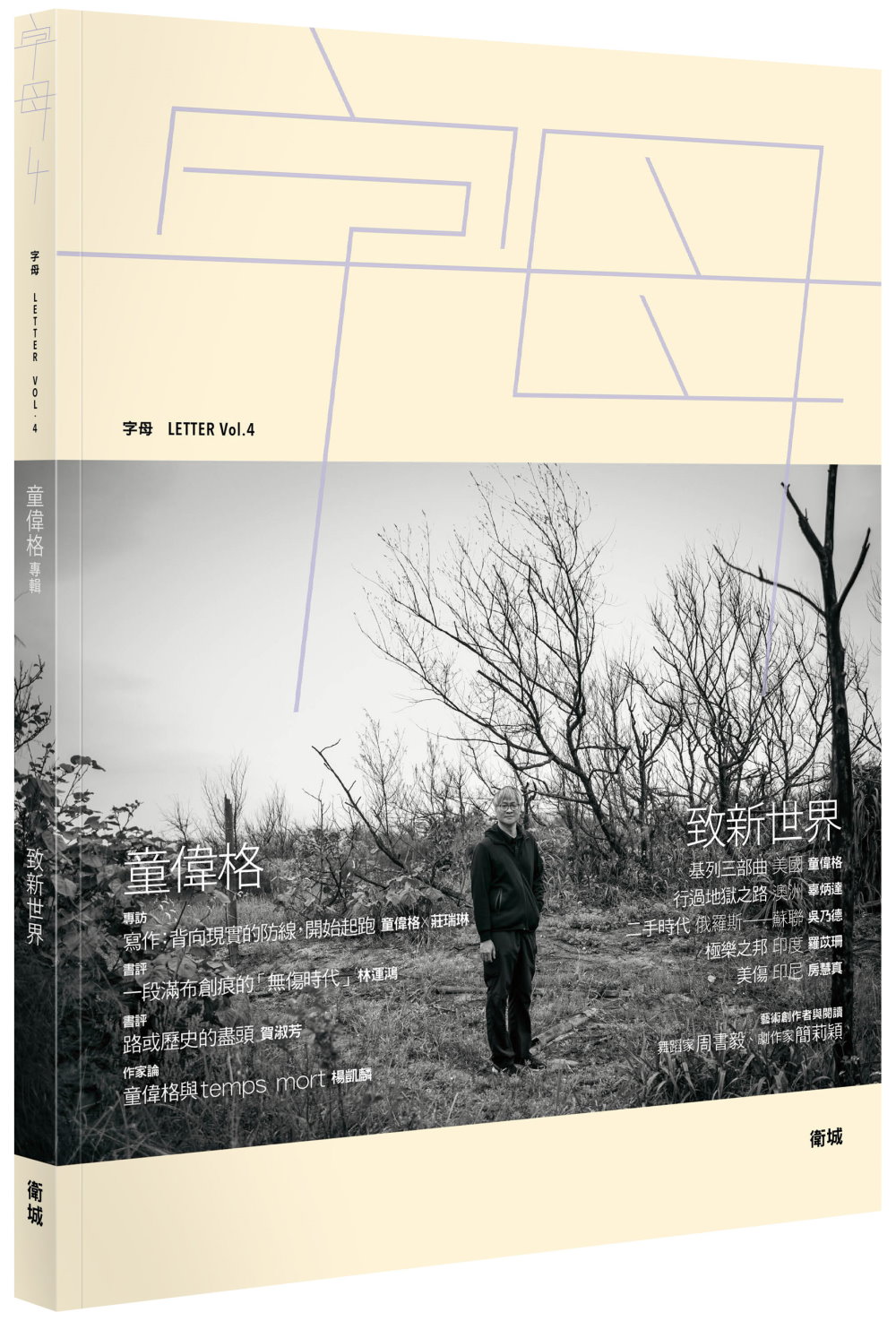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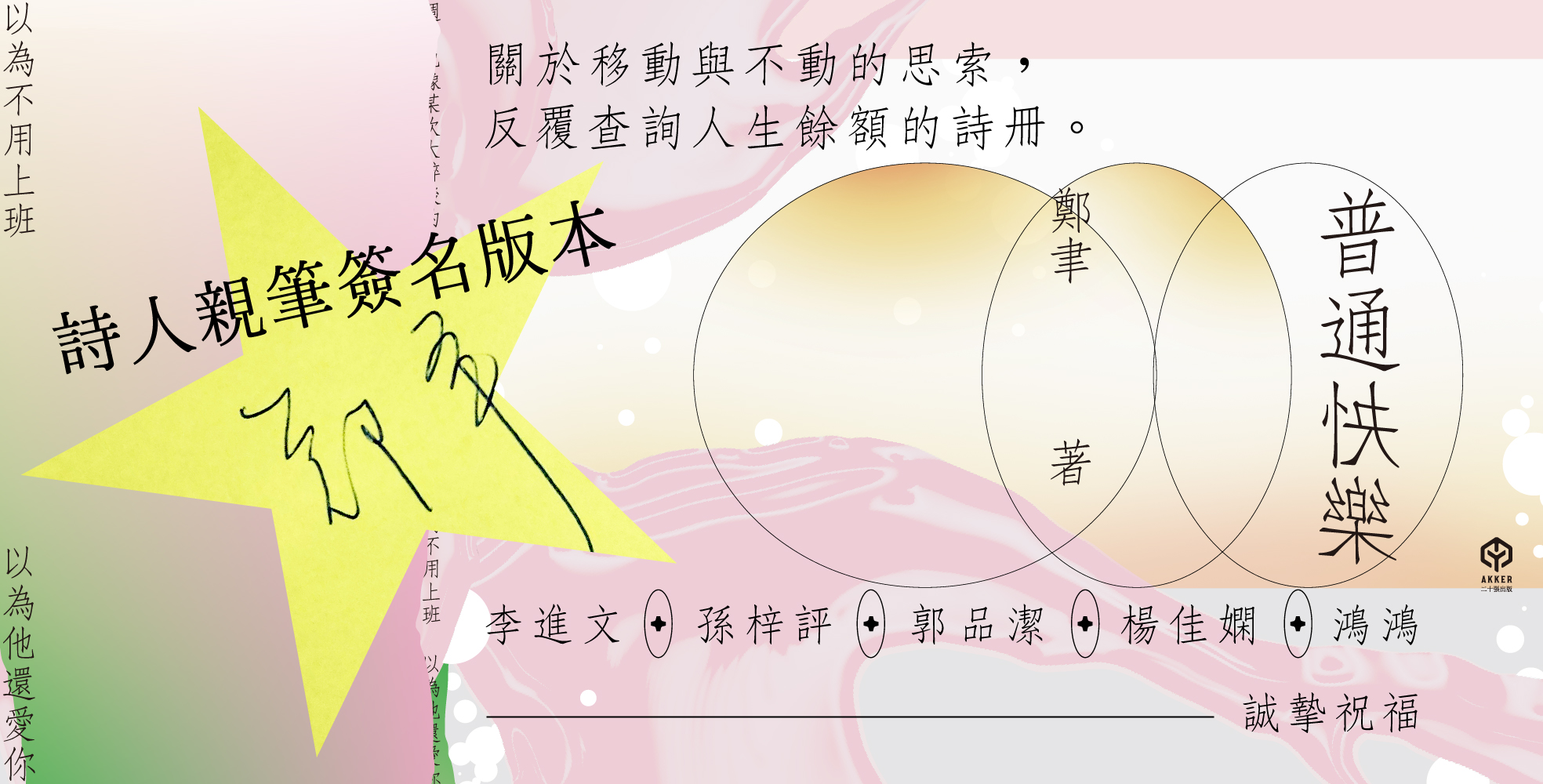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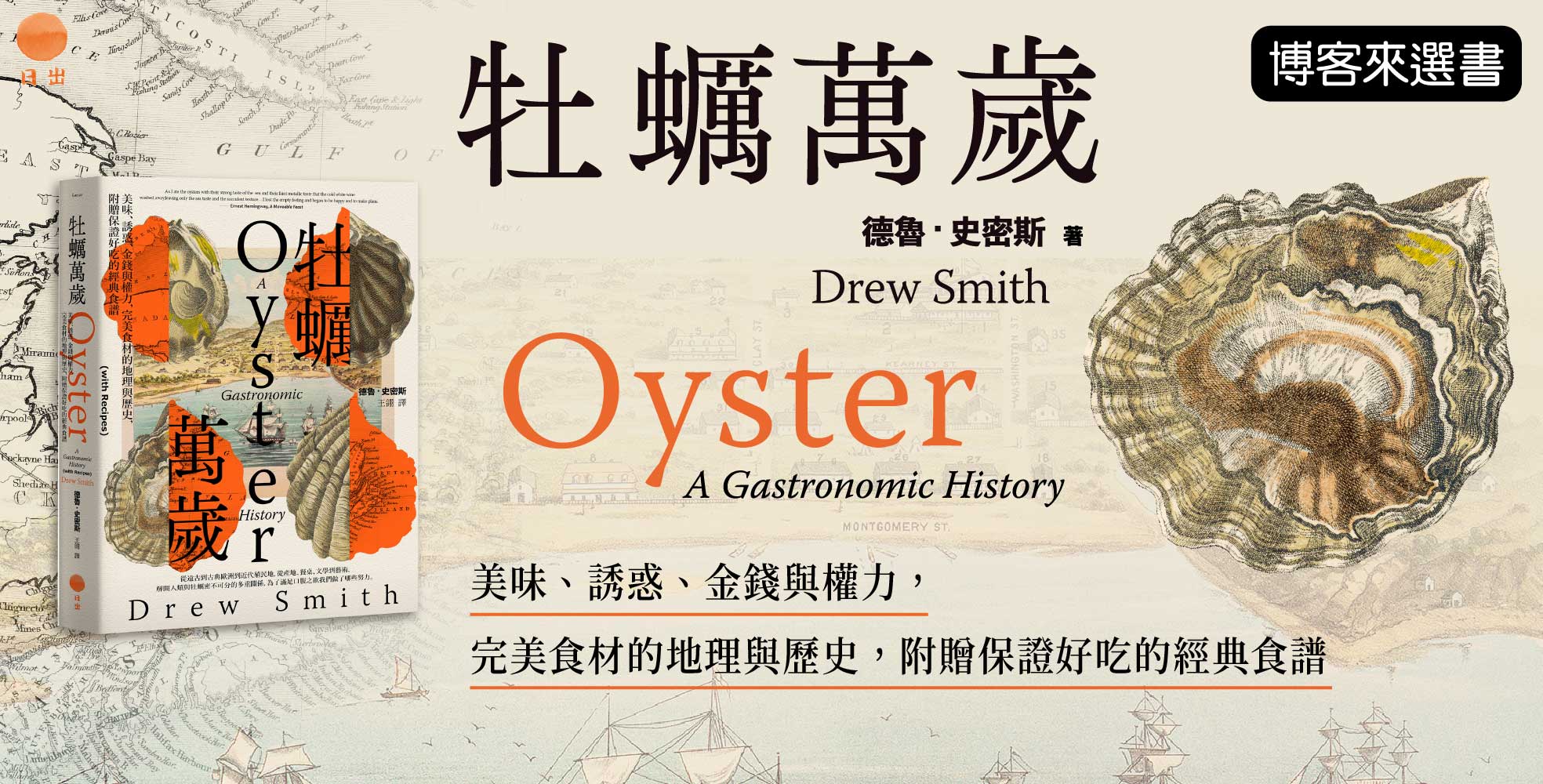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