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我們竟如此理所當然的,以此定義了全世界。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
作者:DL / 2013-02-21 瀏覽次數(7950)
──Pigg,1996
(市場)讓我們(自願的)從溫馨、無聊的小地方脫離出來,成為世界舞台上的自由演員,在世界體系中流動。但讓我們自由的同時,也讓我們暴露在外。──Douglas,1992
自由,某個解釋就是沒有屏障,換句話說就是「暴露」;當我們討論經濟貿易的時候可能比較容易意識到這個問題,可是生活中的其他層面呢?這是個通常不容易被我們意識到的危險,卻的的確確是現實的一體兩面。劉紹華用人類學者瑪莉?道格拉斯的這句話,來形容她的涼山兄弟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處境。我們,也一樣嗎?如今我們理所當然用來定義世界的種種觀念,有多少是危險的?有多少,我們也被全世界定義,而不自知?
年前,國際書展的活動中有一場張翠容的新書發表會,《地中海的春天》。這是張翠容在阿拉伯之春、歐債危機之後,親訪地中海週邊的希臘、西班牙、埃及與突尼西亞,以她的角度,或訪談或隨記,試圖為讀者呈現的事件真相。發表會上,張翠容提到全球化對當地造成的衝擊,以及她與當地人對談的過程中一些想法;她說,「如果大家都用同一種邏輯思考,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是呀,很奇怪,可是我們怎麼會都沒有意識到?我們好像很理所當然的,以相同的邏輯,定義了全世界;也被全世界定義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裡所謂的全世界,並不包括我們自身;以及,劉紹華故事裡的諾蘇人。
2001年,中國政府與國際機構合作,調查涼山地區的愛滋感染狀況,結果非常驚人:諾蘇人佔四川人口比例不到3%,但當地愛滋感染患者卻佔四川愛滋患者的近六成;而調查結果發現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在涼山和大城市之間來回流動的年輕諾蘇男性,其不安全的海洛因注射行為,是造成當地愛滋流行的初因。
為什麼諾蘇人在海洛因和愛滋病面前顯得特別脆弱?當地人的生活因為毒品或疾病有何改變?當地人如何看待?政府當局的介入,引發了怎樣的合作或衝突關係?《我的涼山兄弟》,是劉紹華在四川雲南交界的涼山彝族自治區,針對九O年代當地少數民族的毒品及愛滋病問題所作的田野研究;很學術的說,這是一本醫療人類學著作。只是,看張娟芬的推薦序,她以「逼下涼山」為題,不啻是個貼切又引人心酸的譬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涼山地區經歷了兩次國家權力的干預:第一次,「現代性」的承諾,將年輕人逼下涼山;因為山下比較文明,比較進步,下山才賺得到錢;當年輕人在大都市裡無以維生,抱病、抱毒返鄉,國家則以治療為名,進行第二次現代性干預──山上太多疾病,太多藥癮,需要「現代」醫療才能治癒。一如作者自己所言,許多醫療人類學的研究,都是希望凸顯少數社群在大架構下的困境與適應不良;但她這本,更想呈現的是個人的聲音,不僅僅是陳述個人的痛苦,也希望呈現出個人(被邊緣化的個人?)在企圖參與群體&全球化的過程中,對於參與更美好進步生活的渴望。資本主義和全球化不僅僅讓諾蘇族的年輕人有了不同於過去的部落生活和規範方式,也讓他們對所謂「美好生活」有了不一樣的想像。
所以,或許我們也可以很感性的說,這的的確確是劉紹華以人類學研究的手法,寫她涼山兄弟的故事。寫的,不外是一群年輕人對大千世界的想像、以及唐突探險;還有所謂的「全世界」邏輯的冒然插手,對當地半新不舊文化造成的無所適從。
諾蘇人進入現代性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外力不同方向的牽引:從二十世紀初的鴉片經濟、二十世紀中社會主義進駐,到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帶來了市場改革,諾蘇人改變的不只是原有的社會組織及權力架構,劉紹華首先以兩個重要的時間點:1956、1978──社會主義和經濟改革進入當地,探討這兩項外力對當地傳統價值造成的轉型及影響,介紹涼山愛滋問題的時代背景。接下來講的是諾蘇人,尤其是年輕男性在這兩項外力影響下的適應及向外遷徙:傳統觀念中,男人是要出去探險的,而市場改革之初,下山找頭路成了諾蘇人新興的成年禮儀式,但最終落個功不成名不就的返鄉,海洛因和愛滋病毒也尾隨這批年輕人,成了返回家鄉成了新興的社會危機。最後則是論述官方及當地傳統領袖如何利用國家機器力量,以及傳統親屬組織權威、儀式象徵力量,來試圖解決新興的社會危機?劉紹華最終企圖提問的是:現代性,究竟為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麼?
它依然是本較為學術性的論述。縱然人類學的領域特質、大量口述訪談,作者文學性頗重的筆法讓此書讀來並不過於艱澀;但它依然是嚴肅的。因為,或許為時已晚,這也是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的問題。書中描述的是諾蘇人在成年/追求現代性中付出的代價,可是看看眼下,世界各地的行為模式、價值規範趨向一致,所謂的「普世價值」,合理嗎?我們竟如此理所當然的,以此定義了全世界?
……以銘誌一個可能即將灰飛煙滅的時代記錄。
我希望涼山和我諾蘇兄弟們的生命能廣被認識。這是我始終如一的初衷。──劉紹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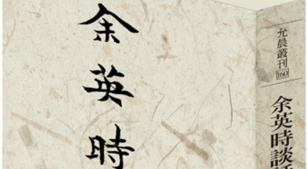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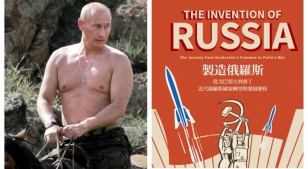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