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演員繆騫人飾演的周郁芬,在楊德昌1986年電影《恐怖分子》開端,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果你了解季節,變化只是一種輪迴的重複。」
當時繆騫人如此美麗知性,散發著同代台灣女演員少見的都會幹練氣質,出演楊德昌的台北恐怖故事。三十八年倏忽而過,繆騫人已息影多年,周郁芬卻投胎轉生,連同片中丈夫李立中等角色,一併被作家陳慧引渡至小說《小暴力》,跨文本重生,透露出香港與台灣於文化與政治上,絲絲縷縷的多年牽繫。近年陳慧同眾多香港作家,轉移出版陣地,以台灣為發聲管道,而《小暴力》便顯出兩地歷史文化的重重疊映。
《恐怖分子》描繪的八〇年代台北,處處潛藏無形暴力,包括國家機器控管、中產階級科層體制的壓抑,夫妻關係疏離,點點滴滴蓄積成多股能量,沒入社會脆弱地殼,如地下水脈隨機流竄;而《小暴力》接續《恐怖分子》營造的現代城市形象,也突顯其流動與不確定性。書中章節標題「安安與小顧」、「大順與安安」、「小顧與洪啟瑞」乍看令讀者摸不著頭緒,實際上陳慧將看似毫無關聯的人物,倆倆繫結綁定,發展出多段關係,直至繩結擴張為一張大網,才逐漸展露出整體敘事邏輯與意義。
城市是張網羅,故事本身也是網羅,而繩結繫起的人物關係,無論是依存、敵對或共棲,個人意志皆與體制扭擰出橫逆張力,因而每一枚繩結皆為暴力,放眼整張網羅,遍是密簇簇的小暴力,由個別人物的小遭遇小傷痛,梭織成陳慧所欲描繪的當下圖像,情狀與她所致敬的《恐怖分子》相似,但時代風景仍有差異。小說裡,國家機器由《恐怖分子》的資本主義與單一政權高壓統治,碎裂為無處不在的資訊操控,獨目巨獸變成百眼巨人,監視掌控人們一舉一動。如書中警察小顧與學妹的對話,談及他人為何得知兩人的私密情感:「他們什麼都知道。因為事情都是他們在安排的,所以他們什麼都知道。」小顧與學妹身為警察,都沒指出他們是誰,彼此卻心知肚明,新世紀的暴力沒有特定形狀,面目模糊,但又無孔不入。
暴力泉眼無處不在,但身處其中的個人,相對應地,也運用城市的流動性,滑脫固定的身分位置。《小暴力》的周郁芬和《恐怖分子》同名角色,都對無愛的婚姻感到窒息,意欲逃離,但小說版周郁芬的逃逸有別於電影,她不僅卸除了妻子的角色,還置換了身分,甚至發現周遭眾人也隱藏著其他身分,置換之外還有置換,替變之外還有替變,最後真假混淆難辨。
而偽裝與冒名的理由,暗指向香港近年的政治社會劇變。反送中運動遭鎮壓後,異議人士一概被政府打為「恐怖分子」,不得不逃離家園。然而,諷刺的是,過往看似困守家庭的主婦兼作家周郁芬,在香港認同秩序鬆動之際,不僅暗自發力,與日常小暴力周旋,更靈活對抗當前香港社會的巨大暴力,逐步引爆小說布局隱伏的掌心雷。小說的周郁芬,竟從潛逃與藏匿中,獲得比電影角色更多的力量。
既然人人都可能被成為恐怖分子,周郁芬便成了一名對抗恐怖的恐怖分子,而作者也帶有後設意味地,安排她所創作的小說《小暴力》,原脫胎於舊作《無盡溫柔》。在大局存亡的危殆時刻,暴烈奇異地成為一種溫柔。
因而從《恐怖分子》到《小暴力》,歷史上的暴力幽魂般不斷回歸,如電影版周郁芬預言式的文字,變化是一種輪迴,尤其對台灣與香港這般經歷多重殖民與政權轉移的地域,總有新舊勢力紛至沓來,而這對雙生島嶼上的眾人,也總會陷入類似的困境,一再遭受現代化與國族的種種危機,受迫、反抗、離散,近乎形成閉鎖迴路。然而,儘管歷史的軌跡相類,每次危機回返,卻都有一些細微歧異,從而產生打破迴圈的可能。這些逸軌與突圍,如《小暴力》顯示,始於個人於生活中做出的微小抉擇:例如在夜店牆上塗寫一首詩發聲,或從創作書寫,催生出真實的反抗行動,或在體制外隱密追索正義,爾後繩結一一繫起,個人意志或成眾志,歷史的弧度因而有了些微改變的可能。
僅是可能而已,但至大起於微末,抵禦小暴力的,正是涓滴意念。
《恐怖分子》片末,周郁芬在被槍殺的夢魘中醒來,在心悸與驚惶中,分不清現實與夢境,這是楊德昌預示的台灣現代城市圖像。近四十年後,陳慧援引楊對於城市的觀照,寫出了當代香港與台灣都會的不可測,而她所重塑的周郁芬仍持續寫作,持續在逃逸中,生長出抵禦的力量。小說結尾,周郁芬說道,她想寫一本關於「小息」的小說。「小息」是香港用語,意為課間休息時間,可以暫歇,可以嬉戲,或如安安所言,也可以是一種出走。陳慧藉此重新定義了港人送中運動後的飄零遷移,移居或可只是小息,小小的,化整為零的行動,暫時停歇下來,潛修蓄力,靜待醞釀,靜待某一時機發酵。
如此,年年四季迭變,但每個人仍會以不同姿態存活,再生。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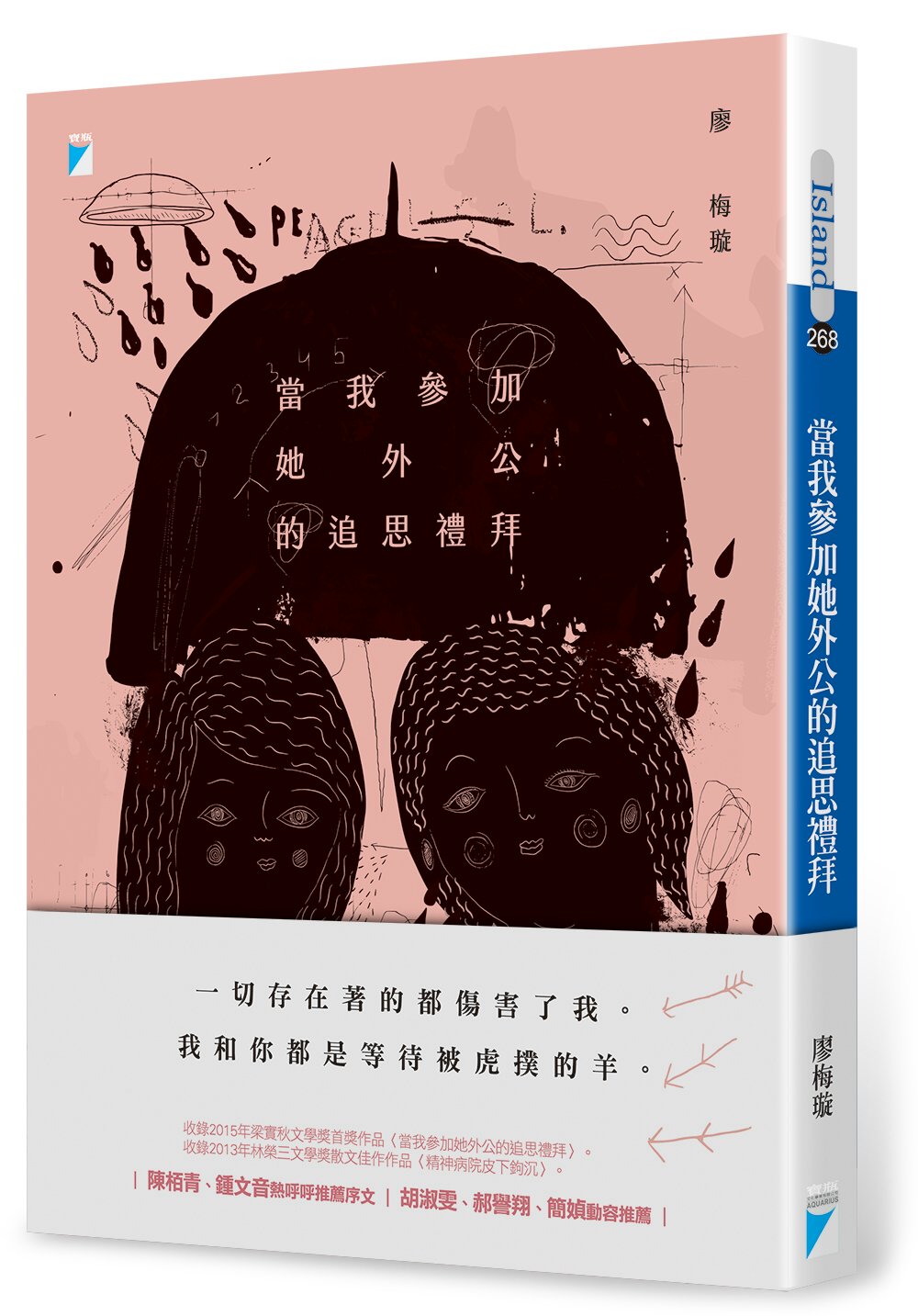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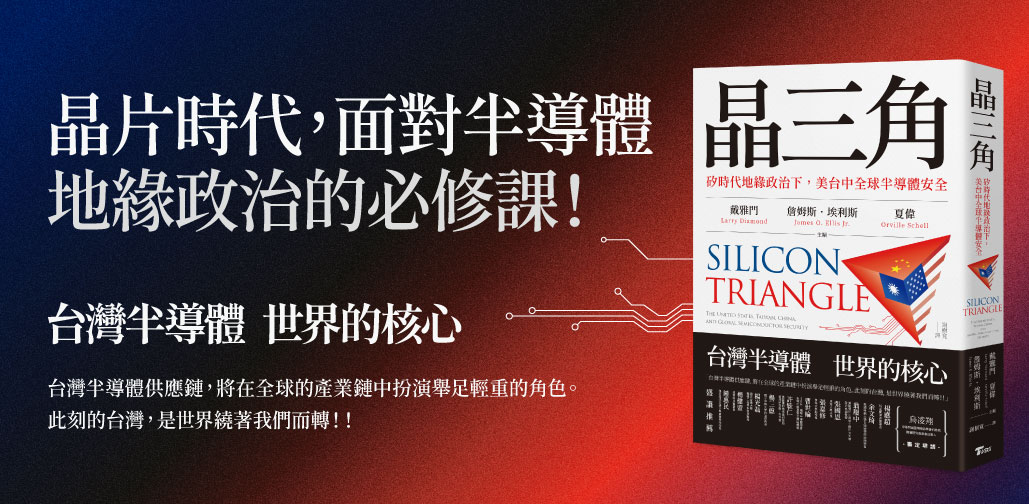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