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昭旨)
採訪當日氣溫極低,下著綿密的雨,小說家推開咖啡店的木門,先為自己其實準時的遲到道歉。離開洗手間的時候他跟店員確認,擔心自己弄壞了裡頭的燈。他脫下外套,露出紅毛衣,從飲料單選出熱咖啡,然後再度道歉,奔去洗手間脫下毛衣內的多層衣物之一二。終於坐定之後,小說家的額頭沁出薄薄的汗。他在舊沙發椅上不斷尋找一種舒服的坐姿,也可能是,眼前這座龐雜華麗、惴惴不安的世界,只能由他來鎮壓或釋放。
三個月前,《小兒子》這本書根本不存在。駱以軍這幾年在寫長篇小說《女兒》,2012年出版了《壹周刊》專欄篩選而成的《臉之書》,而回溯《小兒子》的誕生,得從2010年他使用臉書開始。因為兩個兒子要玩「開心農場」,為了讓孩子來偷菜,他開了臉書。隔年他去香港,擔任為期三個月的駐校作家,「我住在一個舊社區裡的高樓層,空間很像靈骨塔,晚上回到屋子就開始玩臉書。也差不多那時候,我的朋友陳雪開始貼早餐人,我貼香港的倒霉事。」跟創作不一樣,臉書對他來說是耍寶、搞笑,甚至有朋友寫信來規勸他;但對駱以軍來說,寫臉書像是大學時期讀完一整天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後,晚上去電動玩具店打電動一樣,是一種放鬆的方式,如同腦力勞動後的拉筋伸展。
駱以軍打字很慢,回電郵都是苦差事,他用的一直都是老婆或哥兒們淘汰的電腦,以前他養鸚鵡,鍵盤還會被鸚鵡一一叼光。20多年的創作日子,他仍舊習慣手寫。每天起床後,書包一背,裡面必備一疊白紙和筆,就踏上出門寫稿之路。「其實臉書是一回事,跟真的創作是不同的。」駱以軍說,「我養家是靠《壹周刊》,用A4紙寫稿子,再傳真給編輯幫我打字。玩臉書後有一天,編輯跟另外一個同事在看我的臉書,哈哈哈地笑得很開心,赫然發現『他會打字!』,這件事就被取消了。不過我現在還是手寫稿,會付錢請學生幫我打字,再傳給周刊。」
「寫臉書的這些時光讓我覺得,我的孩子正在離開我。」因為大兒子要考高中,開始參加晚自習,以前的駱以軍總像帶著兩隻小動物在身邊,像唐吉訶德般閒晃冒險的父子三人,漸漸有了各自的行程。「慢慢他們就大了,小兒子也要變成少年了,不會再讓我捉弄。變成我將被他們遺棄的狀況。」恰好是臉書,恰好在兒子的這個階段,人生之河流不能重來,對他來說,《小兒子》剛好是這個時間流裡的即興劇,記錄與孩子的相處點滴。

(攝影/陳昭旨)
「我很害羞,很內縮,到人群裡會很緊張,很長的時間拒絕跟世界接觸。現在即使很有經驗,去演講還是會非常焦慮。這樣的我其實不應該繁殖出下一代。」他回想,「因為我不是正常的行業,我選擇創作。30來歲時遇到各種打擊,父親過世,經濟壓力,自尊常常被羞辱,對未來充滿恐懼。父親過世後,我自己吃了非常多的苦,希望孩子如同我爸對我說的,心智要很強大,不能軟弱,要有疏離出來看這畫面的眼睛。」
他希望孩子們能把觸鬚伸展開、把眼睛打開,但對於孩子未來的想像,總是反反覆覆。希望他們寫作嗎?「像魯迅他們說的,一但沾到這個,你是個讀書人、創作者,你生命的苦難就註定了。你就不可能有錢、不可能過好日子,靈魂就要承受比別人複雜一萬倍的褶皺。」駱以軍補充,「你看我們這一輩,邱妙津、袁哲生、黃國峻,被折斷的很多,你不太知道他吃不吃得下來。可是又想,如果養成一個閱讀習慣,他生命是不是過了好幾百倍,像一個演員,內在已經跑過數十萬人的角色流動,各式各樣的進出媒介,你的極限運動。做父親會是這樣,我覺得這兩個孩子不應該吃這個骯髒活,不應該去打撈深海沉船的殘骸、不應該去做在礦場裡把挖屍體起來的人。你當然希望他快樂,可是活在這個世界快樂是什麼?我有時候覺得現在這樣也很快樂啊。」這時,駱以軍的電話響起,突然他轉換聲調,用孩子般的口氣,向城市另一端的妻子報告行程。
熬過生命各種橫逆,甚至在憂鬱症爆發糾纏的狀態下,三年半間寫寫停停地完成長篇小說《西夏旅館》,2014年下半年還預計出版另一本長篇《女兒》。駱以軍說,「我已經不像年輕時那麼恐懼,擔心自己不能寫作,經過困境,又會有好一點的時間。」被他笑稱「含金量零」的新書《小兒子》,其實是一本真正的臉之書,即使河裡的金沙都被淘進了小說裡,被遺留下來的日常之河,依舊動人且溫暖。
〔駱以軍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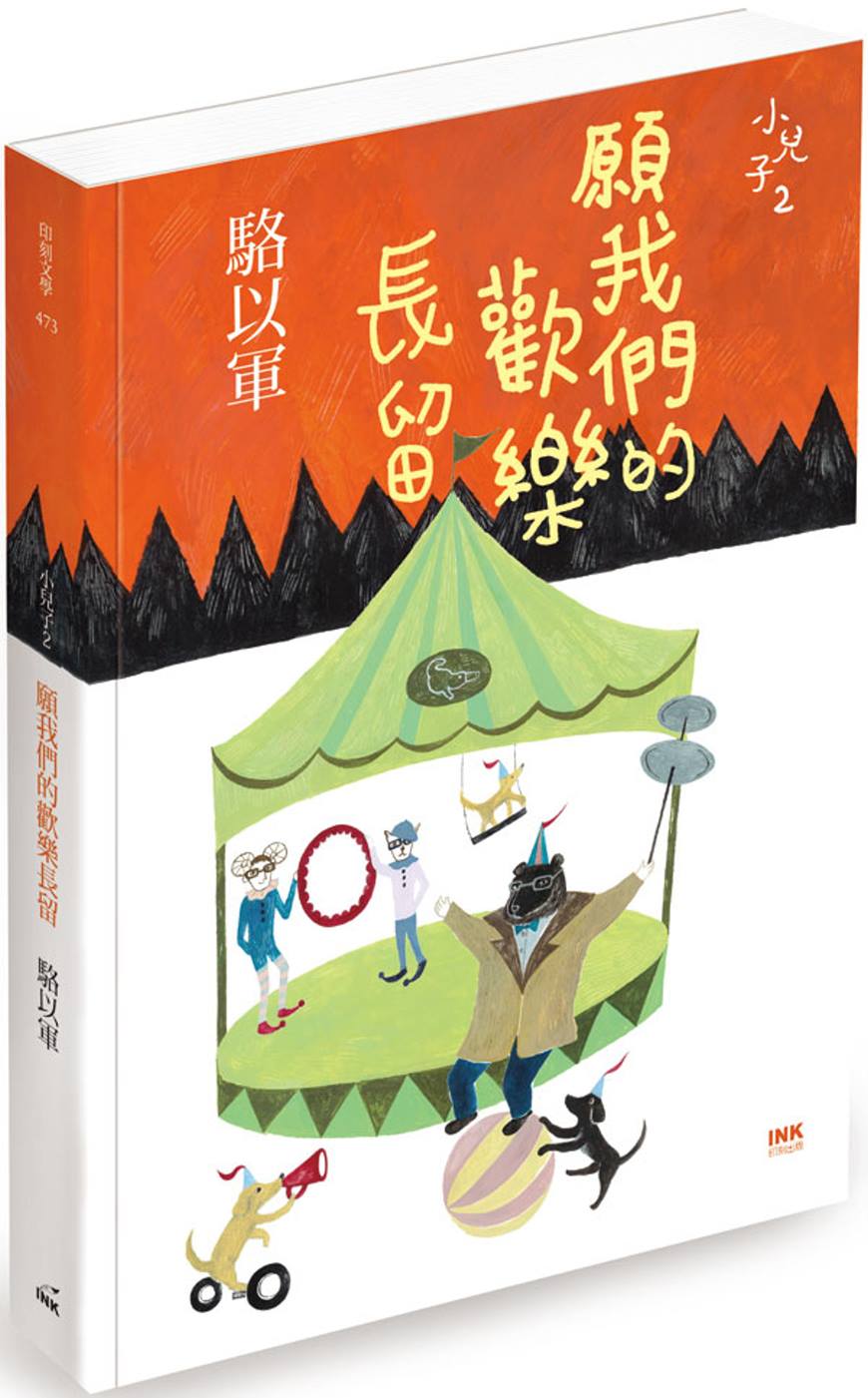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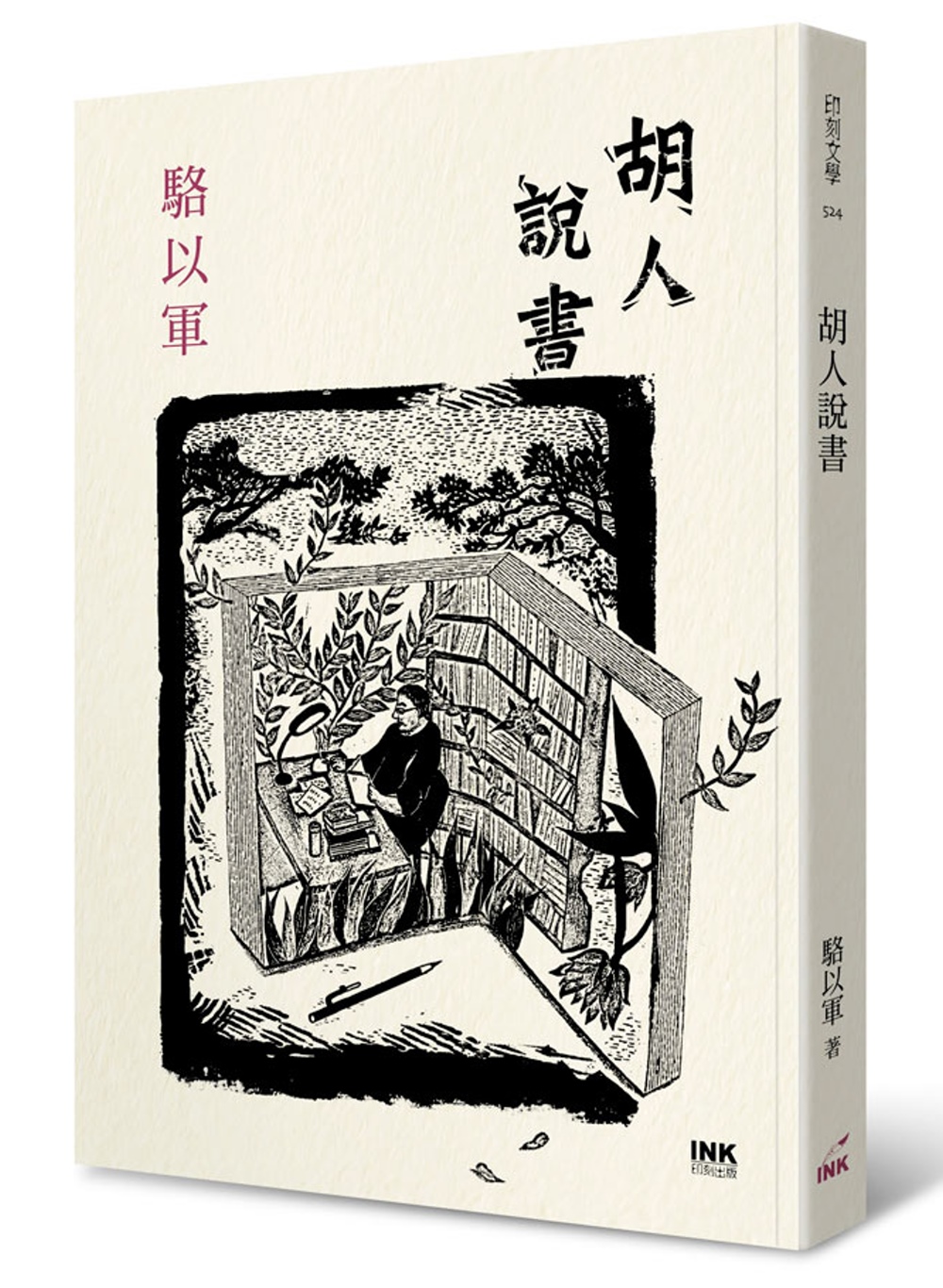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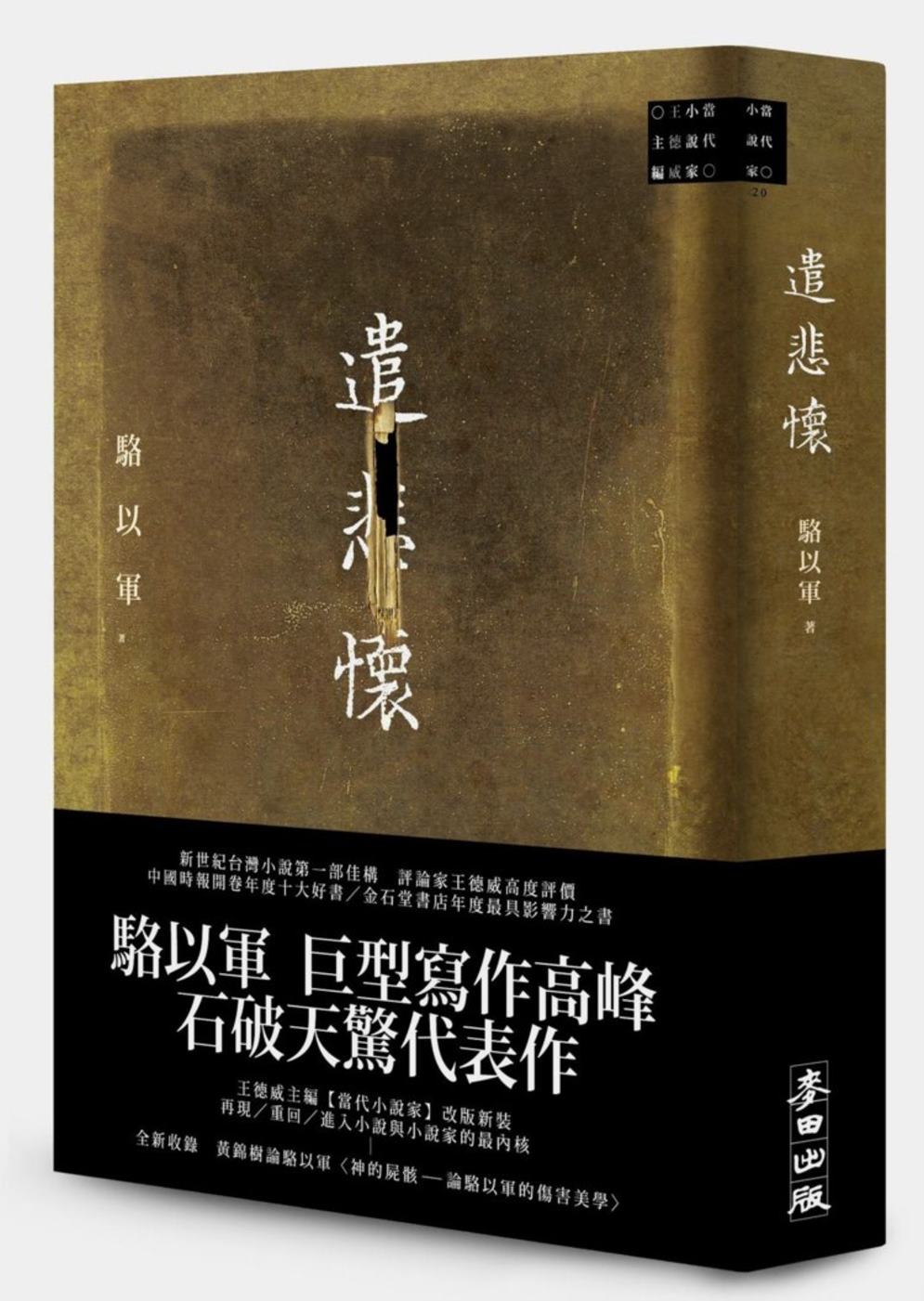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