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今年初的一次訪談,作家雷驤聊起進行中的創作,個人畫展結束後,正提筆寫著他6到16歲、少年愚騃的時光。年輕時早得文名,中年浸淫影像創作,到了年歲厚實的階段,畫筆與寫字的筆同步並進,創作速度穩定,新作《少年逆旅》,看見其從未離開創作領域,一道連續軌跡的呈現。無意刻意回首往事,作家說,這次的寫作很自然。
「寫作初始,定是從身邊的事情寫起,一路寫下來,能寫的都寫光了,自然把沒寫到的事情寫一寫。」但說到記憶,雷驤表示,記憶力其實不是最重要的,隨人生際遇對這世界的了解,才是讓往昔記憶浮現的顯影劑。「少時當下的記憶,在往後的人生,成為一種觸發,」書寫當下的好處是即時,相對欠缺的則是距離,「如同鏡頭,沒有拉近拉遠,視角出不來。」
少年,是光亮燦燦的語詞,雷驤說,這本散文集也可說是個意外,起心動念想為年輕的讀者寫點東西,約莫是12到15、16歲的一群;但所寫所舉的事物,他認為自己一向不太符合所謂的規範,也許無法合於小讀者使用;而脫開了讀者方面的考量,回歸自己第一人的寫法,寫來便天開地闊。
雷驤所經歷的少年時期,除了身邊人事如家庭校園,時代的迅速變異則是他一代人特有的際遇。短短數年,世界在戰爭中解壞重建。讀初中時,韓戰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冷戰威脅,台灣緊接進入美援,「這些時代的大事,後來如何消融?又怎麼被隱蔽了?」變化如何漸漸襲來又迅速變異,足以在人的心裡形成強大的謎團,雷驤選擇述說人的故事,隱隱記錄時代。

(攝影/但以理)
淡筆勾勒人生的重,如同他對生物學的理解,「不可能悉數揭露」;他對繪畫的喜好與開端,也被巧妙拆解隱藏在不同的篇章內。雷驤說,「之前很少有機會討論文字與繪畫間的關係。藝術史裡,留下的是作品,創作者當下的啟蒙經驗很少提及,」自我心靈的成長如何與藝術創作相互影響,是隱在集子裡另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雷驤提及早年學水彩畫,一個令他難以忘懷的經驗。學畫的第一項功課是反覆地畫上一百張畫,原來,在物資缺乏的情況底下,所感知的色彩學在劣質顏料上完全派不上用場,反覆練習求得的不是繪畫的精進,而是了解顏料的特性。多年後,他偶然在文具行購入一只荷蘭進口的水彩組合盤,發現事情「原來可以如此合理」,當下不是驚訝,而是痛恨那些曾經虛耗的浪費。
近年來,雷驤多次回訪自己曾經住過的居所,有時一人獨自前往,有時則有親友相伴。因著出書計畫,女兒雷光夏以自己的方法,透過攝影踏尋父親雷驤往昔之路。父女同為創作者,之間的交流對兩人而言是極為日常的事,「但她不認為在攝影上曾表現得傑出;因為沖洗相片,她是憑感覺抓劑粉的,」雷驤表示,數位攝影的變革讓這種「有感覺的人」得以發揮,「科學對藝術家有著很大的幫助。」
記憶中,少年的母親永遠十分忙碌,曾是個盼著母親能多抱自己一下的孩子,雷驤在等待的時間裡,為出入張羅大小事務的母親編排了許多想像出來的行程,他在〈母親的遊戲〉一篇寫到,生計窘迫時,母親約莫想放鬆一下,玩了個「假死」的遊戲,搞得他的小妹信以為真;經過多年了,雷驤理解,死亡跟生命本是同一件事,是人間的最後一個過程。他在妹妹安息的最終時速寫下親愛之人的臉龐,在告別式上記憶故友身軀上層層疊疊的物件,雷驤說,在台灣傳統宗教儀式裡,亡者如果是已出嫁的女性,最後會由她的親兄弟執槌作勢封釘。「去確定一件事,在心裡上是會產生作用的。」在召喚回憶的同時,更重要的卻是,如何遺忘的能力。
〔雷驤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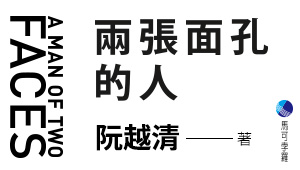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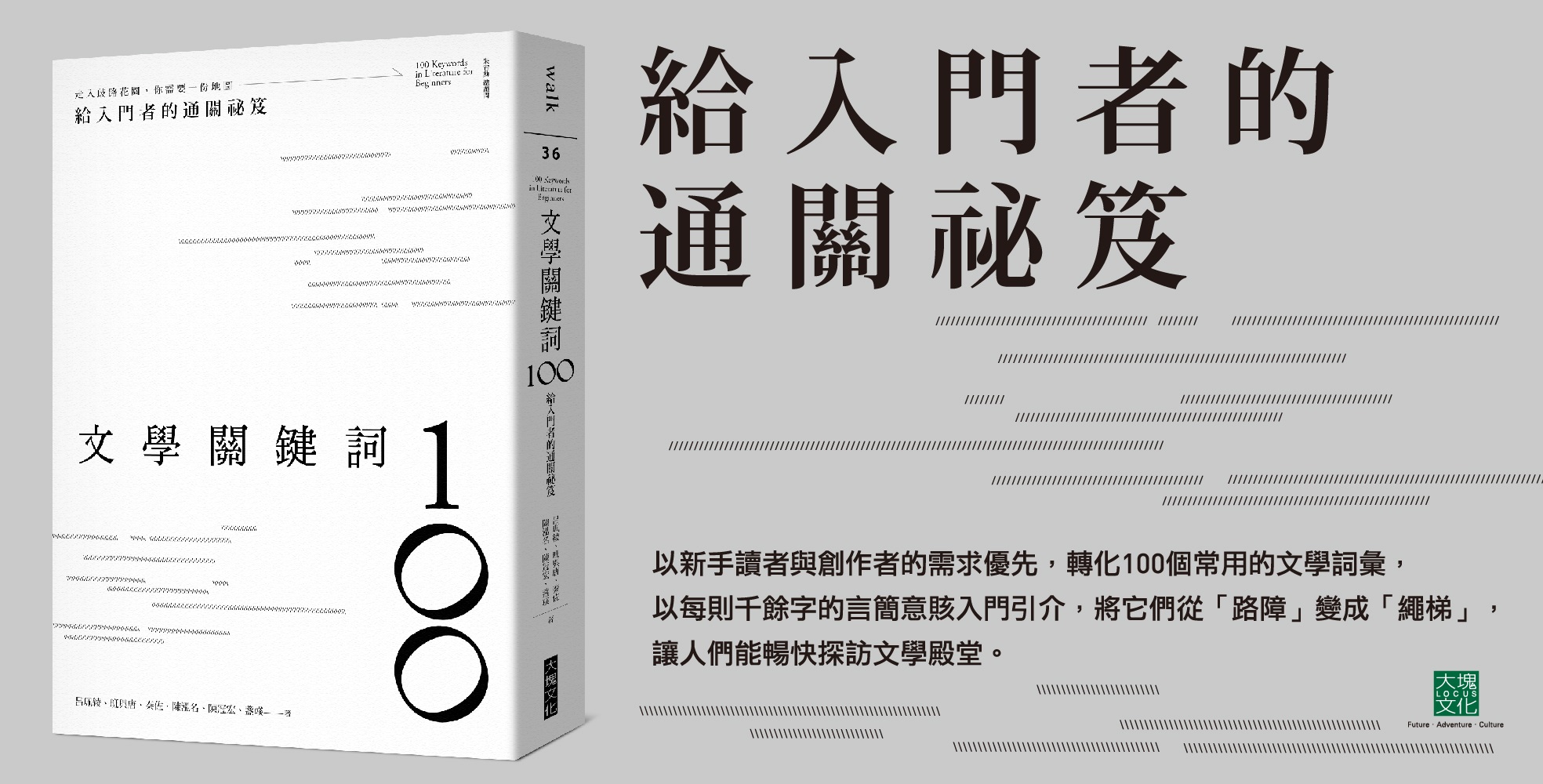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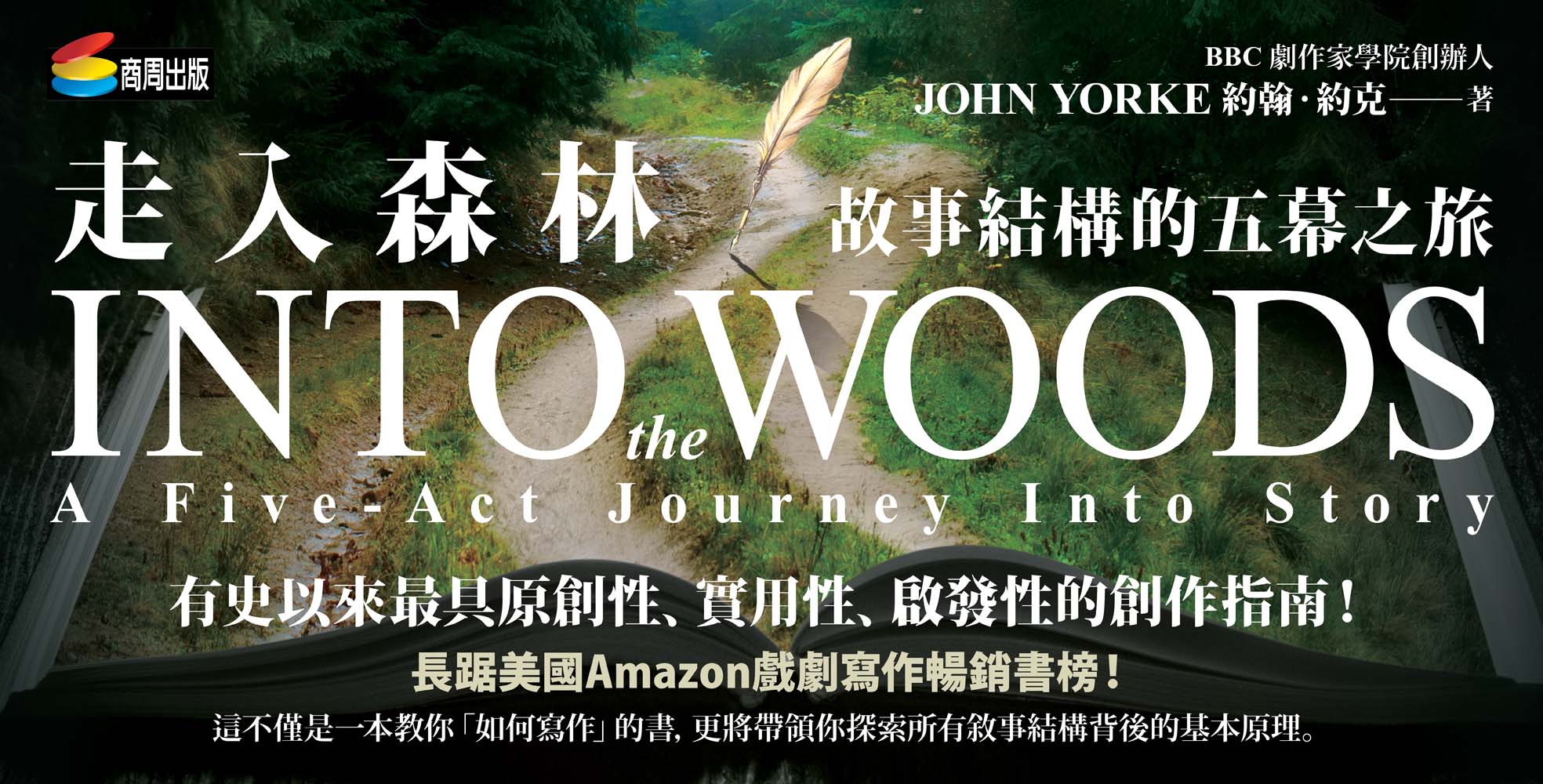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