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家姜貴(1907-1980)的反共反帝長篇小說《重陽》是個異數。它應該是台灣文學中最早的同志文本之一。我自己是在王德威的奇書《小說中國》中首次得知《重陽》的同性戀情節。王德威和夏志清(夏為《重陽》作序)多次稱揚姜貴的小說,姜貴的小說《旋風》成為台灣文學經典,而《重陽》卻長期絕版,好生奇怪。這部奇書是否也意味了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
在《聯合文學》322期的「台灣同志文學及電影大事記」中,被提出來的最早一種文本是1961年初版的《重陽》(初版:台北市作品出版社;目前舊書店較容易找到的版本是台北市皇冠出版社版,1974年初版)。我私下覺得某些1960年代之前的文本也有「同性戀的嫌疑」,但是那些較早的文本不像《重陽》這樣大白話寫出同性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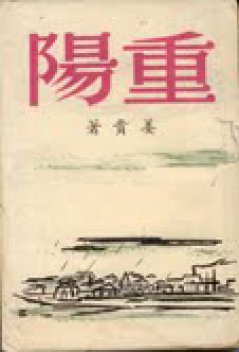
《重陽》初版(圖/紀大偉)
也因為《重陽》是反共/反帝小說,文本的首要課題是反共/反帝,同志再怎樣也要排到後面,甚或排在戀腳癖之後(書中描寫帝國主義者戀腳癖的段落不少)。同志的議題沒列在書中第一位,看起來是同志吃虧了,但我卻覺得同志占了便宜。關心同志文學的讀者並非只要留意「將同志奉為主角」的文本,而也可以「將同志列在次要位置的許多其他文本」。不堅持同志非主角不可,我們閱讀的版圖就更擴大一點。一個人同時具有很多種身份:她除了是同志,也可以是高雄人,也可以是原住民,也可以是社運健將;一個文本也可以同時展現好幾種關懷:除了是反共小說,也是呈現同志的小說,也是戀腳癖小說,也是遵守五四寫實主義傳統的小說(夏志清語,收於《重陽》皇冠版的代序)。承認人和書的多元特徵,我們看人看書的詮釋空間才不會閉鎖。

1974版(圖/紀大偉)
《重陽》書中壞人在書中確實進行了「同性戀行為」,但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或具有「同性戀身份」。我在此將「同性戀行為」和「同性戀身份」對立,的確容易讓人聯想起性別研究界長久 以來的相關討論,但我在此暫不談這個老課題。我反而想要從文本出發,強調這些壞蛋角色在書中的主業其實是欺壓良家婦女,連祖母級的受害者也遭辣手摧花,而壞蛋之間的男同性戀相形之下只是副業。如果逕稱這些壞蛋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並不見得可以讓今日讀者更充份認識他們,恐怕也找不出他們跟今日同志之間的關聯。
《重陽》寫了同性戀,但寫得跟我們熟悉的同志文本大異其趣。趁這個機會,我想提出我撰寫「台灣同志文學簡史」以來逐漸發展的心得:
台灣同志文學也有「現代性」和「非現代性」的分界。展現現代性特徵的同志文學被我們視為名正言順的同志文學,而不展示現代性特色的文本則讓我們困惑,因而被我們忘記甚或否定。我指認的同志文學現代性特徵有三:(一)將家庭視為衝突點:如,同性戀人物跟家庭/家長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發生衝突,常說出「我可以跟任何人出櫃但絕不跟爸媽出櫃」這種話;(二)將自己的內心視為衝突點:同性戀人物內心衝突不亞於跟家人和跟情人的衝突,心生自責自戀等等心緒,比異性戀人物更頻繁進行自我分析;(三)對烏托邦的渴望:同性戀人物因為長期對所處環境感到不滿,便想要脫離現有環境(「逃脫」是常見用詞),改而前往另類空間,以求在全新的時空自由發展心性。這裡的另類空間,包括外國或藥物促成的新感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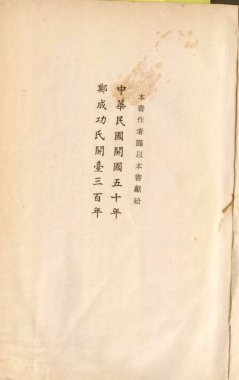
書內獻詞(圖/紀大偉)
現代性的有無,跟出版年份沒有絕對關係。我談過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也沒有展現同志文學的現代性──書中愛好男色的男醫生似乎不跟家庭發生衝突,似乎沒有內心衝突,也沒有掙脫既有環境的跡象。說他是現代化同志之前的前輩,或許算貼切。如果現代性的同志文本大抵在呈現痛苦悲情與苦悶,《玫》就在呈現同性戀的快樂,而《重陽》則在呈現同性戀的邪惡。
書名《重陽》扣合了小說正文前頭的題辭「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很有《倩女幽魂》的意思。但這裡的秋意應指書中肅殺的政治氣氛:小說背景為「寧漢分裂」,當時汪精衛在漢口成立了容納共產黨的國民黨政府。小說中充滿了大叔和辣妹以愛國救黨之名遂行色欲之實,人人疑神疑鬼,讓人聯想起李安的情報片《色戒》,只不過《色戒》中的帥哥大叔汪精衛在別的城市忙著成立另一個妥協的政權。《重陽》的文本跟張愛玲的文本也形成對比:《色戒》小說版幽微收斂,大概因為作者根本就沒有感時憂國的危機感;《重陽》的缺點和妙處則是不知收斂,人心幽微處都寫得明顯得讓人發噱,或許正是因為作者急於反共。作者在《重陽》自序寫道,「反共,需要冷靜,也需要智慧」,似乎就是在警惕自己。自序寫於「台南東門寄廬」──而不是大台北。作者跟大部份大陸來台的作家不同,並不住台北,也因而失去外省作家同聚在台北的安全感。作者晚年家庭不睦,應更有孤立無助之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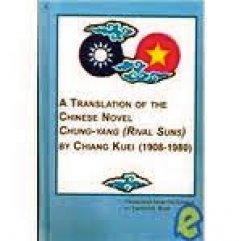
英譯版(圖/紀大偉)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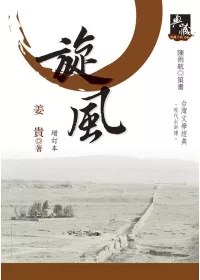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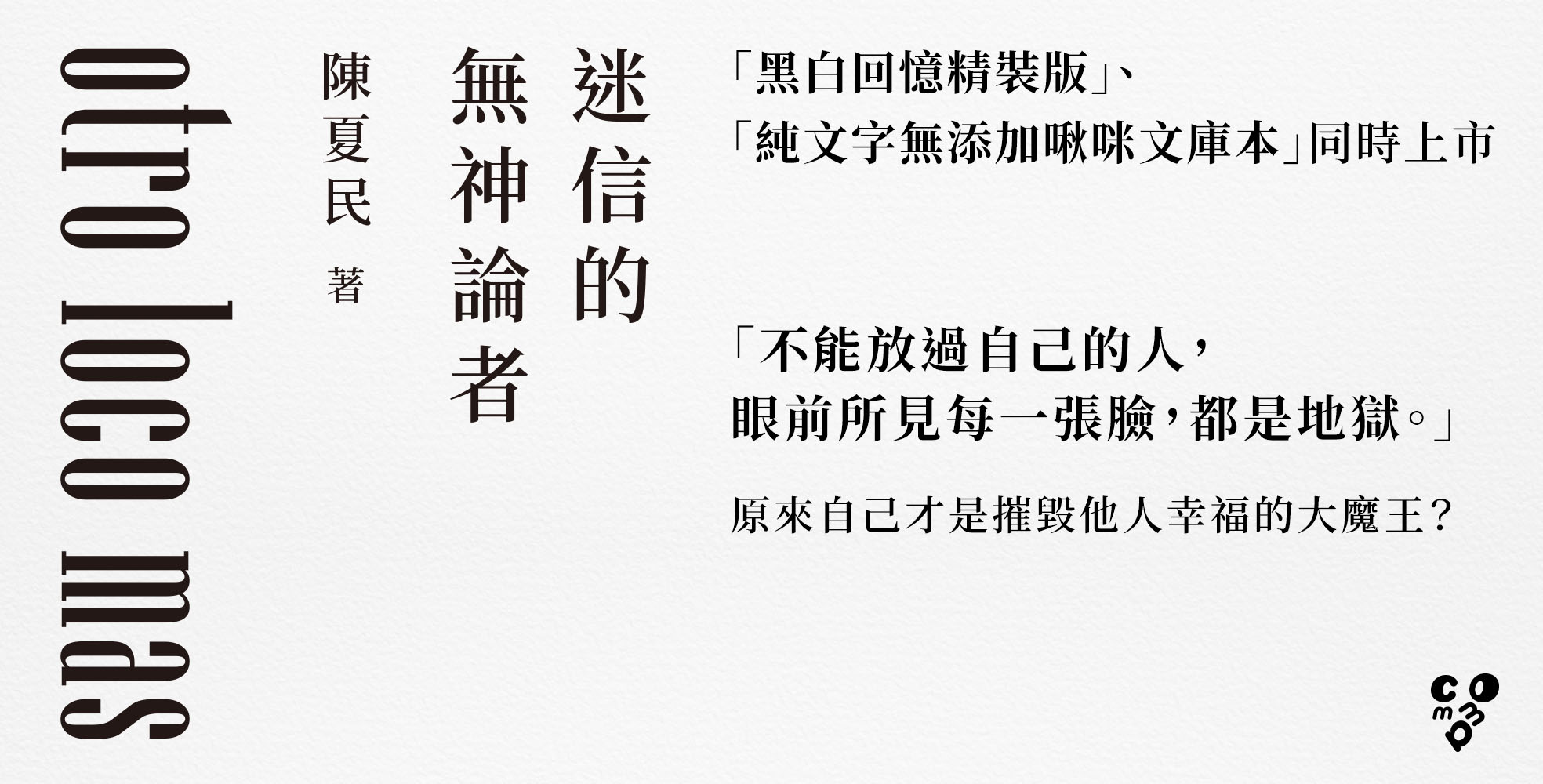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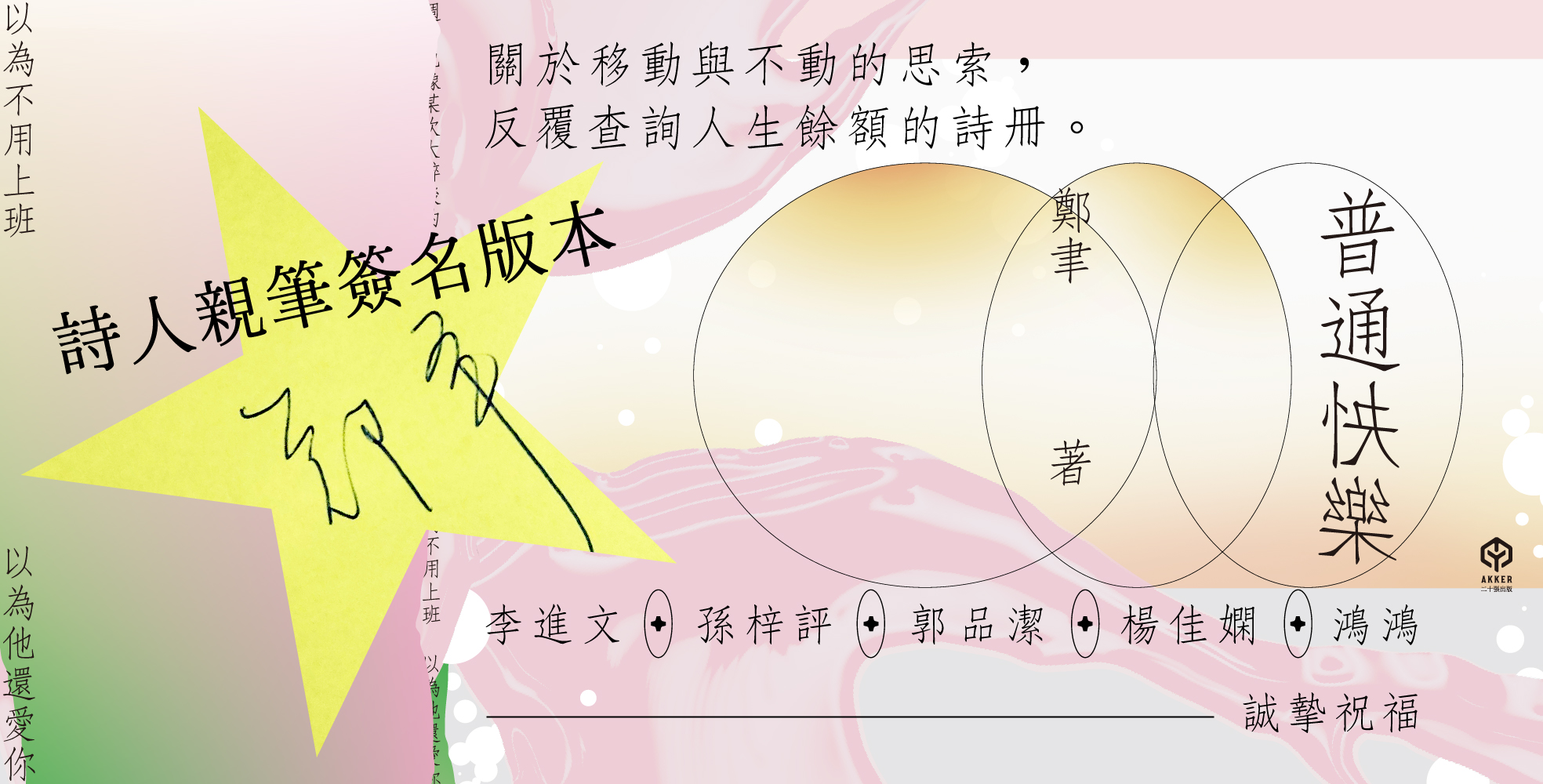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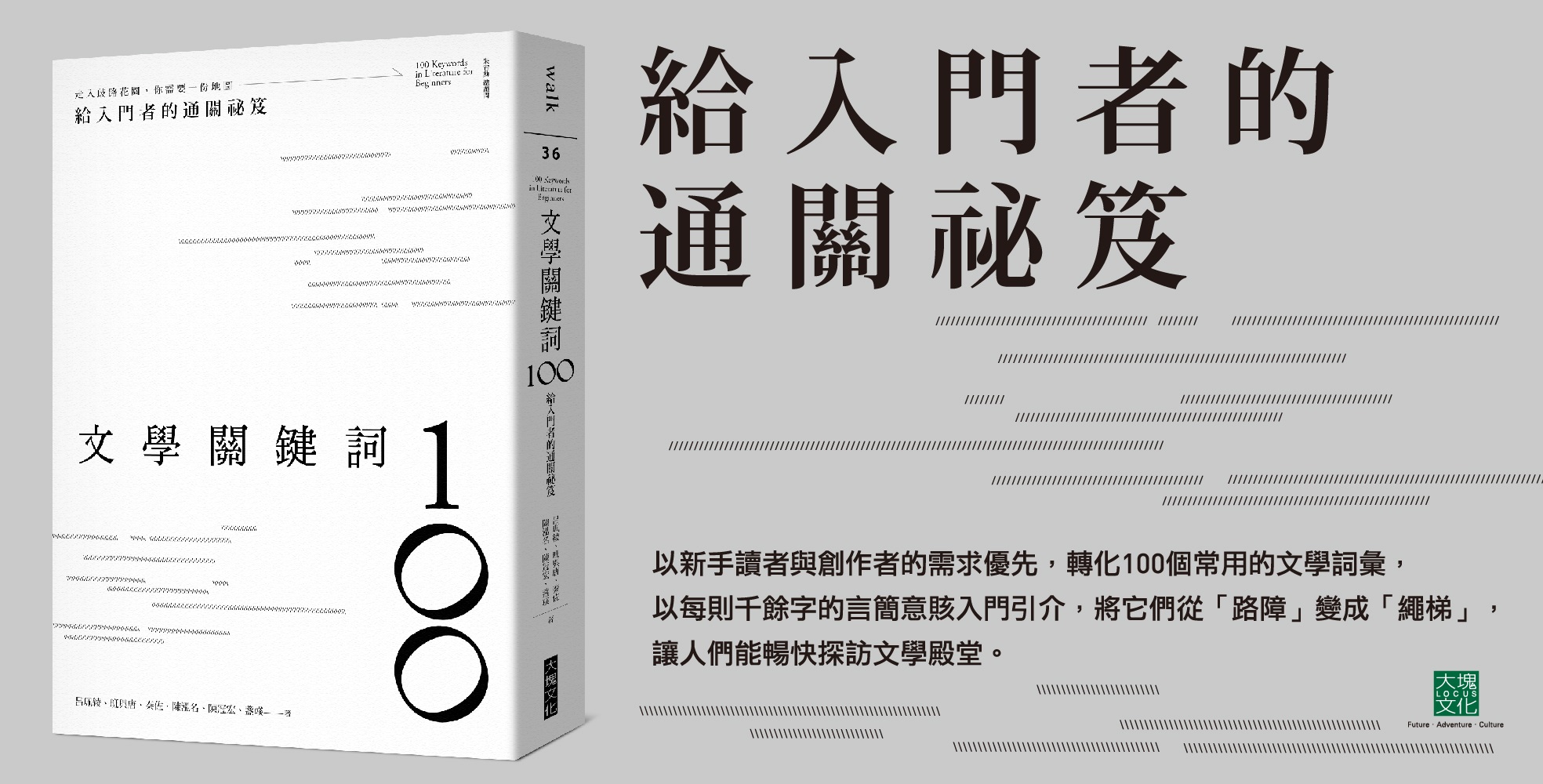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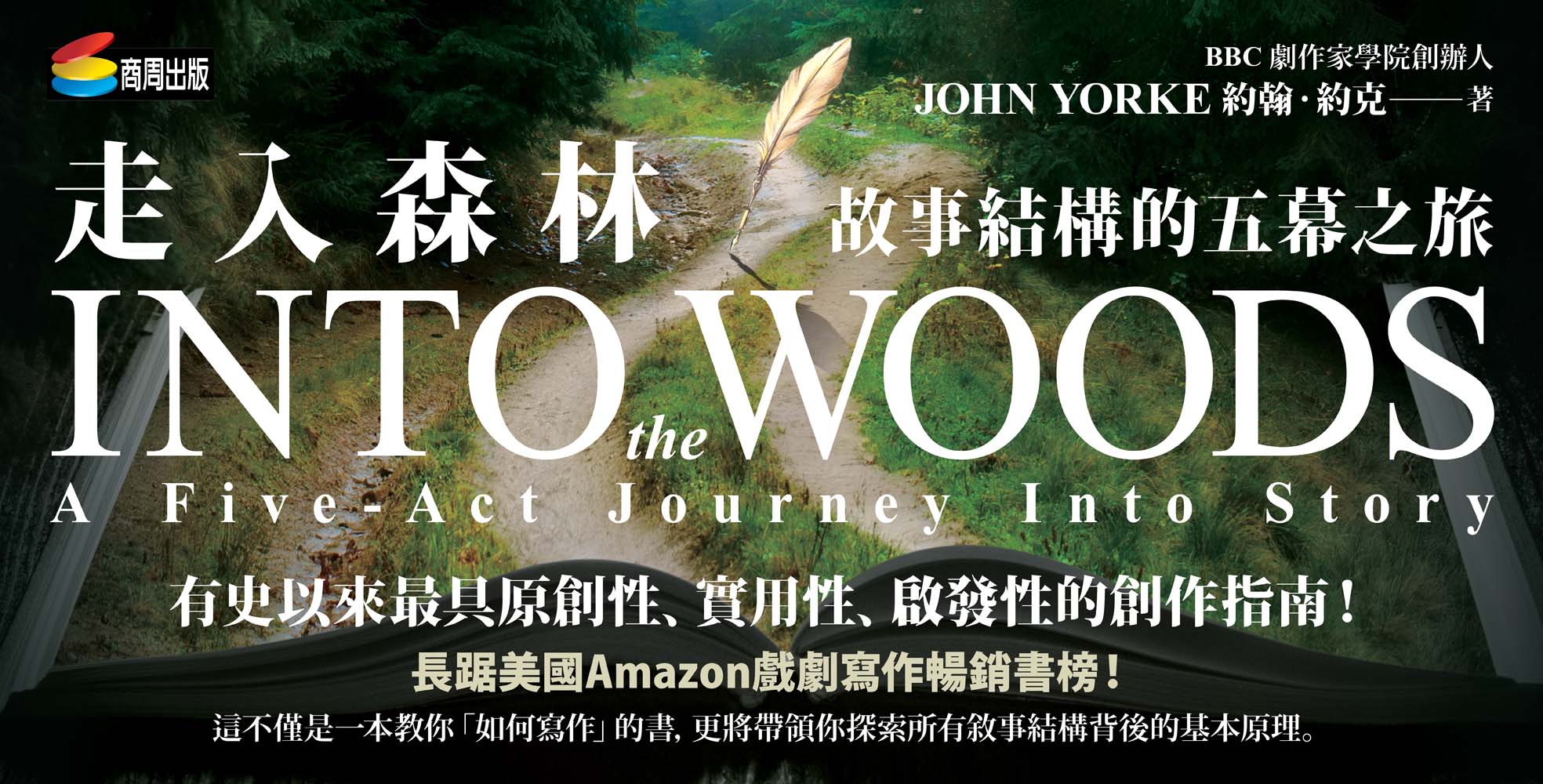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