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co Chanel,她大膽將男性西裝的元素置入女性套裝裡,她走路有風。
瑪莉蓮‧夢露,風吹起她的裙襬,從此她征服了眼前的所有男人。
張愛玲,她執起一枝筆,寫下無數過客,但她從未讓人明確讀出她的一生。
張曼玉,金馬頒獎典禮台上的她,分明有著小女孩般的俏皮,然銀幕上的她,卻讓我們窺見眾生相。
她們行走的姿態、生命的格調,致使時代縱容她們,
人們唯有崇拜她們的靈魂,
並讚頌她們是Gentle Women。
Gentle Woman,看似難以定義,卻又忽之欲出。
Gentle Woman,是一種複雜的元素,
Gentle Woman,又是特立獨行,否定任何形容詞加諸於她。
誰,是你的Gentle Woman?
文/馬欣
你還記得電影《鋼琴師與她的情人》嗎?一部在1993年曾轟動一時的女性電影,描述一名19世紀的啞女子,深受命運擺布,只能以鋼琴表達心情,琴彈得我柔腸寸斷,最後鋼琴墜入大海,代表她想追求自由的心,當時我只能買到第一排,兩個小時得歪著頭看,哭得我眼歪嘴斜,但或許也因如此,那幕鋼琴直入海底的畫面,直到現在,仍衝擊我心。
講Tori Amos對我的影響前,容我先講一下我的學生時代,當時影集《飛越比佛利》正紅,是個歌舞昇平的年代,女孩們開始買很多教人打扮的雜誌,青春期就這樣闖進我的生活。當時學校的空氣中有隱隱的噪動,如同動物星球頻道中,非洲草原的牛隻們為即將來到的大遷徙而亢奮。那時的我面對四方來的訊息「女生該怎樣……才能得到幸福」時,我感覺到落單。他們不知從哪裡來一套獲得「幸福」的SOP,卻沒人能跟我具體解釋迎合大眾標準的「美」就是美嗎?「幸福」又是誰說了算嗎,屬於我身體的「詮釋權」,為何就這樣不由分說地,被資本主義一把奪去呢?在洗腦的資訊中,我們的性別成為永遠鞭長莫及的「模仿賽」。
然我很幸運,在我成長茁壯的時期,90年代的女歌手們,承接著70年代民謠之母瓊拜雅的人文精神,一把吉他、就點一盞光地將火種唱下去。先是蘇珊‧薇格,在那濃妝豔抹的時代,樸素地唱著〈Tom's Diner〉、〈Luka〉,讓生活的真實,包括其中冷冽的部分,都被還原了。相隔不久後,Tracy Chapman 出來了,強大的原音力量,她一唱歌,世界終於安靜下來聆聽,女生們可以就此無畏地讓精神超越她們的樣貌,從此商業打造的南瓜車,我有勇氣拒絕搭乘。
但在眾家女歌手中,最難忘的還是 Tori Amos。這女歌手在1992年出了《Little Earthquakes》,我仍記得那是個炎夏,她來台演唱。我記憶中,沒有人像她這樣彈琴,一身火焰般的紅,身體跟著音樂共震著,彷彿從地心嘶吼出的力道、隨即又是直通天聽的清亮,在〈Silent All These Years〉,她唱著:「你驚訝一個女人會深思,這有什麼稀奇的……我一直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這些年的沉默啊。」多年來,她唱作題材包含女性主義、性、宗教、父權等,那些壓抑錯結的,她俱是以鋼琴譜成一羅網,由歌聲破繭而出,一次又一次,直到妳也夠勇敢地唱出自己的沉默。
我們如今置身在一個「去醜化」的世界,「規格化的美麗」四處擴散,直奔到一個大家都長一樣的「美麗新世界」,但我至今仍難忘Tori Amos這麼文雅的反抗,她會赤腳踩在琴鍵上,如在夜露般輕盈,譜寫的歌詞又如夜中的貓眼這樣通透,「這多年的沉默啊!」她說,帶我回到那鋼琴落水的觀影剎那,我們還要沉默多久呢?

多年寫樂評也寫電影,曾當過金曲、金音獎評審,但嗜好是用專欄文偷渡點觀察,文章看似是憤青寫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說的),但自認是個內心溫暖的少女前輩(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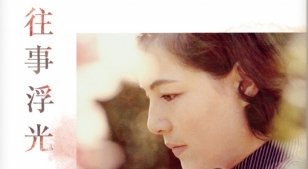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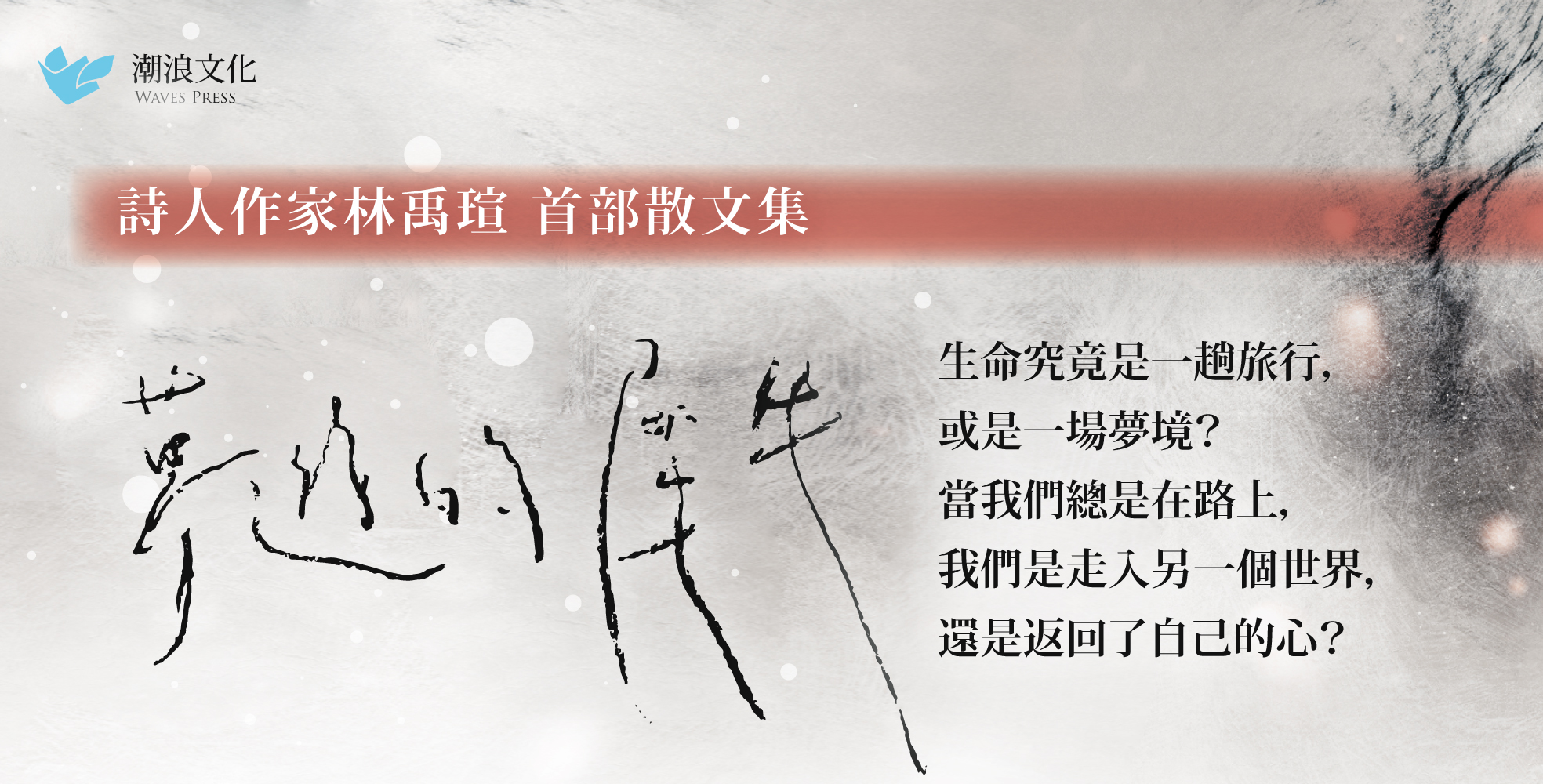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