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在開始論及新書《裸命》之前,香港作家陳冠中,先給我們說了一個故事:
「唐代有個歌女,名叫絳樹。她一張嘴,可以同時唱出兩首歌,而且兩首都唱得很清楚,是謂『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陳冠中曾於2006年一篇文章中提到絳樹這個切入中國的比喻。「我們談中國時,往往需要這樣的技術。」
這是陳冠中決定用小說這項文體來敘寫現世中國的起因。
多年來,陳冠中持續關注兩岸三地的社會、城市、媒體、文化等議題,也是少數曾在中港台三地都長時間居住過的香港文化人。「我出生在上海,4歲時搬到香港,一直到40歲那時因為工作,去北京住了3年。那是1992年,正巧是鄧小平南巡、中國開始開放的時刻。」那一回的居留,讓陳冠中決定日後要在北京做點什麼,但1994年他又輾轉來到台北,一住就是6年。「到2000年時我決定搬去北京,一直到現在。目的就是想寫書,想寫中國,想參與這次中國的『大戲』,看看他們怎麼發展。」
2000年的移居,雖不致於讓陳冠中變成中國這場崛起大戲的一員,卻也讓他從場外看大戲的一般觀眾,轉為進場近身貼著演員們的記錄者。原本他試著用文化評論的角度書寫他眼見的中國變化,怎麼寫都還是有掛一漏萬之虞。「用文化評論來講中國,不是說好就是說壞,很難把好壞同時說清楚。」但眼前種種著實太過複雜,「說了一項,還想到後面有二三四項沒講,好像怎麼也說不完。」非小說的寫作,往往不容許書寫者面面周全,更無法讓人事物的矛盾、斷層與不連貫並存其中,但這些卻是現實所有。後來他想,也許小說能提供更大的空間,把這些看似對立的人與事同時放進去,讓讀者去捏塑中國的樣貌。
於是他終在蟄居8年後,於2009年寫就《盛世》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甫推出即大撼海內外,至今已有13國版本,成了國際間窺看中國近十年變化的共同文本。如今,他再推《裸命》一書,敘寫漢藏之間纏連不斷的糾葛與衝突,為的是補上中國盛世當下的其他面向。
「西藏是我想了很久的題材,但在《盛世》出版之後,我才決定要回頭寫它。」回溯起自己與藏人的緣分,約莫是在1980年代後期,因為某次電影工作,陳冠中認識了一位仁波切,跟著他學佛,也跟著他走過不丹、尼泊爾、中國藏區等地,結識許多藏人。「我的朋友除了漢人之外,最多的就是藏人。」後來在北京,陳冠中又因緣際會頻繁往返拉薩,藏區的發展、衝突與事件,以及藏族人的心態變化,都看進他的眼底。「漢藏關係時而友好時而緊張,2008年後就愈來愈糟糕,尤其2012年。」2011、2012年,在那些狀況最激烈的時刻,陳冠中依然進出拉薩。他在2012年初開始寫《裸命》,「我一邊寫,西藏一邊發生事情。」寫下的,完全是這一年的背景與氣氛。
然《裸命》並未直接談論西藏問題或漢藏關係,而是以性為引,以成長為線,書中諸多男女情事的敘寫,露骨中別有隱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覺得必須要用性來寫。」陳冠中總是認為,漢人雖然稱藏人是自己的「兄弟」,但那種依存關係不像手足,更像是男女間某種性關係,還是最為糾纏難解的那種。「漢藏兩方互相需要、互相依賴,又互相傷害,幾乎是民族跟民族間、很奇異的性的關係。還不是夫妻或情人那麼簡單。」兄弟是親人,但以性來維繫的男女不是親人,沒有血緣,可以需求,又隨時可以斬斷。「甚至雙方的情感位置到底在哪裡?是性靈合一還是分開?」

(攝影/但以理)
不論是像主角強巴這樣與漢族頻繁往來的藏人,或是對藏族有利益需求的梅姐或其他漢人,身處在異己族群中,最核心的動念到底是什麼?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在相處上又有何等微妙?「藏人跟漢人不是每天都在抗爭跟打架,他們也有他們祈求的事物,也有自己希望的快樂,這才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對陳冠中來說,這些都是實際組成中國盛世的一部分。
小說屬於虛構的文體,但虛構的呈現,往往更貼近真實。於是陳冠中讓自己化身擁有兩歌之技的絳樹,「事實上,要把整個中國說清楚,一次唱兩首還不夠,得把所有不同的雜音混在一起,才能聽出個道理來。」《盛世》因內容觸及敏感,無法在中國正式出版,卻早有中國讀者自行打字,將全書內容上傳網路、供人下載,雖是觸犯著作權的行為,陳冠中卻希望也會有人繼之將《裸命》也丟上中國的網站,讓更多人、尤其是身在中國這場大戲裡的演員們,看見中國實際的面貌,進而思考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
中國之盛,已是不可免的國際事實,然中國的內在,是否跟得上外在的興盛膨脹?實與中國息息相關的港台,會受到什麼樣的擠壓,又該從中國的關卡與變化中,找到什麼解套良方?這都是陳冠中近年最大的焦慮。這股焦慮急速染白了他的髮,也正是這股焦慮,迫著他加快腳步,用寫作參與中國現在的發生。只因為他相信,小說可以是談論中國的共同文本,只要開始討論了,開始面對了,或許找到出路與答案的那一天,就不遠了。
「我相信書是有這個力量的,有自己的小腳,到處走的。」陳冠中如是說。
〔陳冠中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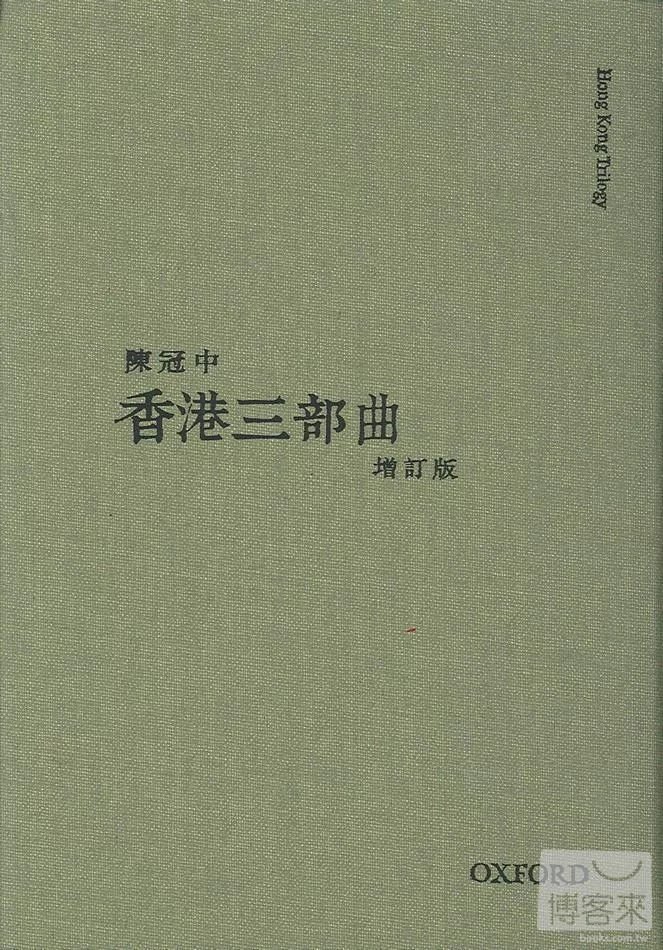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