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青蚨子》是一本傷逝悼亡之書。
小說劈頭便引《搜神記.青蚨》,靑蚨蟲母子不相離,傳說以母青蚨或子青蚨的血塗錢幣,錢用出去還會回來。乍讀令人困惑甚易忽略,經連明偉解釋才明白,他擷取的是青蚨母子鮮血相吸相引的意象。少時便失去母親的連明偉以子青蚨自況,藉由書寫,尋找母親的身影與故土家鄉,「母親是一個容體,用以填充的,是這個故鄉。」
小說的構思啟動於2009年,2014年完成後又花去兩年修訂,緩敲慢磨,終於產出這部高達40萬字的長篇。故事從一場為選舉造勢而辦的墓仔埔路跑活動伊始,在這場競賽中,小說兩位頑童主角「金生」與「羊頭」登場,也越墳踩碑地跑出了故事主場景──有餘村。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以鄉村為舞台的成長小說。從異鄉番茄街到故鄉有餘村,初始原本依著前作《番茄街游擊戰》的頑童浪遊基調,但寫著寫著,連明偉意識到應與舊作有所區隔,於是他如摺紙般,以密麻交織的傳說、方志、經文摺出了三個次元,分別是:有餘村,陰界,以及藉由「生死簿」所開展的「取消時間與空間界線」的有餘村,這三部分彼此映射套疊,既非平行亦非交錯,而是讓三者在敘寫摺疊的過程中相逢,讓「小說」成為一個記憶和歷史的載體。
小說中稍可辨識的情節,是金生和死黨羊頭、以及羊頭的瘋癲老爸「羊先生」,他們鎮日無所事事四處遊蕩,卻意外得知陰間的大秘密,七爺、八爺、土地公、土地婆等一干神仙鬼差,為了丟失的生死簿翻天覆地,在無有古今的有餘村裡,陰陽也泯沒無界,人鬼相伴相生。連明偉用一個個故事,將成人/孩童、古代/現在、陽間/陰間的世界相接,敘事聲音巧妙轉換,又雅又俗,亦莊亦諧。「我是透過書寫認識我的鄉土,堆疊所有想寫的主題,用一種我認為是有機的方式堆砌。從原本的『鄉土』折射出更多可能,包含了記憶與未來的延展,我想努力寫出一個更具體的、不只是物質性的鄉土空間。」
由此,小說中可見鄉土底層的日常生活,再串以陰界鬼物的插科打諢,而生死簿中描述的歷史風物,其實是連明偉試圖重寫《噶瑪蘭志略》的〈物產篇〉,以物言史。書中的底層人物來自連明偉的日常生活,「我住在宜蘭頭城老家,周遭完全沒有年輕人,都是小孩與老人。他們都是社會中的底層,有時候會和我分享生活上的瑣事,書中提到的性和欲望,都是他們展現生命力的方式。」
為呈現角色們的「氣口」,小說約有十分之一使用閩南語文,用字參考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雖然也曾考慮不懂閩南語的讀者,但為形塑角色生命,仍在兩種語境中精心調配,「雖然可能會造成隔離,但應該還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邊緣中,放入的閩南語比例,我是思考過的。」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陰間鬼怪也是本書一大特色,寫完小說後,連明偉才意外翻閱到清代鬼類諷刺小說,分別是張南莊的《何典》、劉璋的《斬鬼傳》與東山雲中道人的《唐鍾馗平鬼傳》。鬼怪戲謔早有歷史可循,他發現自己筆下的魑魅魍魎竟與這幾本古籍隱隱相似,卻遠遠不及古人的想像與瘋癲,他認真閱讀後也回頭修改部分小說細節,承襲了以古諷今,以鬼言人的文學傳統。
在史地部分,他參考《噶瑪蘭志略》、《噶瑪蘭廳志》等方志資料,然他並非為了創作而讀,早在大學時便曾接觸,返鄉後也因為對蘭陽地區的歷史感興趣,長期涉獵。有趣的是,雖然他上天下地串接各種宜蘭地方史料文獻,卻在鋪疊敘事的過程中將之一一消解,似乎正嘗試一種「以故事言說故事」的技法,讓讀者先入霧中,歷經上天下地的小說遊歷,陪以時間,投以耐性,讀至最末才領略此一巨大的傷逝對象,便是母親。小說中三次出現「紙紮人」、「紮人紙」、「人紙紮」的段落,彷彿不斷回返的夢境,重複續寫母親離家前離家後、亡前亡後、成鬼前成鬼後的時刻與細節,讓逝者在故事裡繼續存活。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相較於同輩作家在學院或在出版界接案討生活,連明偉在寫作之外的日常顯得入俗,他畢業後先去菲律賓教書,再到加拿大當木工和飯店服務生,又去了夏威夷做餐廳服務生,回到台灣,先後當過桌球教練、救生員、攀岩教練……「因為想要寫作,我就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很簡單,一個月大概花3000元。」這些經驗自然成為他的寫作素材,但他並非為了寫才做這些工作,「我是想嘗試不一樣的生活,了解社會上不一樣的人。」他預計在下一本書再次前往異鄉,拾回在夏威夷認識的一群人,「我在夏威夷認識一群福建移民,他們因為想定居在美國,所以想出各種方式,包含打官司、跳機等等,我想寫下他們的移民經驗。」
「我並沒有將寫小說當作一個志業,只是有很多故事想說出來。」就在連明偉帶著我們重遊其繁複的小說世界之後,訪談最末,他突然蹦出這句話。然而,他卻也是如今少見的寫作者,在海邊的老家靜靜生活,晨起閱讀寫作,每日產出字三千,靠一點打工收入過活,如此一字一字攢出這個荒唐世界中的有餘村,訴說那些無盡的故事,無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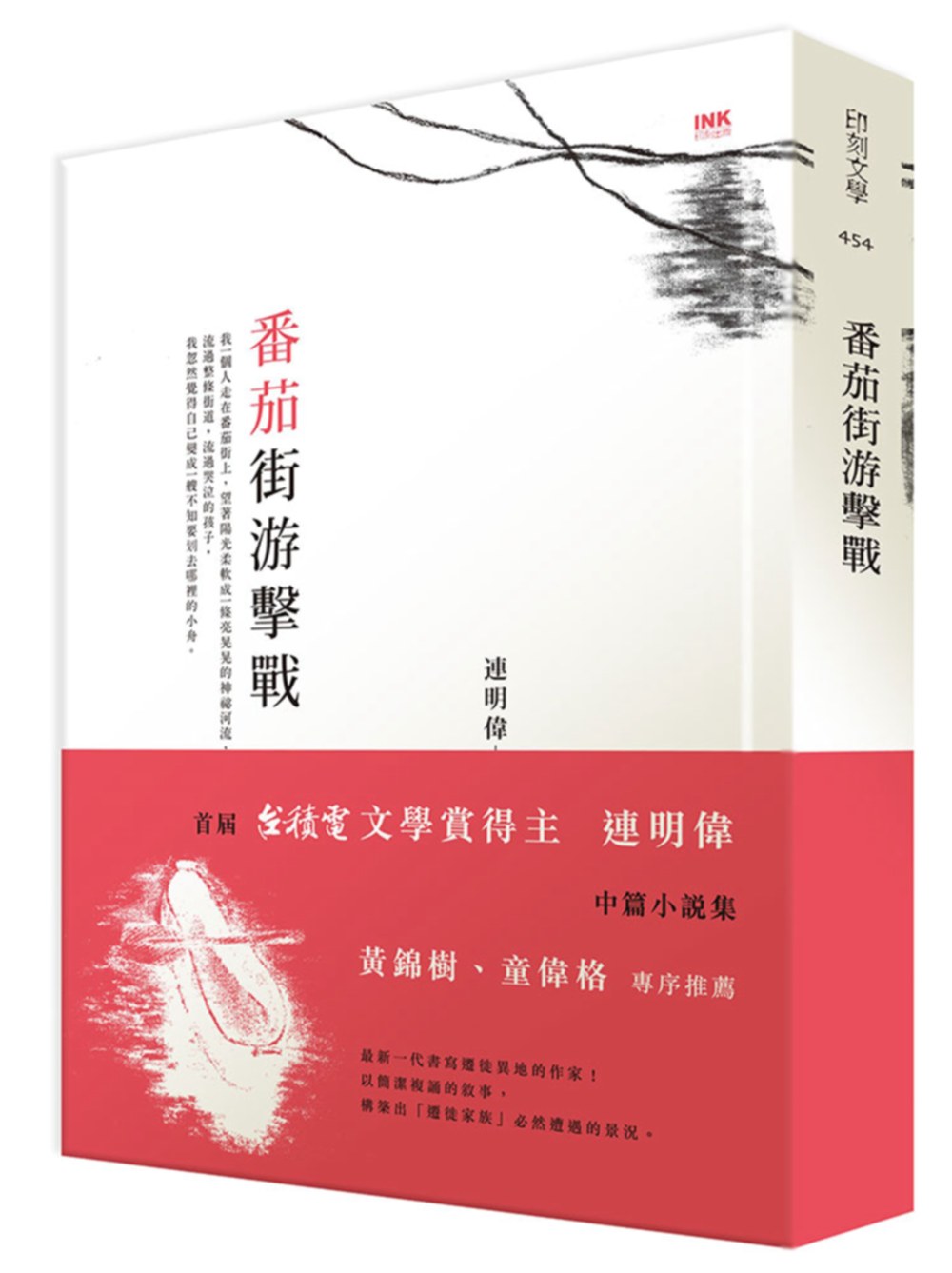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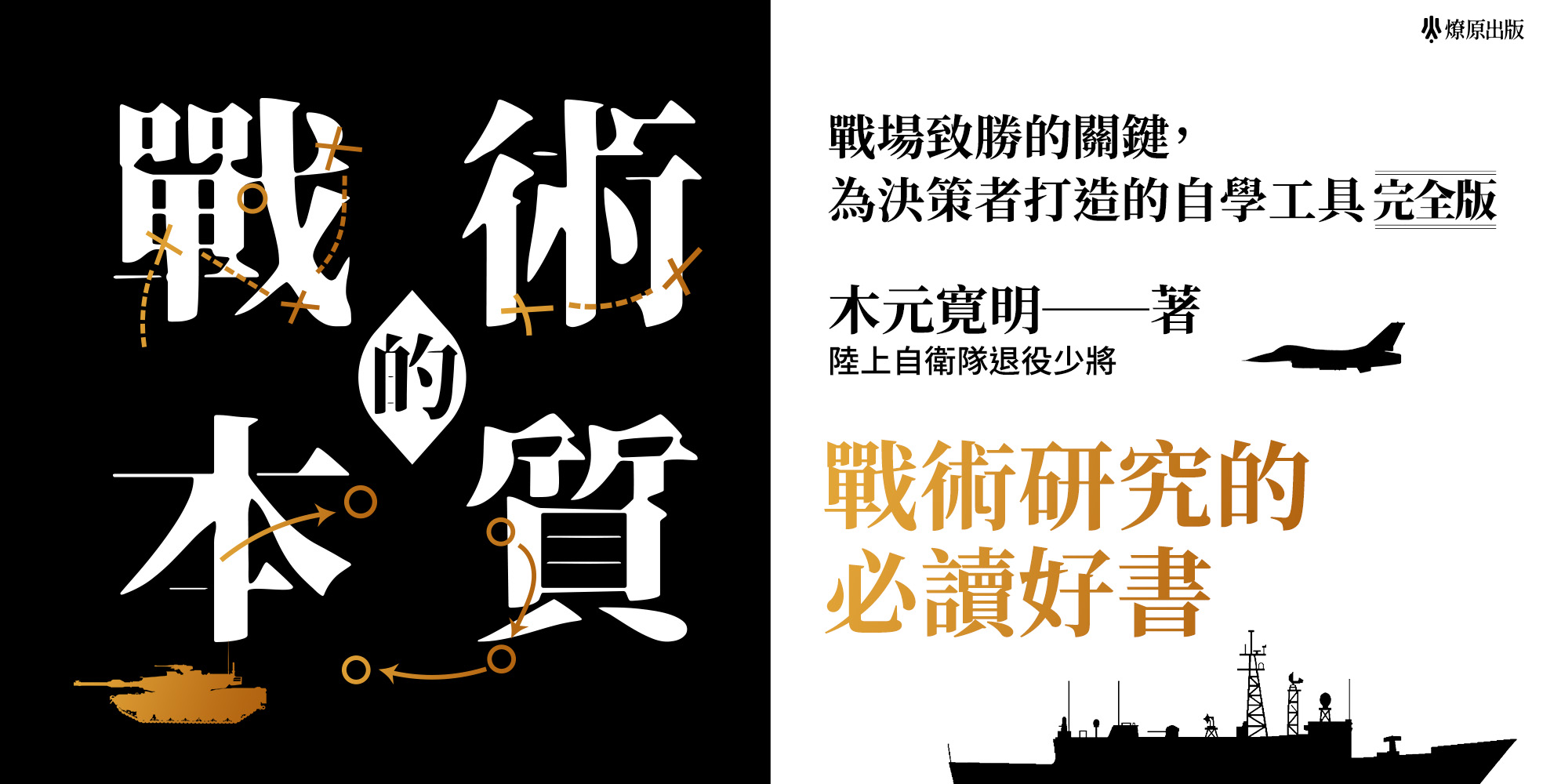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