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幾存
在討論華文創作的年度之最前,我們細細地爬梳了今年的華文創作出版品,發現往年通常是小說較為讀者注意,然而,今年散文的表現相對地突出。也因此,在討論的過程裡,有好幾本散文書名被我們提及,其中這本在今年初出版的散文,最常被提出討論:「我覺得作者的文筆真是好得沒話說。」、「這是我今年讀到最好看的一本書,每次重讀都有不一樣的感觸。」、「在字裡行間可以感覺到作者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如果錯過了這本書,真的太可惜了!」
這本被提出的散文,書名也的確私密;這本書,是梁文道的《我執》。
《我執》裡頭的文章,最早出現在香港一份發行量很少、即將走到盡頭的刊物上;這系列以〈祕學筆記〉為專欄名稱刊載的散文,意外成了當時香港讀者如染癮般追看的熱門專欄,為本書作序的香港青年作家鄧小樺說:當年他們每每談起這一系列文章時,都會激動得語無倫次。
本書初始,像是一位男子的閱聽筆記,他述說了自己的生活片段和閱聽經驗,他談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王家衛的《春光乍洩》,描述Edward Hopper的畫作裡那靜謚的憂傷氣氛,談情歌和其帶來的幻覺,他也聊到創作者在作品與現實當中的截然不同的面貌......
當然,討論「年度之最是否要選擇一本散文」時,也出現了這樣的自問,「散文寫的常常只是作者個人情感... 這樣的內容,適合選成『年度之最』嗎?」
一個散文家寫「我」,大家當然覺得「這就是作者本人」。這個關於「我」的執著、這個創作者與閱聽者之間約定俗成的文類默契,梁文道自己其實是瞭然於心的;於是,在寫《我執》的時候,他決定要試著去撼動一下這樣的默契。
所以,翻過越多頁《我執》,我們會開始發覺,這些始終語氣平靜的文字,在半年的與日推移裡悄悄地轉變......那個書裡的「我」談到自己生活的比例逐漸放大,開始有一個在其生命中出現的角色也同時在文字裡現身了,開始有些再也藏不住的情感滲入其中,他還是一樣閱讀一樣過日子,而那些挫折和思念,痛苦及懺悔,以一種近乎告白的方式,被寫了下來。
從某個層面看,《我執》是本無庸置疑的散文集;但從另一個層面看,《我執》也是以一個專欄作家為主角的小說。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口氣讀完這半年的文字,也可以若斷若續、甚至隨興而至地翻開一篇,沉浸在梁文道散文式的精鍊漂亮的文字裡,例如──
八月二十日〈無名之傷〉裡,梁文道寫著:凡傷口皆有名號,因為它能指認出造成它的原因。但有一種例外:「比如說有這麼一種狀態,你會在日常的對話中突然啞口,不知下一句應該怎樣承接;你會在回家的途中突然迷失,無法辨認本該熟悉的景物座標;你還會在現實的生活裡面毫無預兆地臨時陷進空白的世界。.....我們所說的這種空白不只沒有名字,也發不出任何聲音,它是沉默的傷口。」
十一月二日〈深度〉裡,梁文道談到讀語言學經典《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時,「上下」這組空間方位的說法:從「分數上揚、分數下降」「情緒的高漲、低落」我們發現,這組詞除了空間方位也包含了價值意蘊的隱喻。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說「愛得有多深」而非「愛得有多高」呢?「愛,終究是深沉可怖的。我們每日測量自己對他的愛欲深度,就像下潛海溝,不見天日,不知何處方為盡頭。深得令自己恐懼。」
又例如,十二月九日那天的〈追逐〉一篇的第一句話是:「曾經,所有溝通都是延滯的,都是過去的殘響。」這是戀人們仍以實體信件互訴情懷時的心理狀態;隔日,他則寫下了手機簡訊對愛情產生的作用──我們需要「時間」建立「關係」,是故,愛情當中的時間,在《我執》裡便被反覆書寫。在書裡,我們讀到從前的書信往來裡,漫漫時間裡等待的心境,也同時讀到在這個一切即時的年代,愛情消失的速度可以有多快。「從前很多事都有『恰當的時間』應該發生,現在一切即時、一切同步,每個人都不再有完整的故事了啊。」年初訪問時,梁文道便曾說出了這樣的感慨。
書中的「我」當真就是梁文道嗎?或者這正是他口中想打造的似幻似真的寫作實驗,試圖動搖某些被習以為常的慣例?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這個已經被模糊的界線,似乎不那麼重要,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並不打算計較這件事。或許所有的情節都是假的,但所有的情感都是真的。
如此,我們終會發現:閱讀《我執》已然成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經驗;無關文類實驗,無關字裡行間提及的豐富作品閱聽經驗,而是一種觀看日常的視線,他看得如此冷靜,但寫得如此溫柔。
這是一個喃喃自語百轉千迴的愛戀紀事,也是一篇篇文采滿溢渾然天成的私密散文。
這是 2010 博客來華文創作的年度之最,我們選擇的,《我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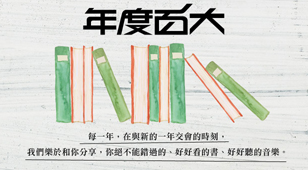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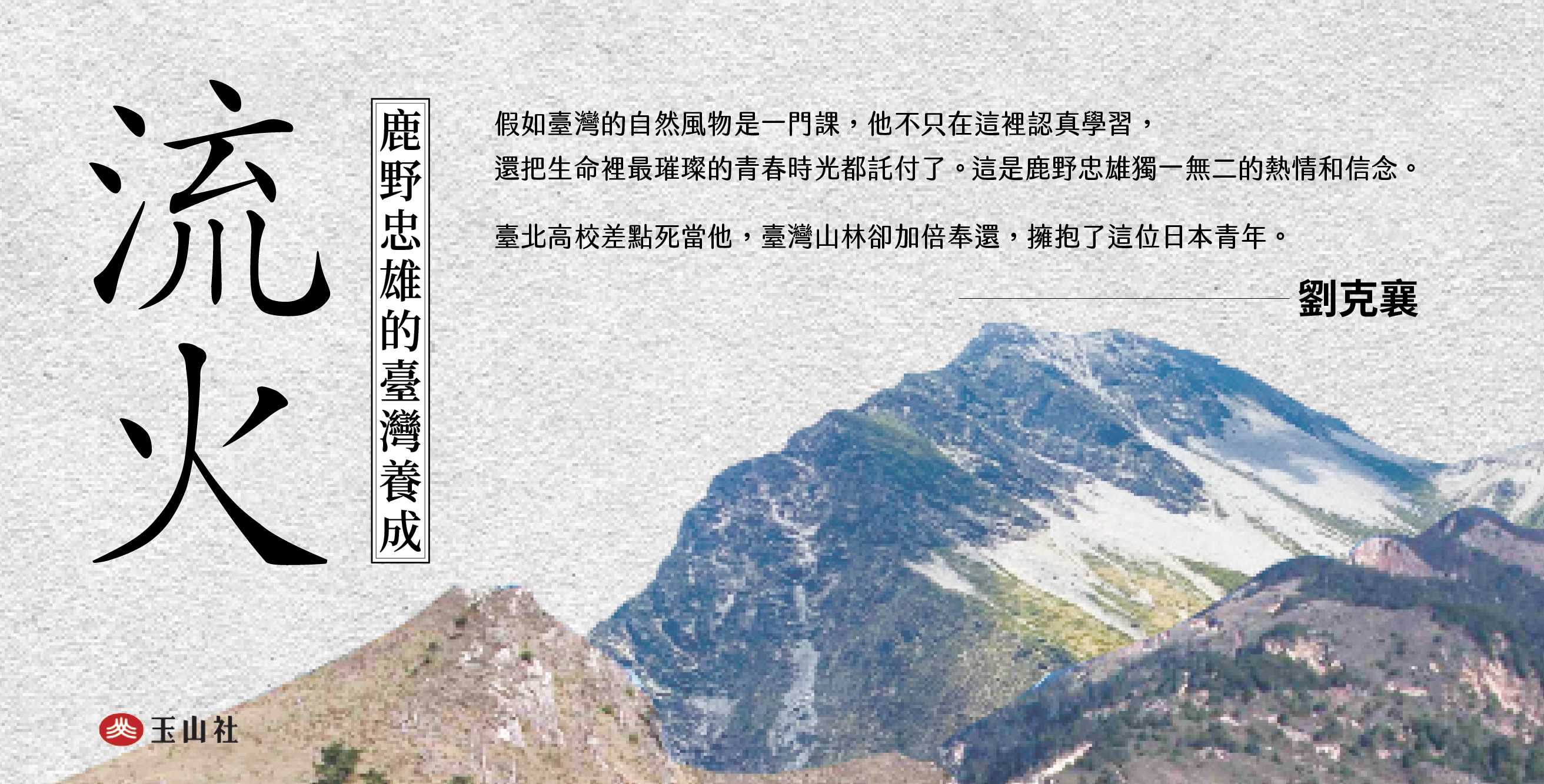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