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樣的時代裡,艱辛的游牧生產生活方式已經不能獨自走下去了。然而傳統自有其強大慣性。無論多麼劇烈的變革,在改變傳統之前,都會先被這傳統過濾一遍。幾十萬人、數千萬牲畜的定居這種大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其過程必然漫長而複雜。其間總會有另外的希望隨之誕生吧。說不定這場毀滅性的變革會慢慢去往另外的出路……但願如此。──李娟
李娟的《最大的寧靜》是一部有關「冬牧」的書,她隨著羊群深入烏倫河南面的荒野深處。對於文學中的大漠,讀者並不陌生,像是三毛筆下的漂泊、勒.克萊喬(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筆下的幻境,它們通常是作為一種相對於自身處境(譬如原來的文明)的意象。但李娟筆下的沙漠卻更為真實,當阿城稱讚李娟的作品「沒有意識到書寫這件事」,我們很容易由此推想,李娟的文字有如相機,直接引用了真實,不待文學觀念的變造。
然就像攝影從不單純,文學也是。當談到無意識的寫作,李娟認為,「也許是我的寫作沒有遵循慣常的套路吧,但其實也自有苦心的經營。從第一本書開始,至今已經出了八本書,從最開始到最近的文字,無論是思考方式還是表達習慣,的確有非常明顯的轉變。這大約與年齡和成長有關,我很滿意這種改變。」換言之,李娟的寫作自始即有明顯的意識,而這種意識,也包含面對讀者,她說,「『如何呈現給讀者』這種意識是從始至終都有的,和現在相比,以前可能會更在意一些,現在的寫作則更率性也更坦白。」
此處觸及了一個問題,如果寫作始終是意識的產物,那所謂不帶意識的寫作,究竟意味著什麼?又為什麼它會一再吸引著我們?一個答案也許是,所謂的寫作意識與真實的傳達,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相反的,不帶意識的寫作,反而最容易帶來刻板的印象。譬如,對生活在城市的讀者來說,李娟筆下的世界帶有一種魅力,彷彿透過她的文字又可以捕捉到某種事物離自然未遠的溫度。事實上,李娟自己也強烈感受過那樣的差異,她說,「18歲進入山野之前,我一直在城市生活,因此我自己應該是此種反差的最大體會者,只是我隱藏了某種態度,敘述得若無其事罷了。也可能正因為這種若無其事,才得以將我所體會到的新鮮與震動最終完整地傳遞給讀者。」


李娟在訪談當中也不隱藏她做為一個漢族與其他人的差異,「大約因為漢族是農耕民族,生存形式較穩定,容易積累較為沉重的生活細節和情感、思想,相對較為壓抑、深沉、內斂;而游牧民族生活動蕩,生活內容簡潔之極,加上生存艱辛,情感表現得也更為單純、直接。此外,農耕民族以改造自然來鋪平生存之路;游牧民族卻緊密依從自然規律而生存,相比之下會有更為自覺的環保意識。諸如此類因生存背景導致的文化差異,不是短短幾句話就能說清的。」這即是李娟的特色,她相信一切自有其積累,不論是人的習性,或一個地區的風俗,事物因此複雜而有趣味,這背後更潛藏了對時間的敬意。她說,「我不知時間是什麼,才會千萬次地以文字去探求。」
談到未來,李娟說,「有一些寫作計劃,想寫的很多,我感到很充實。但我沒有什麼特別想去的地方,我本來就生活在遠方,所以並不嚮往遠方。」問她有沒有興趣出攝影集?「以後吧,如果有合適的機緣會用心策劃一部攝影集。其實我的攝影並不高明,只不過比其他攝影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許多荒野深處一些難得的畫面。我是個寫作者,當然覺得文字的表達會更自由,更充分。」看來,李娟畢竟不滿意一種獵奇式的捕捉,不論拍照或書寫都是如此。
事實上,所謂獵奇就是一種對於相異的事物抱持簡化的看法。造成這種心態的原因,常常是對於「時間」的忽略,再也沒有一個脫離時空的存在,更令人感到好奇而有趣,所以人們喜愛高貴的野蠻人,以及其他關於「異族」的刻板印象;但是李娟筆下的人與物卻是一點一滴形成的,是活生生的在羊糞搭建的小窩之中,思考著昨日與明天。而有時,獵奇的偏見更可能來自於對媒材的誤解,譬如過去人們想像相機是一種忠實紀錄的工具,或相信有一種寫作方式是不假思索;但李娟的寫作並非理所當然的,那種透明的孤單或靜謐的時間感,都是她在內心醞釀已久,然後若無其事地娓娓道來。也無怪乎請她用一句話形容自己與沙漠,她是這樣說的,「沙漠不可形容,自己也同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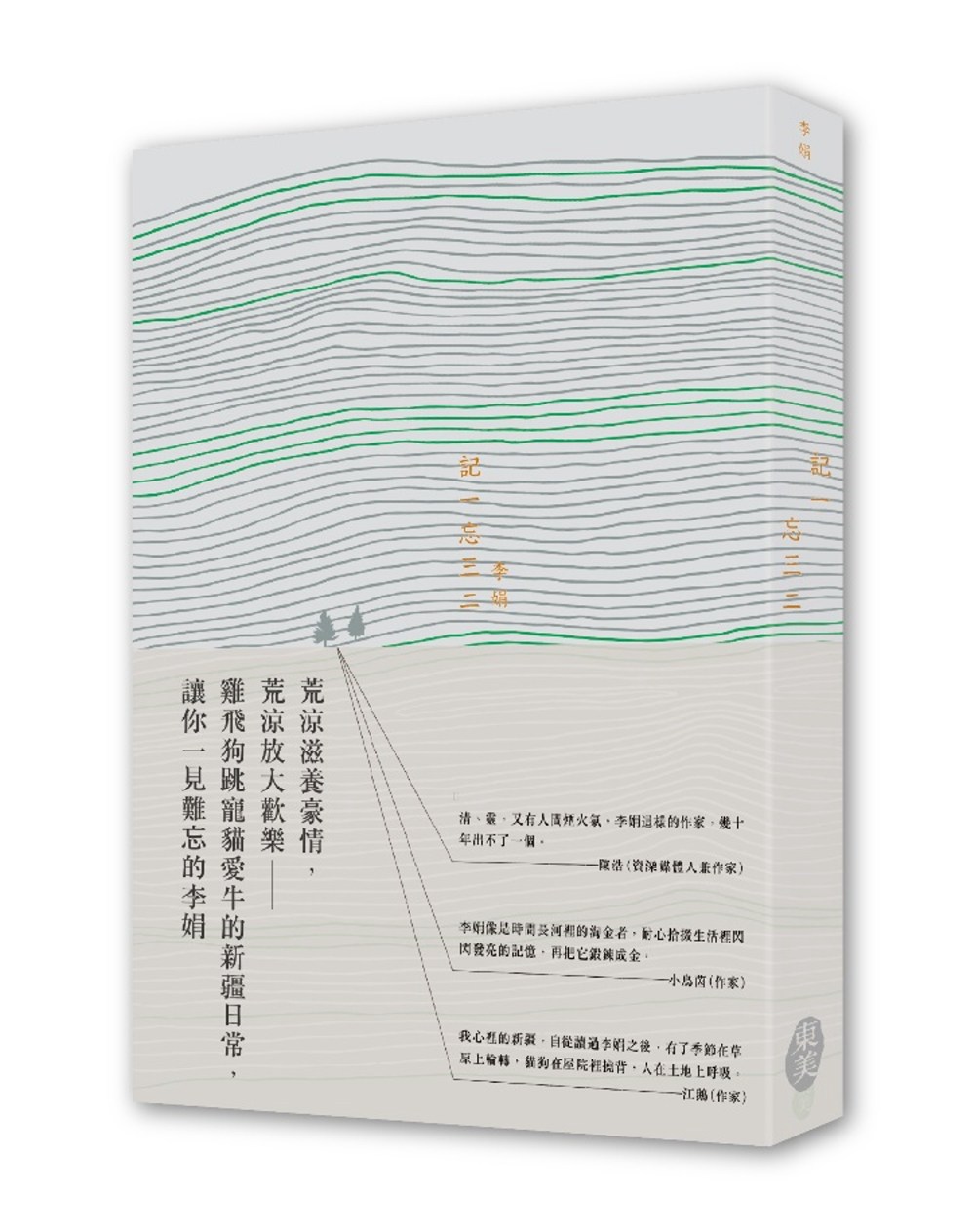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