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有人問「同志文學的定義是甚麼」,也問「同志和酷兒的差別是甚麼」(也就是說,「同志的定義」和「酷兒的定義」有何異同)。這兩個難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有個相通之處:都將「同性戀」視為一個已經被定義完好的詞。
問起「同志vs酷兒」,就是在問這兩者跟「同性戀」的關係,而簡答通常是「同志是同性戀的2.0版本,展現了在體制內爭權的精神」、「酷兒是同性戀2.0的另一種版本,突顯了在體制外挑釁的態度」;問起「同志文學」,就是在問「作品的主題是同志(即同性戀2.0)的才算嗎?角色是同志才算嗎?作者是同志才算嗎?」這兩種問題,都將「同性戀」存而不論,彷彿同性戀是一個穩固基石,不會地震沒有斷層,大家都可以放心在安定的基石上問答、生活、甚至蓋核電廠。
同性戀是不是質地均勻、從裡到外都是正牌零件的跑車?還是四拼八湊的、質地不均勻的拼裝車?這個「均勻與否」的問題,是酷兒理論教母賽菊寇在《衣櫃認識論》提出來的。她認為同性戀是拼裝的、不均勻的。「同性戀」本身就是難以被定義的,絕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國度轉化。既然就連「同性戀」都難以定義,那麼本文第一段的提問(建立在同性戀這個蓮花座上),也就不可能輕易打發。
哈樸林在《如何搞同性戀歷史》中表示,同性戀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同性戀」一詞放在漢代皇帝或羅馬帝國上頭,是很有爭議的),而它的定義是「不均勻的」(incoherent,如前面賽菊寇所說)。這個現代詞語一方面跟「前現代的」種種同性互動的概念排斥:如,古代的雞姦者並不等同於同性戀者,而同性戀者也未必從事雞姦。而另一方面,這個現代詞語卻也「兼容並蓄」,吸收了不同歷史時代種種互向排斥的概念:古時候雞姦卻不男扮女裝的人,和男扮女裝卻不雞姦的人,本來彼此不相干,但現在都被歸入同性戀、「雞兔同籠」。當今的同性戀,是古往今來許多不同概念積澱的混種結果。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如何搞同性戀歷史》藉著檢視男人在歐洲歷史之中的互動(為何只談男不談女、只談歐不談別洲?都是此書的侷限,但大框架仍可參考),歸納出「同性戀」的四種前輩:「女性化」、「雞姦癖」、「兄弟情誼」、「性倒錯」(當然為何只是四種而非五、六種,在別的國度應有別的考量──在台灣,可能並非僅僅四種。我將要加上至少一種:「對同性心動的人」)。這四者的特色都在於「社會性別」(gender,而非生理性別):女性化的男人是陰柔的(不一定跟任何人上床)、雞姦癖的男人(指「攻」而不指「受」)是陽剛的(必須跟同性上床)、兄弟情是陽剛的(不一定跟任何人上床)、性倒錯的男人(不一定跟任何人上床)是陰柔的。
這四者的參與者讓人側目,是因為他們比一般男人陰柔許多,或陽剛太多。
以《紅樓夢》為例:賈寶玉是女性化的人而非性倒錯;以雞姦聞名的人是薛蟠、贾珍而不是寶玉;寶玉跟秦鍾是要好朋友;寶玉欣賞的戲子們是性倒錯者。這四類人/這四類關係在曹雪芹的年代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但對今日讀者來說,他們都類似男同性戀。這四者「積澱、成為」今日的同性戀之後,同性戀的重點卻不再是社會性別而是性取向(sexuality):陰柔或陽剛都不重要,是不是「想要跟同性」發生關係才是重點。以前女性化男人的對立面可能是陽剛的江湖朋友,而現在同性戀的對立面是(未必比同性戀有肌肉的)異性戀。回想古時候,異性戀這個概念還完全不存在呢。
而定義同性戀的巨大變數是,過往的模式仍然倖存,我們現在還活在過去的殘影中。有些同性戀者就是只有要好的朋友,但任何性事都沒做過;有些同性戀者就只是陽剛的雞姦攻方,別的同志生活面向都不參與;有些同性戀者把性取向看得很輕,把社會性別看得很重。我們只能承認:「同性戀」是個「雨傘狀的詞彙」(umbrella term),形形色色的生命體都被歸在同一張大傘之下。
拿《如何搞同性戀歷史》比對台灣文學,可發現兩者有互補之處。前者提供重新整理台灣同志文學的方法,而後者突顯出前者的不足。前者提出同性戀的四種前身,但台灣文學顯然還有第五種:對同性心動的人(這種在歐洲也該常見,但哈樸林沒提到,怪哉)。在台灣文學中,對同性或異性心動的角色很多,他們可能單戀、花痴,但卻沒有做出明顯的動作──他們的性別角色未必太男性化或太女性化、未必有膽跟心儀的對象交朋友更別說跟對方雞姦、未必為了對方而讓自己成為性倒錯者。這些外表看起來毫無異狀但內心戲很多的角色,在古今國內外文學常見。加上了這第五種, 拿《如何搞同性戀歷史》比對1960年代早期的白先勇小說,可發現〈月夢〉和〈青春〉這兩篇同志文學的先驅並沒有呈現我們今日認知的同性戀者:〈月夢〉主要陳述了男人對男性好友的懷念,角色是密友而非同性戀者;〈青春〉展現了老男人耽看美少年的停格畫面,老人屬於我補充的第五種人(對同性心動者),但不屬於《如何搞同性戀歷史》列舉的四種。
同時期姜貴《重陽》寫了做「兔子」的國共兩黨黨員和英國浪人:身為中國古風的兔子,他們是雞姦者,在其他方面跟同性戀的關係不大。白先勇同學歐陽子的〈素珍表姐〉寫出是女性版本的同性友誼 、〈最後一堂課〉聚焦在白先勇〈青春〉一般的老男對少男執迷(屬於我補充的第五種)、〈近黃昏時〉描繪了男男友誼(他們之間有無性愛,在文本中看不出來)。
與其說1960年代的同志文學已經展示了我們當今認知的同性戀,還不如說當年文本各自再現了「同性戀的眾前身」。這些眾前身需要時間積澱,才會顯影逼近後來的同性戀。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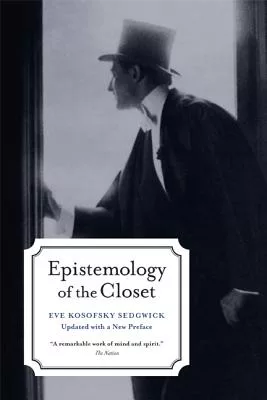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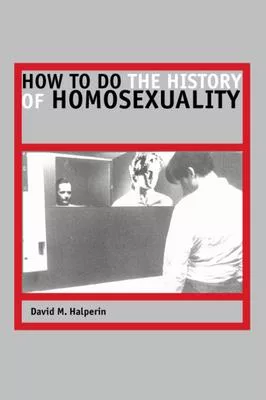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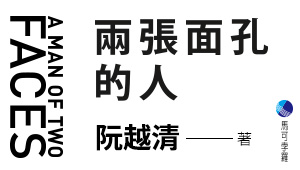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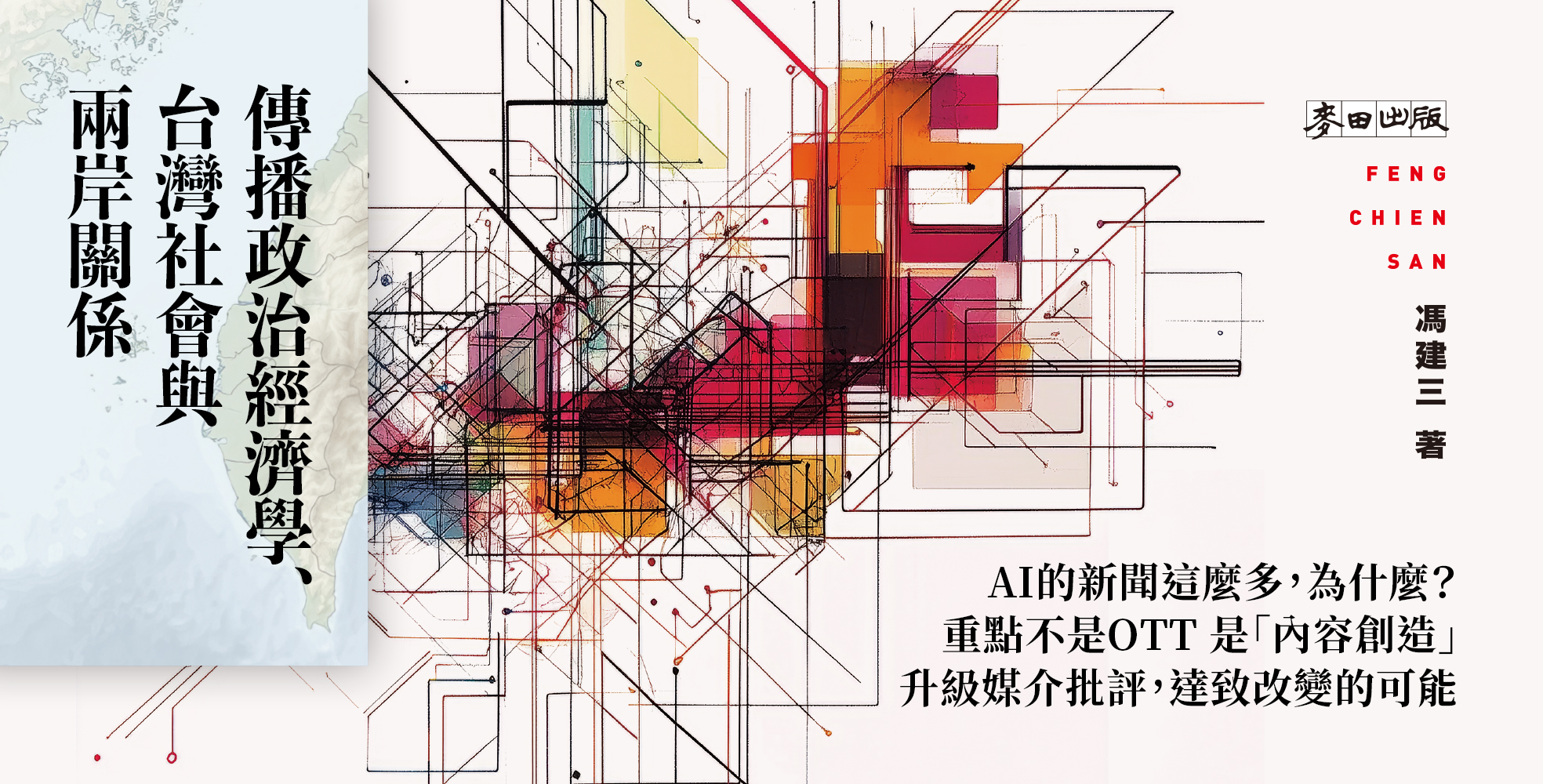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