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的百姓去」出自《聖經.出埃及記》 5:1,摩西向法老傳遞上帝的旨意,令法老讓祂的百姓離開埃及;如同小說主角海瀾讀到的老黑奴的臨終之言所示:「凡人使我們為奴,但上帝意欲我們自由。」〈出埃及記〉是《水舞者》(The Water Dancer)內容裡一個扣結主題的核心典故,整部小說刻劃黑奴在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度中如何透過摩西一般的人物逃往自由之地,但這「出埃及」的路程充滿了超自然的色彩,也充滿了文學喻意與心理意涵,使人讀之深受吸引,無法釋手。
▌書寫生命的自傳式奴隸敘事
《水舞者》這部小說是科茨(Ta-Nehisi Coates)長年從事新聞相關非虛構文類寫作之後的初試啼聲之作,雖然他首次嘗試小說創作,但內容令人驚豔。美國非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對科茨讚賞有加,將他譽為二十世紀初知名非裔作家包德溫(James Baldwin)的繼任者。身為非裔作家,科茨免不了在小說中延續他在其他非虛構作品中對種族議題的關注與省思,然而在小說中他卻出人意外地展現豐富的想像力與創意,以及極具文學性的手法,再現奴役制度的殘酷與歷史創傷,並且在寫作手法的運用及情節安排上巧妙地呼應美國文學中的奴隸敘事(slave narratives)傳統。
在小說形式上,科茨選用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甚至讓主角海瀾偶爾對著讀者直接說話,例如:「而今思之,我自己寫的書,亦即你手上這本,就是從那些時刻——從那間圖書室誕生的」;此自傳體形式常見於奴隸敘事之中,由獲取自由的黑奴自述其為奴的經歷。如同許多奴隸敘事的內容陳述黑奴親身經歷的苦難與對白人社會的觀察,小說的敘述者深刻描述了黑奴如同被豢養的牲畜,任意被拍賣、出租、凌虐,也呈現他對南方階級社會的敏銳觀察和批判。這些觀察描述,因為海瀾身為莊園白人主人與黑奴所生的混血私生子而顯得更加諷刺:白人血統的部分使他對於身為莊園繼承者的身分有潛藏的欲望與揣想,但黑人的血統使他永遠只能當他那位懦弱無能的同父異母兄長的侍從,被白人父親期待如同黑影子般以他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來輔佐白人哥哥。作者透過海瀾與白人兄長的對照諷刺種族主義所造成的權力地位的不對等,安排有黑人血統的海瀾天生聰明能幹,而讓其兄長徒有白人血統所賦予他的權力地位卻毫無能力經營管理,以此逆轉白人社會的種族偏見。
此外,科茨對主角的刻畫隱射十九世紀知名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也就是小說第一部卷首題辭的作者;兩者同為黑白混血兒,道格拉斯脫離黑奴身分後,寫了三本自傳,第一本《美國黑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敘事》(Narrative of Frederick Douglas: An American Slave)輔出版即大為暢銷,他脫離黑奴身分後所展現的演說口才與文筆推翻白人對黑人的偏見;小說中,海瀾這位同樣有位白人父親的混血黑奴展現超凡的記憶力,因為過目不忘而有了學習的機會,得以遍覽群書,甚至得以運用其特長解救其他黑奴。小說第一部的題辭「我的職責是訴說奴隸的故事。奴隸主的故事從不乏人講述」乃出自道格拉斯第三本自傳,科茨以此句作為小說卷首的題辭無疑是暗指此書是一部奴隸敘事,也頗有向道格拉斯致敬的意味;另一方面,透過引文,科茨也指出黑奴被剝奪發聲權,相對於白人得以建構自己版本的官方或主流歷史,黑奴的人生故事卻無人聞問。黑奴敘事因此不僅是個人自傳,更是另類的非裔歷史書寫形式。
 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圖/wiki)
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圖/wiki)
▌小說創作即是歷史書寫
這部虛構的奴隸敘事以非裔族群的觀點建構十九世紀南北戰爭之前的黑人歷史,但作者也藉此揭露社會權力結構上根基於種族歧視的不公義以及上層白人階層的偽善;海瀾不只見證到維吉尼亞州的莊園主隨著菸草種植業的興衰如何剝削下等白人與黑奴,還有白人如何透過地道與地下營窟來隱藏蓄奴的黑暗面以活在高尚亮麗的假象中,他也看穿那些同樣在社會制度下無法自我實現的下等白人只能將自己的憤怒與羞恥感發洩在比他們更沒盼望的黑奴身上。然而,海瀾卻領悟:這些握有權力的上等階級卻是最軟弱無能的一群人,因為離了他們所鄙視卻依賴的黑奴,他們就無法生活,連燒開水的能力都沒有。當海瀾逃至北方,他見證到南北兩個世界的不同——人權思想在北方興起如雨後春筍,自由黑人擁有自主權,得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相對的,南方的蓄奴社會卻因莊園主貪婪,過度種植菸草而引來衰敗,開始拍賣黑奴換取資金,加深黑奴逃亡的動機。
這些歷史刻畫中最特別的就是科茨將南北戰爭前南方黑奴經由「地下鐵道」(underground railroad)逃往自由北方的歷史事件納入情節,甚至可說是情節的主要骨幹。所謂的地下鐵道是由同情黑奴境遇而願意收容並協助逃往北方的家戶所形成的地下網絡,這些家戶就如同車站一樣,讓黑奴停留,再經過指引路線後逃往下一站,如此直到進入北方安全處;這些協助者,除了北方廢奴人士與桂格教會之外,很多是逃亡成功的黑人。在小說末尾,作者特別提及威廉.斯蒂爾(William Still)於1872年所著的《地下鐵道紀實》(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Records),書中收錄許多逃亡黑奴的文件資料與經歷,科茨在昆西.米爾斯(Quincy Mills)新編的版本中還寫了一篇引言,足見他對這段歷史的熟悉與看重。
小說中的地下鐵道這個逃亡網絡與「出埃及典故」關係密切;談到地下鐵道的歷史背景就必然要提到一位重要且知名的引路者,也是位非裔傳奇人物——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人稱「摩西」,其典故自然是出自《聖經.出埃及記》那位奉神的旨意將以色列民從埃及法老王的高壓奴役之下拯救出來,並且以杖分開紅海以脫離埃及追兵的摩西,這個稱號說明塔布曼在逃亡黑奴心中是位如同摩西那樣的奴隸解放者;在小說裡,科茨特意描述她如同摩西一樣手拿著杖,她稱之為:「我忠實可靠的手杖……我走到哪都帶著它。」她被喻為摩西,而馬里蘭與所有蓄奴的南方社會則是受法老管轄的埃及地!
 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圖/wiki)
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圖/wiki)
然而,科茨並非以紀實或是歷史小說的寫作方式再現南北戰爭前的黑奴境遇以及地下鐵道的運作;這部小說的文學性與獨特性在於科茨以魔幻寫實手法賦予地下鐵道這段歷史豐富的想像,並且結合了非裔傳統文化,例如歌詠中的「呼應」(call and response)形式;此音樂形式源於黑奴在棉花田裡工作時的唱和,後存於黑人靈歌與爵士樂中,其特色是在一呼一應之中帶著自發性與自由度,形成與他人的情感與思想的交流(亦即社群關係的建立)。此種歌詠的形式如同對話,也具有故事性,因為往往內容涉及歌者的人生經歷或是情感,甚至可以視為口傳文學的一種形式。黑奴們歌詠骨肉分離的傷心、際遇的悲慘與對上帝的呼求與信靠,透過歌詠中的呼應形成奠基在集體經驗所產生的共感,其中所陳述的經歷也匯聚成為集體記憶,甚至帶來集體的心靈安慰與療癒效果。
科茨的創意在於他以魔幻寫實手法,將地下鐵道、記憶與黑奴歌詠中的呼應串連起來,賦予地下鐵道的營救行動與記憶積極的救贖意義。地下鐵道的傳奇引路者哈莉特(摩西)在小說中被描述為具有超能力的傳送者,能夠將人迅速傳送到北方;海瀾的祖母珊蒂.貝斯據說也具有這個超能力,曾經傳送了48個人至非洲,而海瀾也遺傳了這個超能力。這個傳送能力是靠著回憶與水兩個元素才能發揮,當回憶湧現時,這些記憶中的畫面彷彿形成一個異次元通道,引導回憶的人走在水上,穿越進另一個空間。海瀾首次意識到自己的傳送能力是他墮入古斯河時,當時他看見回憶中他的母親跳著水舞的畫面,雖然她的面貌模糊不清。這些跟水有關的傳送元素源自於一個奴隸船的傳說:一艘滿載奴隸駛往北方的船上,一群奴隸相信能夠踏浪返回故鄉而行走在海面,返回非洲。易言之,這個超自然的傳導能力扣連非裔族群的原鄉情結——水連結他們與非洲原鄉,而原鄉與母親的形象密不可分。「水舞者」這個標題的意義自然不單指海瀾的母親而言,更是暗指與此傳說相關的原鄉情結與集體對自由的嚮往。
哈特莉在傳送的過程中吟唱:「我們以人生為鐵路,故事為軌道,我是火車司機,將帶領這次傳送。」這句話點出小說中地下鐵道與傳送的重要喻意;所謂的傳送乃是透過回憶的能力發揮超自然的輸送功效,而回憶的傳遞管道則是來自口述回憶所形成的故事。哈特莉帶領幾個手足與海瀾進入傳送時,他們一行人踏入水中,開始進行詠唱與呼應;哈特莉主領,背後是她的合唱隊,回應她所歌詠的回憶,也就是她的人生故事。童妮.摩里森在她多部小說中特意呈現口語化與合唱的效果,她曾在〈根源:先祖基石〉(Rootedness: 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這篇文章中特別指出她小說中合唱隊形成具有回應功能的社群,而此種口語性與眾聲合唱的效果即是黑人寫作的特色。由於黑奴會被白人主人任意販賣導致骨肉分離,在棉花田工作時即興的歌詠與唱和,不只抒發內心的苦楚、講述自己與他人的故事,也成為具有社群型態的交流。此外,由於黑奴不識字,不具有書寫的能力,無法寫下自己的歷史,這些傳承的歌詠或口傳的故事成了集體記憶的載體;當沒有人能為自己的過去發聲時,集體記憶如何傳承,歷史如何被書寫保存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族群議題。在黑奴能夠以文字為表達工具之後,奴隸敘事便是為自己發聲的平臺以及在主流白人歷史論述之外另闢蹊徑的管道,所有接續奴隸敘事之後的非裔作品均可視為以小說文類建構而成的非裔歷史,摩里森更是表明她的小說即是一種歷史書寫,而科茨明顯也在延續這樣的歷史建構工程。
▌暗藏的集體記憶軌道
非裔歷史的書寫與重建必然牽涉到對於奴隸歷史的集體記憶,非裔小說中常見的一個主題即是創傷記憶;弔詭的是,創傷的存在形式乃是被潛抑(represssed)於無意識、難以言表的記憶黑洞,在語言的表述上只能以迂迴的方式去接近,或是以片段的意念、閃現的記憶畫面呈現。在小說中,海瀾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能記住眼睛看過的任何細節;然而,諷刺的是,一個什麼都能記住的人卻記不起母親的臉,他所能看到的記憶畫面只有母親頂著水罐跳水舞卻容貌模糊的身影,這顯示母親的臉正是他記憶中的黑洞,亦即他創傷的所在。直到找到與母親相關的失落物件(貝殼項鍊),他才憶起母親的臉,同時他的傳導能力也能發揮極大功效。顯然,作者藉此意指回憶創傷經歷所帶出的修復與醫治具有拯救的力量,而與母親的分離正是許多黑奴共有的創傷。
創傷記憶、故事與母親(水),這些是海瀾傳導能力的構成元素,也是非裔創傷敘事中反覆出現的母題;海瀾的超能力承襲自母系血統,而水不只連結於母親頭上所頂的水,也連結於子宮內的羊水以及踏水返回非洲的傳說,也就是原鄉情結。小說標題「水舞者」,暗指那些踏水而行進入回憶的傳導者,因此所謂的「傳導」,其實是集體的記憶之旅;不同於歷史上的地下鐵道,小說中的地下鐵道變成是暗藏意識之下的記憶軌道。科茨這部小說不只以文學手法建構內戰發生前的一段非裔版本的美國歷史,也可以視為一則寓言故事,說明歷史記憶乃是帶領非裔族群脫離奴役,進入自由的驅動力。以創傷理論的角度視之,當創傷得以被憶起且口述之時,亦即倖存者能夠招領失落記憶並對過去進行認知整合之日;易言之,水面上進行的集體回憶與吟唱象徵集體的心靈醫治,使得非裔族群得以脫離創傷經驗的禁錮,進入心靈的自由。
蔡佳瑾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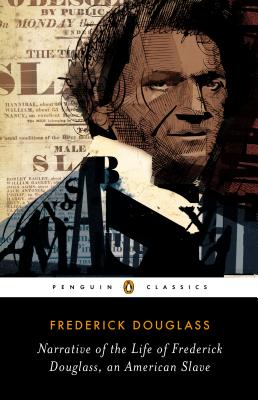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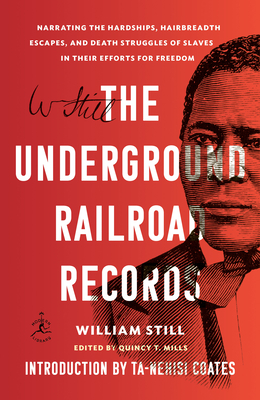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