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尊嚴》為研究社會結構壓迫與受害者主體性的民族誌作品。(照片提供 / 楊啟巽工作室)
《尋找尊嚴》講的是紐約東哈林區的故事,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作者菲利普.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 1956- )於此區斷斷續續住了幾年,和幾名波多黎各裔的快克(或海洛因)藥頭及其親友建立了交情。關於人類學的資料整理及分析,我無法說得比作者更詳盡,但身為有一點寫作背景的譯者,我想從窗戶聊起。
▌一扇扇失去功能的窗戶
在翻譯這部作品時,我無法克制地注意到,東哈林區的房屋窗戶及車窗幾乎都是被封閉住的。有些用厚重的窗簾遮蔽、有些用油氈布貼住、有些裝上外板或金屬柵欄,有些則是封上黑色卡紙,為的是掩藏屋內的非法交易、防止打劫、減少學生或老人看到窗外的各種暴力場面或槍戰,又或者是男人想控制女人不往外「亂跑」時,先沒收她往窗外觀看的自由。
故事的主角之一名叫普里莫,他跟母親及姊姊住在暱稱為「埃巴里歐」(西班牙文的El barrio,直譯的話是「鄰里」之意)的東哈林區,而他的父親就跟1930、40年代來此追求功成名就的許多波多黎各工人一樣,在失敗之後酗酒、濫用藥物又毆打老婆,最後終於被趕出家門。這樣的男人有些留在當地茫然無措,想辦法找別的女人寄生或淪為流浪漢,有些則跟普里莫的父親一樣回到波多黎各,最後一身病痛的死去。
他最後死在一間破爛的小棚屋,據說小棚屋周遭只有兩個街區的生活範圍。關於這段描述,其中完全沒提到窗戶。倒不是那裡沒有窗戶,而是那裡的窗戶沒有真正隔絕什麼,也沒有為住戶帶來什麼。
東哈林區的窗戶作為一種隱喻,反映的則是普里莫及他父親這兩代人在紐約的尷尬處境。他們從農村生活被連根拔起,來到需要廉價生產業工人的大城市,卻又在大環境的經濟體系升級為服務業之後,成為完全無法融入中產階級生活的異鄉人,就算花大錢買了好衣服去上班,以為自己看起來體面,卻發現大家覺得自己穿得「像個流氓」。這些人大多住在大型公宅社區,層層疊疊的狹仄居住空間將他們堆在一起,卻又讓他們更為隔絕及孤寂。在這裡,窗戶無法成為他們與社會連結的管道,反而可能暴露出他們的弱點,畢竟他們不是被搶就是得剝削他人才有辦法活下去。
普里莫第一次打破窗戶搶劫公寓是11歲,他的搶劫之路始終是由表哥及鄰居大哥哥帶領。16歲有次打劫電器行時運氣不好,手臂被窗玻璃劃破,翻開了一整塊皮,肌腱瞬間鎖死,手掌無法動彈。
若說封閉窗戶是為了逃避無法適應環境,打破就是為了重拾自主權。普里莫是移民第二代,他進入學校之後就逐漸發現,幾乎只講西班牙語的母親是被主流社會嘲笑的族群,而他若想擺脫波多黎各裔的邊緣人生,就只能試圖融入主流制度。他於是學會用學校教的英語捉弄、羞辱自己的母親,藉此與過去斷裂,然而當他發現即便如此也難以受到整個體系接納之後,靠著非法藥物或偷竊等地下經濟的相關行動,他打破了這個拒絕他的世界,嘗試重拾尊嚴。
但若要更進一步談窗戶的隱喻,我們得先暫時把普里莫放到一邊,來談談1980年代的「破窗理論」。這個理論假定一棟大樓的窗戶被打破,卻一直沒有修復,之後那棟大樓其他住屋遭破門搶劫或縱火的各種犯罪率也會提升。於是到了1990年代,紐約市長推出了「破窗法案」,強調「輕罪零容忍」的概念,意思是這些犯罪率太高的區域,警方必須由小見大,從糾舉「破壞生活品質罪」(quality-of-life crimes)做起,也就是要「大動作逮捕乞丐、洗車窗賺錢的人、地鐵上的逃票者,還有在街上遊蕩、穿著嘻哈風的黑人或拉丁裔年輕人」。這種生活糾察隊的行為,若就隱喻來說就是:窗戶哪裡裂了一點小縫,我就立刻補起來,想像能藉此恢復窗明几淨的居住環境。然而整棟屋子內外的黑暗,實在不是幾扇窗戶可以解決的。
更諷刺的是,即便政府針對穩定租金及預防弱勢家庭遭驅逐設置了嚴格法律,許多房東仍會鑽法律漏洞,以符合「基礎設備優化」的翻修窗戶為名目來合法提高租金,藉此逼走他們不喜歡的房客。而這種翻修窗戶的工作是誰在進行呢?是這些無法融入主流就業市場的當地人在打黑工。這些工人比較便宜,發包商也能抽到更多油水。於是當地窮人賺錢的方法,最後會讓自己更住不起當地的房子,而許多破敗老舊的房子則閃著一扇扇過度明亮的眼睛。
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窗展示的是內在及外在世界的出入口,然而在這裡,窗是各種透光的死胡同。即便是一次次追求自我的打破,最終傷到的仍是自己。

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窗展示的是內在及外在世界的出入口,然而在這裡,窗是各種透光的死胡同。(圖 / pixta圖庫)
▌槍與檔案
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明確地意識到,槍是武器,檔案也是武器。
《尋找尊嚴》作者是男性,因此跟男性建立了較為深刻的友情。來自波多黎各農村的這些人物稱自己為「吉巴羅」(jíbaro,西班牙文的鄉巴佬),基於「吉巴羅」文化當中男女有別的習慣,他能詳細訪問到的女性也有限。然而糖糖是其中一個血肉飽滿的角色。她幾乎是忠實搬演了這個文化中所有女性的命運,但又想辦法靠著「成為一個男人」獲得尊重。為了壯大自己,她不惜重演父權腳本中認為女人才會「發神經」(ataque de nervios)的行為,向背叛自己的老公肚子開了一槍,成功利用男性的厭女心態獲得了男性的尊重。果然不論在什麼文化中,女性利用父權體制反抗父權體制總是一條難以避開的道路。
在吉巴羅的脈絡中,為愛私奔是合理的文化機制,能讓反抗父親宰制的十來歲少女表達她們追求個體權利的需求。只要逃家女孩重新受到愛人的掌控,並在懷孕之後就跟對方共同建立家庭,她和被她拋下的父母就不用承擔文化上的汙名。
正如普里莫是在11歲時第一次打破玻璃,糖糖實踐這份腳本的年紀也差不多,13歲。如果男人的身體是尋求尊嚴的最後依歸,女人的身體則可以是續命的籌碼。她們靠身體換到男人和住處,靠生孩子感受到幸福並申請各項福利補助,有些還用身體換取藥物。當男人為了複製過往的吉巴羅榮光,不停透過強暴或愛讓女人懷孕卻又丟下她們的同時,她們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跟生命作戰,而其中的糖糖尤其兇悍。
她開槍,她也花很多時間研究各種福利措施,利用各種漏洞盡可能申請到最多的錢。她有時嘶吼著跟官僚體制對戰,有時想辦法軟性地博得法律系統的同情。她善用女性的受虐身分獲取好處,不因此感到一絲愧疚。男人尊敬她,但又害怕她的僭越。他們說她變得比男人還大男人,簡直變成一個「科學怪人」。(但他們若是進一步想,或許就會想起《科學怪人》的作者是女性。)
但儘管是科學怪人,跟這些男人一個關鍵的不同是,她要拿自己獲得的權力去劃清「私奔」跟「強暴」的界線。畢竟厭女的一個面向就是將男性的「性」視為權力和享樂的象徵,女性的「性」本質上就代表了屈從及痛苦。而將「強暴」指認出來的關鍵,就是要肯認女性的性有痛苦和美好之分,而且必須要由她自己決定。
糖糖的女兒婕琦也經歷了男人口中的「私奔」,糖糖的發生在13歲,婕琦是12歲。普里莫說:「她感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我看來。她總是往窗外看,她根本是在希望街區的男人來找她。」
糖糖不接受這個說法。在女兒出事之後,糖糖花了極大的心神與精力要身邊的男性承認,就算自己的女兒逃家、事後沒有表現出極大痛苦,也沒依循傳統腳本跟騙她發生性關係的男人「私奔」,仍不代表有誰可以判定「她想要被幹」。當然糖糖是做過許多大事的女人了,除了開槍之外,為了養家活口的她還曾因賣藥被抓進監獄,可是看到她面對身邊這個共同扶持又共同憤恨的集團,要求他們去扭轉這麼一個性別觀念中根深蒂固的死結,我心中搖起了地震。這樣的她不只是試圖在官僚檔案構築的主流世界遊走,也不只是殘暴地調度自己的身體,而是鑽入自我及周遭之人內心的創傷,以無力者之姿打出一場微小卻精準的社會運動。那不是一場生命的武裝行動,而是一次次靈魂的針灸。
▌蔓延牆面的塗鴉
此書也有提到奧斯卡.路易士(Oscar Lewis)著名的貧窮文化理論,這個理論在1960年代開始獲得關注,路易士針對墨西哥貧民窟書寫的作品也曾成為全美暢銷書。然而作者強調,「路易士的研究手法奠基於一1950年代主導人類學的佛洛伊德『文化及人格』典範,卻沒有注意到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結構是如何限制了個體的生命發展。」
因此,《尋找尊嚴》是一本結構之書,是探討一個人在社會上試圖活成一個有「尊嚴」的人之時,整個環境如何可能以各種形式阻礙他達成目標。當然,「尊嚴」在不同文化中擁有不同定義。吉巴羅生活的環境讓他們社群關係緊密、為了農作人力生養大量孩子,而且家父長角色掌握絕對的權威。當這些關係在強調個人主義及小核心家庭的社會中分崩離析之際,掌握不了訣竅的他們就彷彿進入了異世界。
因為始終不懂如何應付官僚體系及主流社會,普里莫和他的親友選擇一次次回到熟悉的世界賺黑錢。他們想掙脫一種無力感,卻只是陷入另一種無法肯定自我價值的迴圈。普里莫的朋友凱薩是這樣說的:
我在遊戲間賺的錢是為了讓自己瘋,是為了滿足藥癮,也是為了毀滅我自己。這是我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沒人能管我要怎麼做。
(突然開始激情演說)所以我可以從體內傷害自己,我可以每天早上醒來時肚子痛得要死又嘔吐又反胃。我沒辦法吃,我沒辦法呼吸,我一直拉肚子。我的糞水拉得到處都是。我一團糟。我的一隻眼睛是粉紅色,一隻是白色,我的頭髮臭得要命,我很髒,我不洗澡。我一團糟,我臭得要死,我恨我的女人,我在早上時恨所有人。
其實我們都可以想像的。一旦無法肯定自我價值的環境無從改變,人們只能用扭曲的方式尋求愛及掌控感,而這些情緒最後甚至會逐漸跟恨疊合在一起。畢竟有些時候,恨感覺讓人更有力量。糖糖的兒子叫朱尼爾。朱尼爾身邊的所有親友都在賣藥產業中,為了幫忙分擔家計及幫助親友,他逐漸開始幫忙跑腿和販售,但他也曾經是有夢想的:他想當警察。不過面對一個孩子懷抱的夢想,普里莫是這樣說的,「不可能!你會跟我和凱薩一樣變成白癡。一個糟糕、一無是處、作奸犯科又浪費生命的人(desperdicia'o envicia'o)。」因為你是我們的其中一員,我們不要失去你。
所謂「尊嚴」的定義若已往陰暗之處傾斜,愛與親密也會跟著將人吞噬進去,變成某種共同憤恨的集團。普里莫曾想跟母親劃清界線,結果卻還是始終仰賴著母親的愛及金錢支援;朱尼爾曾想過上與身邊其他人不同的生活,但後來依舊跟著大家結夥走入這個地下世界。
當然,還是有些方法可以讓他們保護自己的尊嚴。作者在書寫時儘量完整呈現他們受訪時使用的西班牙語彙、說話風格及節奏,也是為了尊重他們維護自我尊嚴的方式。就算他們的口音或說話習慣常讓他們受外人排擠,卻也正好是反映他們自我認同且不可退讓的媒介。不過為了編輯上的需要,作者在儘量呈現原文風格下做了不少取捨,而我翻譯時也儘量在不對作者版本進行更動下做了小幅度調整,比如為了強調他們語氣中的強烈節奏感及誇張表演性,我會將句子重新分段或縮減,或是多加上一些語助詞或贅字。不過無論怎麼修改,最高原則仍是確保讀者閱讀時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作者曾在註解表示,他們的語言中帶有某種詩意,我在翻譯時深有所感,然而更進一步說,我感覺到這種詩意帶有一種相對性。我的意思是,若從這些主角的立場來看,主流世界的英語或許也帶有一種朦朧「詩意」。普里莫和糖糖他們說的話混雜了英語、紐約拉丁裔英語(New York Latino English)、西班牙語,還有這些語言各自或融合後出現的俗稱及簡稱。這一切反映出他們的出身背景和生活形態,因此對於學習主流英語的譯者來說,我可以跟作者一樣感受到那種詩意。也正因為如此,儘量保留西班牙文並做出大量解釋及標記,並忠實或強化提示出他們的肢體語言,藉此確保讀者感受到這種閱讀上的輕微隔閡與困難,也就帶有維護他們尊嚴及主體性的重要性。然而這項工作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備,我只能在有限範圍內儘量嘗試,希望讓讀者在可接受範圍內偶爾讀得不是百分之百順暢,卻又能因此更加認識彼此之間的不同。
然而,除去語言的部分,當存活的意義無法在結構中開枝散葉,這些人開始縱情地使用自己的肉體尋求意義。物質濫用跟暴力行動如是,生小孩如是,這種不停向身體內部累積意義的作為,最終會堆積成死亡。於是我們看見了無止盡紀念死者的塗鴉名人堂,在這區的牆面上艷麗地著展示著肉身最後的爆炸。
塗鴉做為「破窗法案」想要消滅的「破壞生活品質罪」的目標之一,彷彿更是象徵性地濃縮了他們的反抗之心。這些塗鴉可以用來紀念死去的朋友,也可以用來劃定地盤。普里莫小時候感覺被老師及學校放棄時,他也學會了自我放棄,上課時不停在桌面塗鴉亂畫。他所就讀的中學牆面上也布滿塗鴉,幾乎找不到一絲蒼白的空隙。
一條郊區通勤火車的路線就從此處經過,穿越了埃巴里歐中心的公園大道,彷彿要彰顯出在美國都會區存在這樣的種族隔絕措施有多諷刺,你還能在遊樂場的水泥牆邊看見火車經過時投下的影子。每個上課日,透過這條特定的通勤路線,數千位紐約薪資最高的財金、房地產及保險部門主管呼嘯而過,回到他們位於康乃狄克及紐約「上州」的家。這條鐵路服務了美國最富有的幾個人口普查區。如果這些通勤者望向窗外,可能會瞥見覆蓋校園水泥牆上的顏料從噴漆罐噴出後在空中飛旋的瞬間。
不過儘管紐約的藝廊也會展示各種嘻哈或塗鴉風格的藝術品,卻不歡迎東哈林區的孩子去看,就怕他們亂尿尿。若真有出身此地的藝術家,就算有人引介,卻也仍像是那些飛旋的顏料,凝結成張揚的靜定樣貌,終究無法穿越那道種族及階級隔離的高牆。
▌黑色卡紙上的天空
為了不讓孩子身邊圍繞著太多暴力和用藥場景,東哈林區有老師在教室窗戶貼上黑色卡紙,然後讓孩子用白色粉筆在卡紙畫上天空。
《尋找尊嚴》出版近20年了,現在回頭去看,一切彷彿都是很遙遠的事。可是作者1990年住在東哈林區時,曾在住處窗外看見一間公寓熊熊燃燒起來,他知道這類公寓很可能在棄置之後被無家者占領,之後又因為不當使用而失火,而那個失火場面就跟他在此區文獻中讀到的場面一樣:「我們開始意識到火中錯落著一扇扇彼此隔離的孤絕窗口——其中一扇窗裡有盒裝花或是窗簾布,另一扇窗裡有張孩子的臉。」
這類世代重複的故事總在不停發生。早從1800年代末期開始,東哈林區就陸續來了德國人、愛爾蘭天主教徒、中東歐的猶太人、非裔美國人、北歐人定居,而紐約「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畫在1880及1890年代開啟了第一波移民雇工潮,東哈林區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貧窮且文化最多元的區域之一」。為了確保有廉價好用的勞工,紐約在愛爾蘭人罷工之後又引入義大利勞工,等義大利勞工罷工之後又引入了波多黎各勞工,歷史不停自我重複,不同種族都得面對類似的階級及歧視問題,偶爾又為了爭奪主流以外的資源彼此傾軋。
在波多黎各勞工之後,更「好用」的是墨西哥勞工,書中的普里莫也有跟他們起過衝突。然而隨著基礎建設的工程需求減少,本書作者最後提到多方勢力都想將本區「仕紳化」,直到今天,這項試圖將此地重塑為紐約新興居住熱點的計畫仍持續在進行。另外再加上更多亞洲人移居此區,東哈林區的面貌逐漸有了改變,不過為數最多的仍是波多黎各裔居民。跟當時相比,現在此區的貧窮率確實有所下降,跟紐約整體相比的差距也大幅度縮小。
 東哈林區,萊辛頓大道與116街的街道。(圖/wiki))
東哈林區,萊辛頓大道與116街的街道。(圖/wiki))
然而問題消失了嗎?那個時代的東哈林區做為一個縮影,會不會也是其他類似地區的預演?
2019年,東哈林區從公園大道到歡樂大道之間的111~120街街區,被國家歷史地點註冊局列為「東哈林歷史區」。這塊地方就是普里莫、朱尼爾、糖糖、婕琦,以及他們所有親友當時生活的地區。「歷史區」聽起來是很遙遠的事了,但若普里莫還活著,現在也才55歲,他的大兒子也就跟我差不多大而已。若是再認真探究,作者住進東哈林區進行研究工作的1989年,也正是台灣因為經濟起飛面臨嚴重缺工困境,政府為了推動重大建設通過相關法律,就此拉開移工來台序幕的年份。歷史的河道總是這般交錯又岔開,沖刷出各種不同面貌的流離。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就算窗戶在某些情境下令人害怕,也沒有人不樂意擁抱天空帶來的無限想像。閱讀《尋找尊嚴》這類作品,或許也是讓我們看見人在無盡的結構限制之下,依然如何試圖去撞見天空,即便只是粉筆畫的也一樣。又或者正如本書後記結尾,作者寫了一個在東哈林區常常被家長毆打,求救聲不停穿牆而來的小女孩。作者沒見過她的樣子,也不清楚她的名字,沒人知道她會不會成為糖糖或其他模樣,但至少我們能做的,就是不要迴避去聽到這些吶喊。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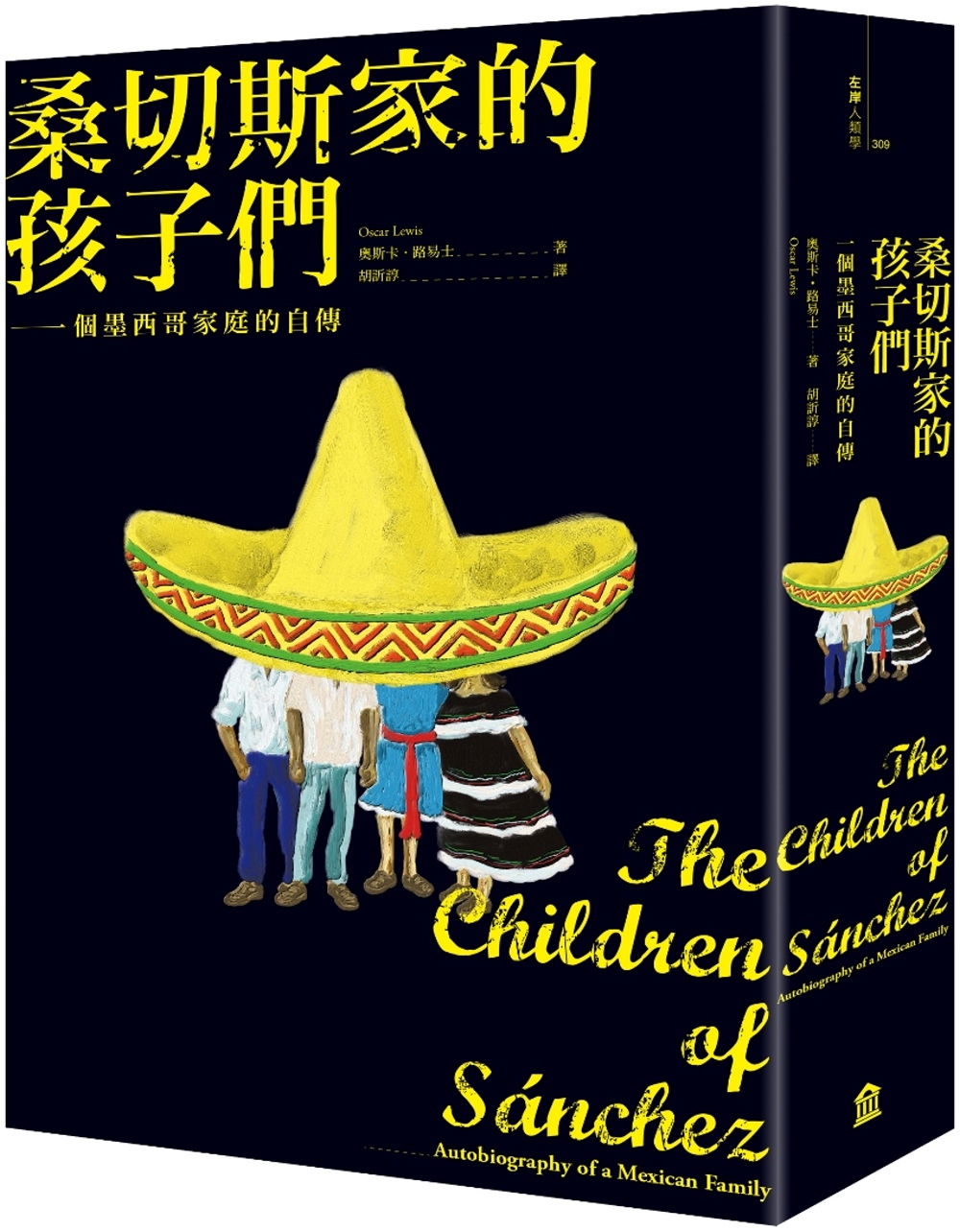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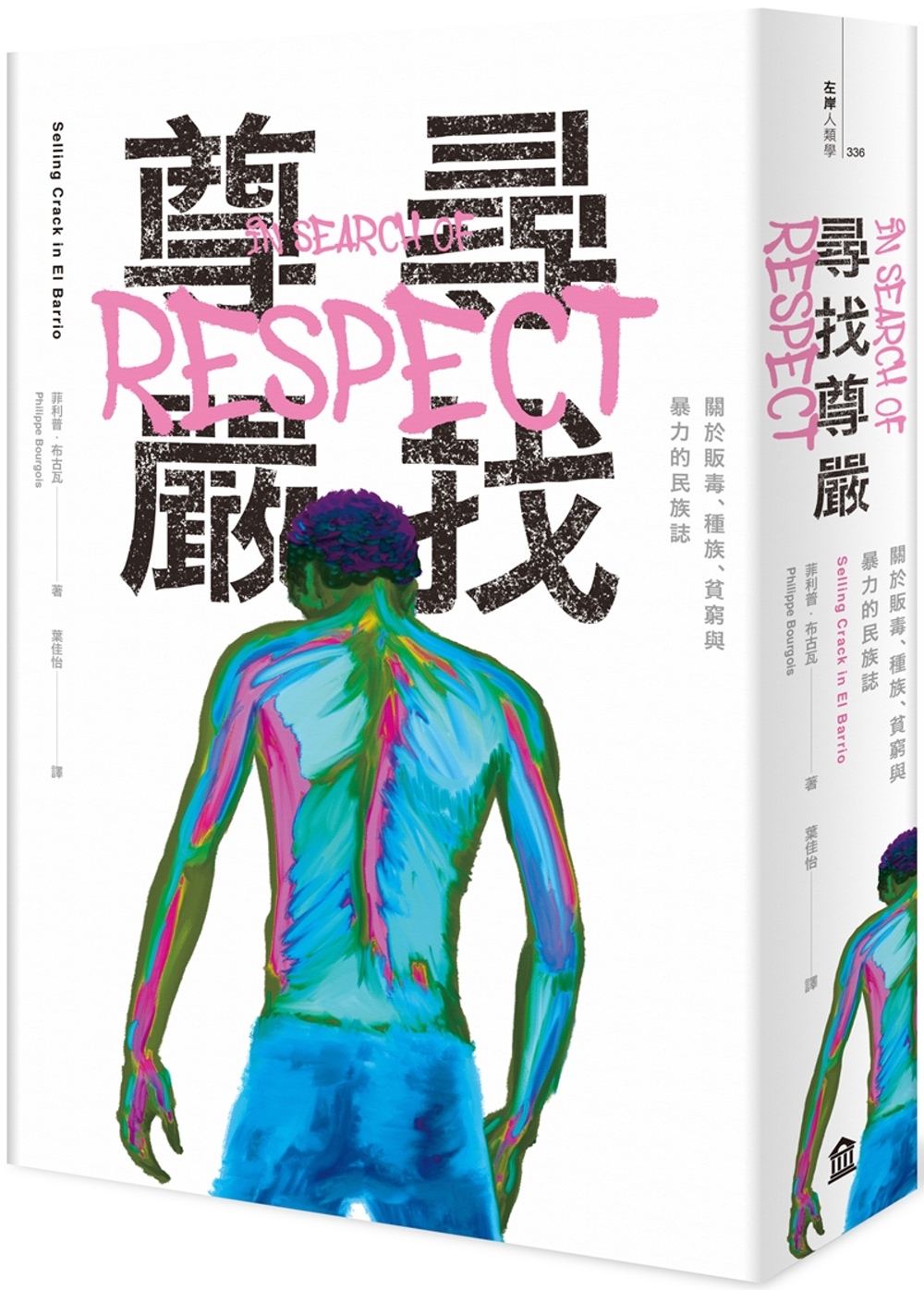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