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說起《孽子》舞台劇的緣起,一開始主要是董陽孜老師先提議,她興致高昂,像是懷抱著一個夢似的催促著白老師。反倒是我心還未熱,畢竟戲拍得久了,很難想像自己會與劇場沾上邊,因為那可是我從未涉獵過的專業場域。董老師對於《孽子》舞台劇的想像非常熱切,在她的邀約下,我去看了施如芳編劇的戲,她的腳本十分大氣,和我對這部劇的想像是契合的。後來,又再透過紀蔚然與創作社製作人慧娜有了進一步的接觸,那時我們並無多想,一切都是且走且看,因為沒有人知道資金在哪裡?製作方會是誰?未料,《孽子》這部劇後來竟成了二○一四年TIFA的首檔演出,這時我才開始緊張起來。
化整為零,舞台便是我的投影幕
在整個籌備的過程中是非常辛苦的,於我而言,身邊的人並非自己所熟悉的團隊,但大家都是劇場中的佼佼者,而我連許多專業術語都還聽不太懂。因此,在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我便告訴團隊的夥伴,要把我當成一個劇場的小學生,重頭開始。在心態上,我把自己歸零,重新學習。當然,我亦稍加運用了我所擅長的語言在這齣戲裡,雖然劇場中的細部技術問題並非我的專業,但我能去想像燈光、想像畫面該有的樣子……我將舞台當作是電影的投影幕,一幕幕去畫了分鏡稿,這是我較能掌控的。而現在能有如此舞台呈現,我真的要感謝美術孟超、燈光祖延、影像奕盛,以及舞監仲平,他們是如此充滿才華且熱切的幫助了當時的我。另外,還有素君老師華麗、靈動的編舞,作曲陳小霞與編曲配樂張藝也功不可沒,我們一路從影視合作走進了劇場。

在黯然石柱間穿梭的青春鳥
當劇要開始,布幕一拉開,根根粗壯而斑駁的大石柱矗立於舞台,它是我想表述的黑暗王國,沒落、頹廢且傷痕累累;它的壯碩對比出了底下人物的渺小,及其在命運中的微薄與脆弱,它象徵了一座神殿的殞落,青春鳥躍然而出。我明白,在許多人的想像當中,《孽子》應當是深暗且壓抑的,既定的框架深植在許多劇場人與讀者的心中,小劇場的想像顯而易見。這無可厚非,臺灣的文化產業資源有限,做一個夢都顯得奢侈極了。可在我們幾個人的心裡,對於這齣劇都有一個共通的想法:《孽子》,會是一齣大部頭的劇作,且將會以歌舞的形式進行呈現。我個人以為《孽子》這部劇應探討的不僅僅是我們已知的那些事,還要能在劇情當中,更加凸顯出人物性格與故事的呈現。第一次演出時,我們獲得了觀眾的一致好評,然而劇場圈卻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場面過於歡快,他們想要看到更多同志情感上的糾結與壓抑,但於我而言,這種情緒的表現,在電視版已經深刻地講述過,而且完成了。我認為,在他們被社會貶抑、限縮於那處黑暗小角時,勢必應有屬於他們的快樂,我想要在劇場版本裡,讓觀眾看到他們熱情奔放的生命!而關於所有內在情感的糾葛、外在環境賦予的壓力,我們透過現代舞蹈的方式,在序場便訴說完了,說完之後讓我們一起進到人物的故事裡,而毋需在兩個多小時的演出當中,不斷地去表現那沉悶、委屈的情緒。
我認為《孽子》之所以為《孽子》,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素便是在其時代氛圍的獨特性,在今日社會你我身邊仍不乏關於同志的故事,然而,那些情感的流動會有幾分差別嗎?我想,唯有那無可複製的時代感,才能帶出《孽子》舞台劇獨有的味道。

文學與劇場的語言,相互交錯
在我與白老師的合作過程中,最困難和最衝擊的,是我們彼此都有自己所堅持的理念,白老師十分在意他所有衍伸作品的呈現,而我也得承認白老師當時書寫《孽子》時的文字確實充滿巨大魔力。那時我告訴製作人,我得先躲起來,讓自己好好想清楚,才能與白老師碰頭,我需要一個導演的執行本,在文字與影像之間取得平衡。是以約莫快一個月的時間,我窩在我的工作室裡頭,未與白老師聯繫。我不斷去思考內心的想法,希望能讓文字與影像有一個好的整合。因為無論是劇場、文字抑或我所熟悉的影像,他們都各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表現語言,要將之整合成為一個可執行的版本,且得到白老師的認可,並非易行之事。
二○二○年《孽子》的經典重返
二○一四年的演出之後,時間轉瞬來到了二○二○年,適逢《孽子》小說發表四十週年、臺灣的同婚法案已然通過,白老師和董老師再度談起劇目的重返,湊起了大家的時間,開始製作。
事實上,對於第二次的重製,我曾擁抱著許多的懷想,那時候我最大的想法便是期望能有現場交響樂團與歌唱隊的加入,當時我找了衛武營的藝術總監簡文彬,他非常支持這個構想,但製作人很是頭痛、白老師亦不熱衷;再來則是劇院展演的問題,如此的編制,某些場地的限制便無法容下。那時我已開始進行新戲的拍攝,這麼一個想法,只能暫且作罷。我們找來年輕有才的劇場導演黃緣文主導第二次的重製,我並未給予他太多的限制,但緣文的壓力非常大,每個人都要他去看第一版的錄影帶,可錄影帶肯定是經過裁剪的呀!燈怎麼進來、幕怎麼拉,這些都無法在錄影帶當中全然呈現。在重製的後期我又跳了進來,二○一四年的演出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而奠基在這個基礎上,第二版顯得更為精煉了。
從影視到戲劇——回到純粹的創作裡
我還記得當時拍攝電視版的時候,龍刺鳳的那一幕傷透了我的腦筋,而同樣的問題在劇場裡頭再次出現,那一幕的畫面該如何讓觀者感到震撼而難以忘懷呢?在影視裡頭的那一個版本,我特別喜歡當龍子刺上阿鳳、阿鳳癱軟下去時,在他的臉龐有一抹對龍子寬容的微笑……而我該如何在劇場裡呈現這樣的氛圍呢?我畫好了分鏡,和美術、燈光、舞蹈進行溝通,我說我要讓整個舞台變成黑白的,唯有落下的彩帶、花瓣以及阿鳳的褲子是艷麗繽紛。雖然,對許多劇場人來說它是一個非常老派的做法,但我認為那會是你看過最美麗的落花瓣。而至於無法用鏡頭特寫去做的事情,就讓我們以肢體代而行之。你或許無法看到阿鳳臉龐的那一抹微笑,但我要阿鳳伸出手來、試圖去撫觸龍子的臉,卻在指尖抵達之前、便已氣數散盡,他的離開沒有殘念,是不帶怨、亦無有恨。

劇場的魔力唯有真走過一遭的人才能懂得,我記得二○一四年的那場首演十分成功,我開心得哭了,但他們告訴我會出現所謂的「魔鬼場」,亦即劇來到了第二場卻什麼都亂了套。我那時心想怎麼可能呢?可沒想到,真到了第二場,什麼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場演完我一出劇院,便把車停在信義路旁,趴在方向盤上狠狠地大哭了一場,像是失散的戀人找不回頭般的肝腸俱裂。那一刻我才明白,什麼是劇場的魔力。
劇場和拍戲不一樣,再困難的戲拍完也就放下了,但劇場不行。每一次的演出都是獨一無二的,今天的九十五分並不代表明日能依然如故,有太多的變數在操弄著,像是老天給了一個又一個的考驗,讓我們學習如何勇敢、如何調適。
我認為《孽子》的舞台劇在今年的演出別具意義,我和白老師認識滿二十年,而這書已經四十歲了。二十年前拍攝電視劇,它像是一種控訴,觀眾聞之而來,又或許是帶著窺探的心理,想要去瞭解另一個族群的生活型態。而今,台灣的社會環境更加健全了,終於我們能夠回到純粹的創作裡,去體會更多關於人性的脆弱與滄桑。當我們走出劇場時,不再是一種窺探的心思,而是更多的慈悲與溫暖。終於,我們可以真正地用藝術,去講述藝術,去欣賞藝術,這是我認為,在現今臺灣最幸福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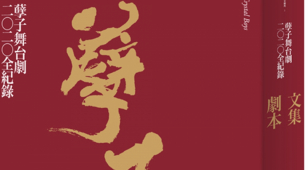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