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
金融界整個慘兮兮,明白狀況的每個人打從第一天就嚇得提心吊膽,他們似乎能看到未來一切即將分崩離析。嚴格來說,馬克沒受到多大影響,他的工作很安定──甚至可說比以前還安定,因為他專精的主權債務就是人們在金融海嘯時需要求助的事項。但是每個人能拿到的獎金都減少許多;這倒也還好,畢竟我們不算活在貧窮線底下──直到他很多朋友開始被遣散,那就真的嚇人。看著那些成年人不知所措,我嚇壞了;他們有小孩要上學,卻連房貸也繳不起,加上他們的妻子在懷孕後就沒再工作過。沒人事先想好後備計畫。那一年,朋友們來我們家聚餐時不禁痛哭失聲,他們離去時為此道歉,擠出勇敢的笑臉,保證會在搬回鄉下安頓完畢後再來拜訪我們,結果很多人從此再也沒跟我們聯絡。我們聽說有些搬回伯克郡跟父母同住,有些搬去澳洲工作,有些離婚。
馬克換了一間銀行;他原本那間的同事全被遣散,他一個人得做五個人的工作,所以他決定冒個險,去別的地方。
我不喜歡那間新銀行,感覺就是不對勁。那裡的男士們竟然有辦法讓自己的身材既肥胖臃腫又肌肉噴張。他們各個身材走樣、菸不離手;我以前其實一點也不介意旁人抽菸,但現在看他們抽菸,彷彿散發一種緊張又絕望的氣息,這很讓我擔心,那種菸味聞起來像苦楚和破碎的夢想。他們有時候跟我們一起上酒吧,彼此抱怨妻小,好像我根本不在場,彷彿他們如果當初沒娶老婆,現在就能在哪片沙灘上逍遙。
馬克跟他們不一樣,他懂得照顧自己。以前的他跑步、游泳、打網球,讓自己維持健康,現在卻得跟那些傢伙天天共處十一個鐘頭。我知道他意志力堅定,但我看得出這開始對他造成影響。而現在,在這一天,偏偏挑這一天,在我們的週年紀念日,他宣布他想更專心工作。
專心,意思就是我會更少見到他。他原本已經工作過度。他在每個上班日都是清晨六點起床,六點半出門,在辦公桌前吃午餐,晚上七點半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門,回到我面前。我們共進晚餐,聊聊天,也許看個影片,然後他在十點上床熄燈,周而復始。
「可是這就是我想改變的,」他說:「我已經在那裡工作了一年。我剛進這間銀行的時候,他們保證我只是暫時待在這個職務,直到我們重整這個部門。可是他們不讓我這麼做,沒讓我重整,所以我其實沒在做他們雇我去做的事。」他嘆氣,揉揉臉。「這也無所謂。可是我得跟勞倫斯好好談一次。我們得討論我的年終獎金,或改變組員,因為裡頭有些小丑根本在混。」他停頓幾秒,看著我。「我是認真的,艾琳。我原本不打算告訴妳,但星期一完成那筆交易後,漢克特打電話對我哭訴。」
「他為什麼哭?」我難掩驚訝。漢克特跟馬克共事了好幾年。馬克在一切急轉直下而打算離開原本那間銀行時,保證會想辦法把漢克特介紹進新的銀行,也說到做到。馬克在跟新東家談判時,把漢克特列為必要條件:除非他們倆一起進新銀行,否則免談。
「妳還記得我們昨天等著他們提出的數字,好決定要不要簽字?」他凝視我。
「嗯,你在停車場接的電話。」我對他點頭。昨天在旅店吃午餐時,他中途離席,在停車場的碎石地上來回踱步一小時,任憑餐盤上的食物變涼。我等他的時候拿書出來看。我是自營業者,所以我熟知「講電話講到像在流浪」這回事。
「嗯,他跟我說他收到數字。平時想在辦公室找到交易桌的那些傢伙就很不容易,更何況現在是假日期間,而且他們刻意找他麻煩。他們要求等我們回去後討論加班時間和行為規範。簡直荒謬。總之,漢克特跟紐約那邊聯絡,試著解釋辦公室裡沒人而且數字為何一直拖延,紐約那邊氣得發瘋。安德鲁……你還記得紐約那個安德鲁吧?我跟妳說過,有關──?」
「我在布瑞安的婚禮上聽見從電話裡對你飆髒話的那個?」我打岔。
他噗哧一笑。
「沒錯,安德鲁,他很……很緊繃。總之,安德鲁在電話上朝漢克特咆哮,漢克特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批准那筆交易、寄出去,然後睡覺去。醒來時發現幾百通未接來電和電子郵件。搞半天,他們在那串數字的尾巴多加了一個零。交易桌的葛瑞格那幫人為了拖延這筆交易而這樣惡搞,他們以為漢克特會在寄出前檢查,如此一來我們下星期都回到辦公室時就會叫他們重做。可是漢克特沒檢查,他簽字批准,而且寄出去了,這就成了有法律效力的契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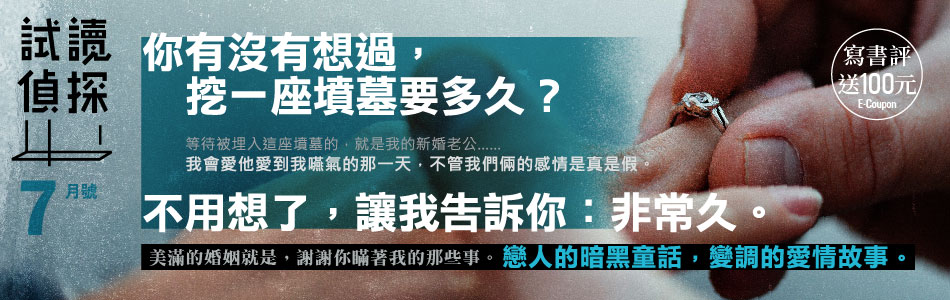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