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致亨破解了哪些關於臺語片的迷思呢?迷思一:臺語片始於一九五六年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止於一九八一年的《陳三五娘》。錯!這種「斷代史」說法,會讓人看不見臺語片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也等同將臺語片時代定位為臺灣電影發展歷程中的一段「支流」。但臺語片在五〇年代中期興起後,直至七〇年代急遽衰亡前,總生產量達上千部,制霸臺灣影壇,國語片長期連車尾燈都看不到,毫無疑問應是「主流」才對。
迷思二:臺語片在七〇年代迅速沒落是自己不爭氣,太過「粗製濫造」所致。錯!臺語片末期的確有粗製濫造的現象存在,但此為結構性問題爆發出來的表面病徵,望聞問切找出內裡病灶便是全書核心所在。先前主流論述多云臺語片的終結是「自然死亡」、是「低俗」引來的咎由自取,作者梳理海量史料予以反駁,翻案證明:臺語片為「非自然死亡」,「低俗」乃人為製造出來的汙名。
迷思三:儘管六〇年代臺語片風華正茂,但那是商業領域上的勝利,討論臺灣戰後文化史不討論臺語片是很OK的。大錯!臺語片興衰起落的故事,正是幫助我們反省臺灣戰後文化史敘事主旋律的極佳個案。當你看到張英《天字第一號》的構圖,當你讀罷鄭義男《白痴之愛》的劇情梗概(拷貝已佚失,男主角陽明為《痞子英雄》導演蔡岳勳之父蔡揚名),當你看完林摶秋的《五月十三傷心夜》、《六個嫌疑犯》,應會大感訝異:原來六〇年代不是只有《劇場》那一掛文青,在吸納、反哺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養分,臺語影人同樣積極觀摩進取,融入創作中。這些跡證明明白白,但在既有戰後本土文化書寫中,始終被忽略。
為什麼會被忽略呢?因為臺語片被官方正史給邊緣化了。書送印後,四小時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剛好在Netflix上線。在欣賞這部「臺灣新電影」代表作時,我心裡不時冒出作者序言中的這段話:
我們看待臺灣戰後文化史的目光,已經停留在菁英視角,尤其是官方視角太久,若我們願意稍微轉移一下視線,將臺語片擺在正中央,全新的臺灣文化史敘事將隨之呈現眼前。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六一年。如果我們熟悉臺語片的歷史,看到開頭小四兒和小貓王跑去片廠偷窺,你會知道那是臺製(臺灣省電影製片廠),應該也會想到再過不久,臺製將力邀林摶秋玉峯影業培養出的臺語片實力派玉女張美瑤復出。接著你應該又會想到,那一年,張英登門邀請白虹演出「天然禽獸裝臺語童話故事片」《大俠梅花鹿》,叫好又叫座,今日已獲深度影迷奉為臺灣「邪典」經典。最後,你應該一定會想到,迥異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沉重基調、陰暗結局,跟電影劇情處在同一時空的臺語影壇,隔年就要邁向百花齊放的全盛期,北投就是臺灣的好萊塢。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多希望不用加上「曾經」。
盧意寧
春山出版社副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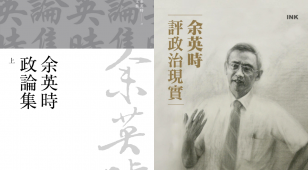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