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麗娟(1960- )的〈童女之舞〉在1991年獲得聯合報第十三屆文學奬短篇小說第一名,算是台灣同志文學奪得主要文學奬的先驅之一。在此之前,凌煙在1990年以《失聲畫眉》獲得自立晚報百萬小說奬,書中描繪歌仔戲班內女性表演者和異性與同性之間的情慾;在此之後,大批同志主題的作品紛紛摘下大大小小文學奬奬座。
當時,聯經出版社將每屆文學獎作品和評審會議紀實編印成冊。〈童〉及其評審紀實收錄在《小說潮:聯合報第13屆小說獎暨附設新詩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1992年初版,1997年三刷──當年這種文學獎作品集還很有市場)。在評審紀錄中,五位評審對〈童〉的評價都很正面,覺得這個題材少見(再過幾年後他們就不會這麼說了),也都討論文中女女情誼到底算不算是同性戀(他們沒有定論,但態度算是友善)。
有趣的是,評審們都提及英美女女文學經典(但未提及中文世界的女女文學前例),仿佛是要借外國之力為本土背書:李有成聯想到《紫色姐妹花》,齊邦媛聯想了《寂寞之井》,而張大春表示自己在1980年代就讀過 Lillian Hellman的書(對台灣讀者而言,她最有名的作品應是拍成《雙姝怨》(Children's Hour)的原著小說;《雙》由奧黛麗赫本與莎莉麥克琳演出雙姝)。在那個年代,女同志文學的範例好像只能在國外尋找,而無法在國內想像。
那時候還是文學獎的黃金時代。楊德昌在1986年推出的台灣新電影經典之作《恐怖份子》,片中女主角繆騫人因為獲得文學獎而上了電視 ,結果捲入情慾風波。要不是那個年代重視文學獎,《恐怖份子》的情節就要少掉一大塊,〈童〉的得獎與評審討論也就不會成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文壇歷史事件。
我無意重彈「文學獎今非昔比」的詠嘆舊調,而想要指出「公共性與私密性」的關係:文學獎當年那麼重要,是因為它們曾經具有高度「公共性」;同志題材作品往往以「私密性」著稱(同性戀本來就是「不能說出口的愛」)藉著獲得文學獎而曝顯在公眾面前,形同私密性攻佔了公共性一樣叫人痛快:就好像是本來只敢偷偷在暗處牽手接吻的同性愛侶竟然可以在公共場所公然牽手接吻那樣爽。
許多同性戀者將「決定出櫃現身」、「參加同志大遊行」、「爭取同性戀婚姻」(公然結婚並受公家認可)視為英雄之舉,都多多少少出於私密性反攻公共性的痛快心理。
但是「私密性」和「公共性」都是意涵繁多的詞語。「公共」尤其複雜:都更建商所稱的「公共」空間和「公共」利益、哈伯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走出學院象牙塔的「公共」知識分子、乍看免費其實要收錢的「公共」停車場、看似被公家認可實則被公家撲殺的「公」娼,都通往了相異的「公共」概念。 同志並不能僅僅憑著「出櫃」、「遊行」、「公然結婚」就感到滿足,因為除了這些私密攻佔公共(哪一種公共?)的明顯範例之外,還有太多別的「公X私」可能性。
文學獎的公共性至少有兩種:
一,主辦單位藉此促進「公共利益」(為民眾提供學校之外的文學教育);晚近各縣市文學獎興起,無非也看重了這兩種公共性──老實說,尤其是將之視為公關工具。在〈童〉的評審會議中,評審們以這個題材私密的文本為起點,引用英美經典,為公眾進行文學教育──這是為了公共利益;但他們(在學校體制之外)的公眾教育卻意外成了同志文學教育(在當時學校課堂內也不大可能光明正大教同志文學),而且意外地為同志做了公關。
二,主辦單位也藉此達成「公共關係」(公關;文學獎是主辦單位的公關廣告)。
然而,再過數年,待獲奬的同志作品漸多之後,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評審們就要開始爆出「同性戀題材的投稿太多」、「同志題材趕流行,總有過時的一天」等等抱怨。針對評審這種反應,而我的看法是:公共性跟私密性的矛盾浮出檯面了。寫作者(尤其還處在青春期或後青春期的年輕寫作者)將同志題材視為進可攻公共性(曝光,得獎)退可守私密性(不管是同志或非同志都可藉著私密而狂野的同志題材進行身心的告解);然而,審稿者已經不認為公共資源(文學獎)應該持續腋助私密文類(同志文學,以及連坐的情慾題材等等)。評審大老紛紛表示厭棄年輕寫作者一直再寫「肚臍眼的世界」而該關心「真實社會的苦難大眾」──這些大老的反應,我並不認為百分之百是「恐懼同性戀」或「恐性」心理作祟,而認為是他們對於公共性的焦慮。按他們的邏輯,作為公共資源的文學獎應該改而投注到更應該被公眾關注的對象,不該再是同性或情慾,而該是(想像中的)真實社會的勞苦大眾。與其說他們真的特別關心(知識分子所想像的)社會大眾,不如說他們一時想不出來有甚麼更有正當性的題材足以配得上被神聖化的公共性。
當評審們這樣想像文學獎的意義時,他們的首要關懷已經不是文學或美學的價值,而是悍衛他們所想像的公共性。書寫同性或情慾的私密文本未必是壞的,但描寫所謂該被寫的社會、大眾的文本──見諸古今國內國外──卻常常是教條的。也該承認的是,社會大眾之內本來就存在同志,同志之中本來就存在社會大眾──公共性本來就不可能跟私密性完美切割。
在〈童〉得獎的那一屆,林裕翼(1963-)也剛好拿下兩座獎座:他的〈我愛張愛玲〉為戲仿張愛玲的後設小說,獲短篇小說第三名;他的〈白雪公主〉獲得極短篇小說獎,剛好是在文本之內(而不是文本和評審之間)爆發公與私的矛盾:小說主人翁在私生活的情人是一位單親媽媽,但主人翁跟情人卻不能出入公共場所,更別談公開結婚──主人翁在小說最後宣布,因為她本人也是女人,所以她跟她的情事只能私了,不能公證。小說刻意平行地安排兩種愛侶:異性戀伴侶是被公然祝福的,同性戀伴侶卻是私下憋氣的。
〈白雪公主〉這個題目也展現了另一個同志文學常見卻很少被討論的特徵:「童話故事的傾向」。小說呈現了兩種世界:世俗世界 vs 童話世界。在世俗世界,人人接受社會常規的安排,成為主流社會的參與者;童話世界仿佛提供了世俗世界的另一種選擇,童話中人拒絕長大,抵抗男婚女嫁的成年人常規,也就可以自己私底下當同性戀。當年所謂的「酷兒文學」縱然跟所謂的「同志文學」之間存有立場差異,但「酷兒小說」也常常依賴同志文學的童話故事傾向:洪凌(1971-)的《異端吸血鬼列傳》取法自青少年的奇幻文學,紀大偉(1972- )《感官世界》的〈美人魚的喜劇〉擺明倚重了童話,陳雪(1970- )的《惡女書》深具童話色彩/夢境氛圍,以致於被導讀者楊照要求:(私密的)女同性戀該面對(公共的)真實社會(即「女同性戀請長大吧」)。陳雪和一些學者已經質疑了楊照認為理所當然的正統社會。童話世界展現了別於主流社會的真實,並非主流社會所宣揚的真實就是人人都要照單全收的。人生的真實面並非只有一種。
〈白雪公主〉的結尾是足以驚嚇當年讀者的哏,是因為當時讀者想不到小說主人翁竟然是女子/女同性戀者。這個哏放在1990年代末就行不通了,因為彼時讀者已經見過多種女同性戀小說主人翁。要體會〈白〉的妙,就必須將之歷史化、脈絡化,指認它是「認知」前夕的歷史產物:此認知乃是對於同性戀主體性的認知。這個認知得以形成,是因為台灣人對於同性戀的想像逐漸公共化。在原住民主體的認知得以公共化之前、在身心障礙主體的認知得以公共化之前,這些主體在主流文學(漢人的、身心健全的)中「猛然現身」(仿佛本來並不存在)也會造成類似〈白〉的驚嚇效果。
以上兩篇小說都收錄在林的短篇小說集《我愛張愛玲》(聯合文學,1992年)。集子中最受同志讀者留意的短篇小說應該是〈粉紅色羊蹄甲樹上的少年〉。這篇小說是典型的「成長小說」:小說主人翁在青春期偶然獲得經驗(尤其是性經驗)由此獲得知識(尤其是性知識),卻也往往因而覺得幻滅。小說主人翁是個高中男生,死黨是發育良好(體高毛豐的「野狼」)、聽說性經驗豐富的排球校隊隊員,崇拜國文老師因而將「中文系」列為考大學的第一志願。小說中平行陳列了兩種性的啓蒙:一邊是異性戀的,主人翁跟高中同學計畫好要結伴(因而公共?)去歌劇院看脫衣舞女(這種歌劇院是公共空間嗎?我認為它是同時揉合公共性與私密性的空間);另一邊是同性戀的,主人翁「在計畫之外」「獨自」爬到國文老師家門外的粉紅色羊蹄甲樹上,赫然目睹國文老師大叔跟野狼型排球隊員(疑,他理應閱女無數的猛男)在老師家親熱。異性戀那邊是公共的,害羞的,卻有「轉大人」的驕傲;同性戀這邊是私密的,羞恥的(對主人翁而言),看破大人齷齪真相的。
〈粉紅色〉也收錄在楊宗潤編、開心陽光出版社出版的《眾裡尋他:開心陽光當代華文同志小說選〈一〉》(1996)。林裕翼為《眾裡尋他》寫了〈粉紅色〉的後記,強調「偽善」(指國文老師的偽善)帶來無可補救的傷害,並推崇「誠懇」才能維持人性尊嚴。他並希望「圈內的朋友」可以加入「社會道德的網絡中」,「與社會中的每個人平起平坐,且受到尊重」。將後記比對小說,或許男生結伴去看裸女跳舞是誠懇的(男孩們互相承認對女體的慾望),而師生同性親熱(大叔和野狼甸甸吃三碗而不對外承認)是偽善的;前者是參與社會的,後者是不被社會尊重的。於此,公共性再怎樣色情,都是可以合理化的;私密性──某些年代同性戀者所依賴的救生圈──就是不道德的。
在同志的種種情慾之中,同齡的、平起平坐的同志性/愛關係本來就比較能上檯面,比較能被主流社會尊重;跨世代的同志師生戀則算是同志的家醜之一,只能藏在衣櫃裡,不然就要被主流社會暨主流同志所唾棄。
以上提及的林裕翼小說都以平行對照的方式,讓公共化的異性戀突顯私密化的同性戀。這種平行對照乍看之下很工整並合乎大眾對於同志的認知,不過這種工整的認知其實只是同志文化以及同志文學的冰山一角。同志文化對於主流社會的挑釁,以及同志文學對於種種機制(並不僅限於文學機制、教育機制)的挑戰,就在於同志並不遵守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切割。公共性和私密性對同志而言常常是「混搭」的。例如,同志的性並非乖乖守在私領域,而一直在公領域滲透──在女校中、在軍隊中、在保守宗教的國家中偷度同志情慾,在國內外文學中都很常見。
美國性別研究中的概念「公共的性」(public sex),就指出性未必只在私密空間發生的事實。這個概念所指的私密空間是指「家」(family/home),而家之外的空間就是公共的。台灣掀起風波的「火車趴」,和本地年輕人流行的「轟趴」(home party,私家被轉變為公家),都是公共的性。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新公園和三溫暖,都是公共的性空間。這些空間讓許多人(含同志本身)覺得焦慮甚或羞恥,原因之一是它們打亂了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分界,讓人覺得世界失去秩序。
林俊穎(1960- )在199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焚燒創世紀》 (主編是出版界奇人楊淑慧,編輯之一是奇人駱以軍)寫了一批中年男同志的聚散。他們有時候建立自己的家,在私空間裡跟愛人過點小日子,但他們把更多心力投資在家之外的公共的性。之前提過,吳繼文(1955- )的《天河撩亂》描寫了主人翁在1960或1970年代電影院目睹男男互相手淫的盛況,《焚燒》也寫了作為公共的性空間的電影院。小說中某人物,士英,「輾轉從朋友那得知的」(得知那家傳奇電影院),「傳話之人也沒去過」──也就是說,士英透過同志朋友的二手傳播才知那場所。這種同志私下傳口碑的行為,是公共的還是私密的?其實都是。士英輾轉得知,也輾轉來到電影院:搭公車過河(按:從台北市到北縣),出市入縣,再走路走到天黑,穿過菜市場,來到「很容易便錯過的一家小戲院」。士英「融入黑暗的莽林」(按:走入戲院),後來在一片黑暗中「相濡以沫… 在淵黑之中迸裂成億萬個分子,嘩嘩的灑下」。(我讀到這裡,覺得林俊穎似乎並非描寫吳繼文所寫的相互手淫,因為手淫應該不至於這樣澎湃。)
士英完事之後走出放映廳,在外頭打盹,醒後回廳再戰。再走出放映廳時,士英看見「一獸尾隨他之後出來」(按:獸,爆發獸性的男同志也),全身是汗,手裡提著衣褲,只穿了球鞋(所以這個同路人在放映廳內應該是全裸的,但穿了鞋)。士英看他穿衣,對方彎腰的時候「烏青的臀如同一粒鉛球」。後來有人問士英,這家電影院還在不在;士英答,早就拆掉了。
這本小說的主人翁也去一家健身俱樂部尋找肉體結合的快樂。健身俱樂部內有一間間「電話亭似的小房」,內有「一具具的裸身等待我去…」──這個俱樂部恐怕是(公然)以健身房之名,(私下)行男同志三溫暖之實。
這些公共與私密交錯的空間與人體,在霧漸漸散的時候,它們已經不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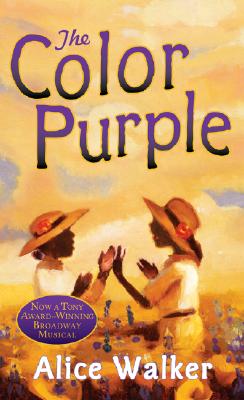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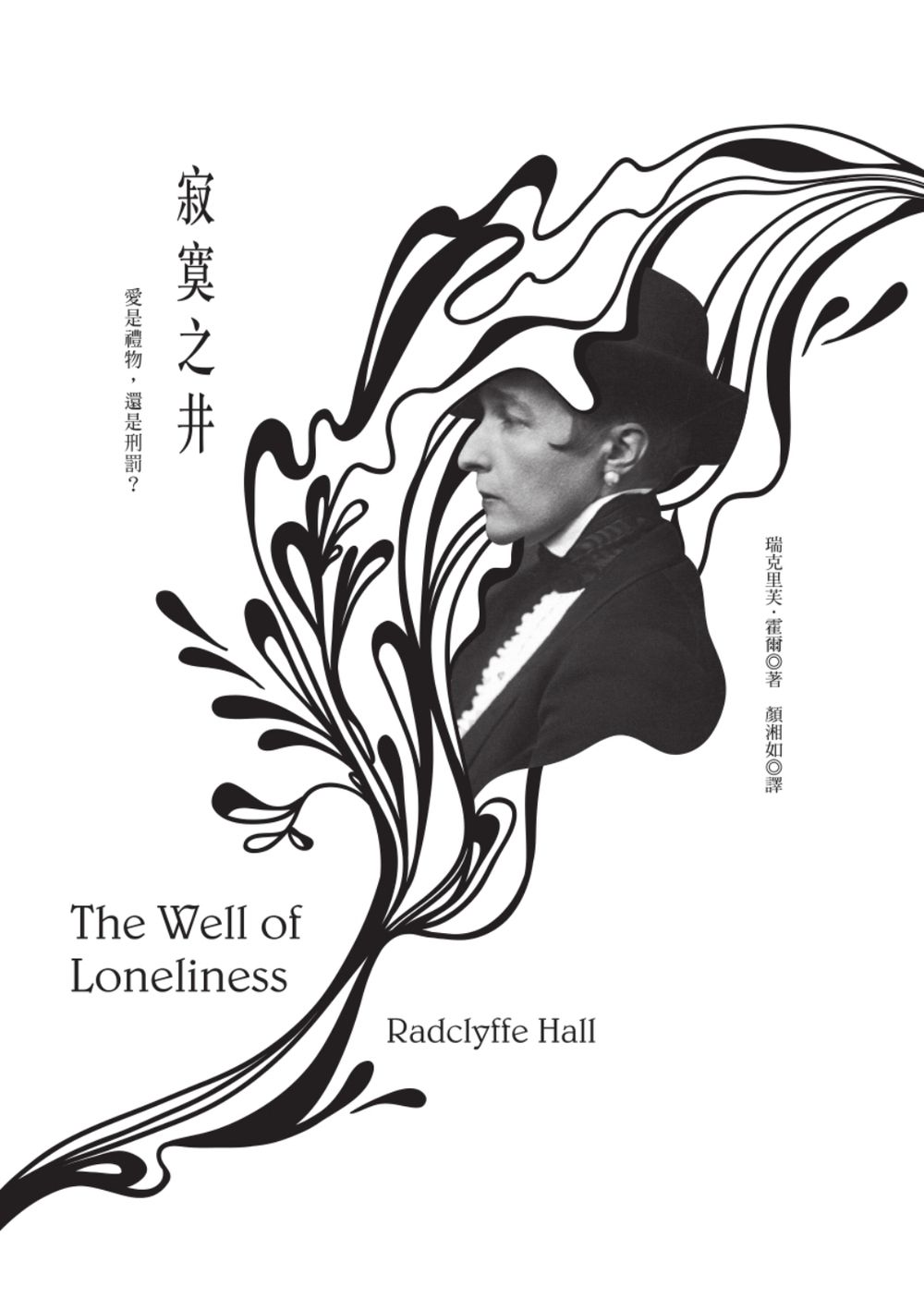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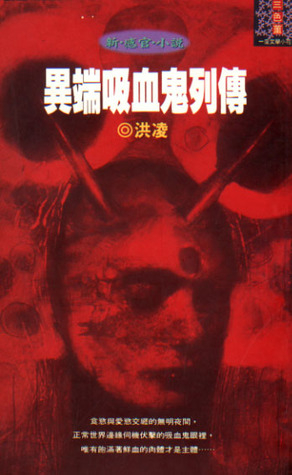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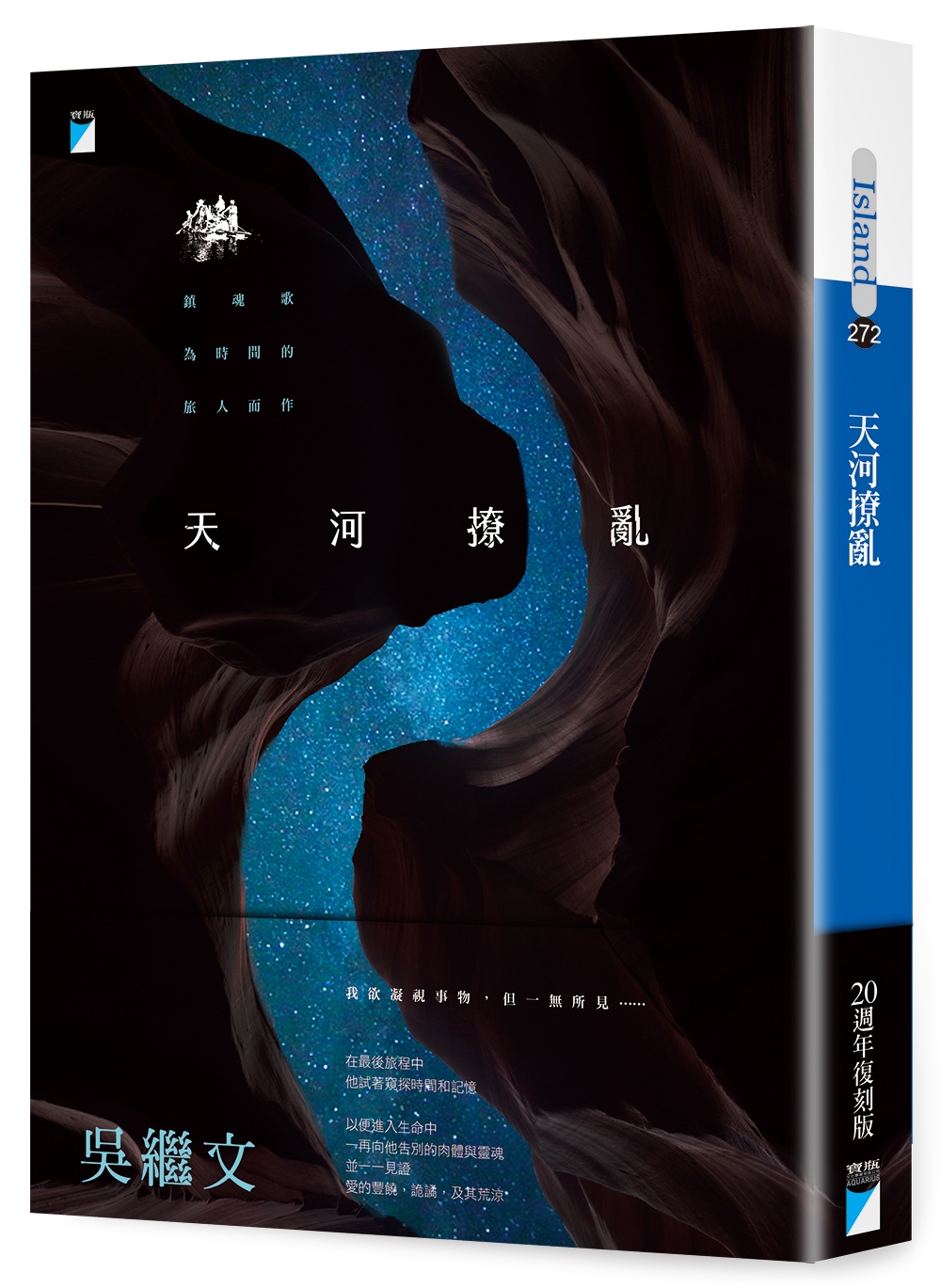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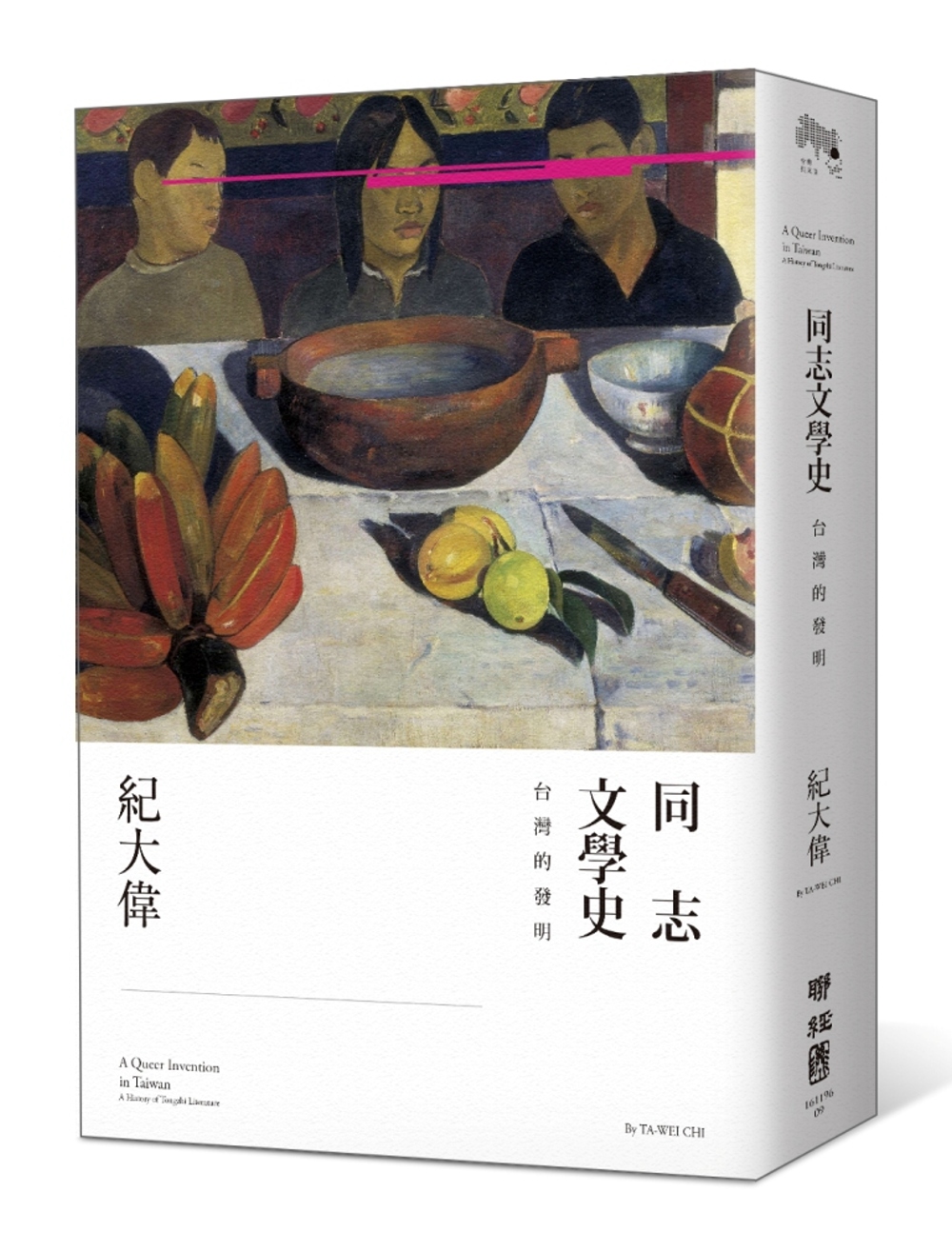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