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我,然後是我們,接下來他們出現,爾後「我們」和「他們」對峙著,互相猜忌恐懼。
族群關係是許多國家的難題,然而問題並非一開始就是我們與他們的簡單區分。沿著時間川流回溯,總會在上游發現各種人為因素撬鑿的罅隙,稍稍施力,裂縫便無可挽回一路蔓延下去。
2016年的法國暢銷書《小小國》(Petit Pays),書寫非洲內陸國蒲隆地境內圖西族(Tutsi)與胡圖族(Hutu)在90年代爆發內戰的始末,源於作者蓋爾.法伊(Gaël Faye)親身經歷。書中主角設定為與法伊相同背景的混血兒,父親是從法國來非洲尋覓新機的白人工廠老闆,母親是因60年代盧安達種族衝突奔逃至鄰國蒲隆地的圖西族難民。法伊藉由主角中上階級混血兒的身分,將隱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種族矛盾凝縮在一個社區裡,一眼描摹少年時代經歷的蒲隆地內戰與盧安達大屠殺,另一眼回望過去,追溯血河源頭至殖民時期種族政策,探究暴力的前因後果。
 蓋爾.法伊(1982-)是有盧安達血統的法國作家兼饒舌創作歌手。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盧安達人。在1993年蒲隆地爆發內戰、1994年盧安達發生圖西族大屠殺之後,法伊於1995年以難民身分抵法,定居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圖片來源 / 作者fb)
蓋爾.法伊(1982-)是有盧安達血統的法國作家兼饒舌創作歌手。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盧安達人。在1993年蒲隆地爆發內戰、1994年盧安達發生圖西族大屠殺之後,法伊於1995年以難民身分抵法,定居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圖片來源 / 作者fb)
主角加比以第一人稱敘述非洲的童年生活,成長的啟蒙意識與國家政局動盪平行並進,透過加比雙眼,可以看出歷史深漬的陰影在所有人身上發酵,例如,加比母親不想在戰亂連連的蒲隆地養育兒女,希望能移民到法國定居,父親卻認為在非洲才能維持白人特權階級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的意見也如父母互相扞格,如社區裡傲慢的德國人夫婦、家中支持胡圖族政黨的胡圖族廚師、加比父親工廠的剛果基督教徒工頭,渴望從軍投入圖西族復國行動的舅舅,這些人對國族與國家未來各有不同立場和詮釋。多方族群匯聚在此,隱斂過去的傷痕度日,但創痛仍時時發作,彼此缺乏信任,稍一摩擦便可能喚起痛楚,擦槍走火。
加比隱約察覺成人的世界布滿裂隙,無處安放萌芽的自我,只能與背景相似的同伴結為盟友,以嬉戲占領巷口。加比與他的死黨在社區的玩鬧,其實最接近「居住」的定義,也就是他日後移居法國領悟的「在肉體上融進一個地方的拓樸地貌,與那個環境的折曲起伏融為一體」,不是殖民者對土地產出物的掠奪,不是族群宣稱的復興固有領土,也不是往返於巴黎和衛星市鎮的定點通勤。居住是人與地理最純粹親密的關係,只有當人面對生命的原鄉,才能生出這種情感。
孩子終究會走出巷口,加比無法永遠只跟封閉的混血兒圈(死黨中唯一的純黑人是大使之子)往來,住處距離巷口一條街半的小混混法蘭西斯,便是孤懸在小圈子外緣的暴力閥口。隨著法蘭西斯加入小團體,引入外界煙硝味,男孩們便愈來愈像成人幫派,開始在內戰中區分我們和他們,認定胡圖族全是叛徒,以保護社區為名挾武器自重,甚至沾染了鮮血。天堂變色的回憶,也暗示了許多類似的族群團體,原本以凝聚個體的崇高理想號召人們,而後卻一步步走向極端,陷入仇恨深淵。
本書也沒有遺漏內戰與族群屠殺的另一催化劑,也就是白人對非洲事務的介入。白人以想像的體貌特徵,武斷區隔圖西族與胡圖族,排拒分化各族群,埋下了種族屠殺的種籽,遠至19、20世紀之交,近至內戰期間西方國家只援救歐洲僑民,放任暴力橫行,惡果歷歷可證。儘管如此,法伊沒有將所有白人塑造成負面的刻板形象,除了抱持傲慢殖民心態的德國夫婦外,他也寫了粗莽無禮卻視非洲為故鄉的比利時裔剛果人賈克,以及擁有普世情懷的艾柯諾摩普羅斯夫人。
有意思的是,法伊設定艾柯諾摩普羅斯夫人出身希臘,一個不曾參與近代血腥殖民的古老文化,西方文明的源頭。艾柯諾摩普羅斯夫人不斷借書給加比,使加比領略了閱讀的樂趣,在備受男孩團體嗜血傾向壓力之際,從文字獲得精神的喘息,象徵著當殖民政權嫁接的歐洲文明在戰爭中崩壞,古希臘文明做為西方文明根源,為荒蕪心靈提供了一絲救贖的可能。因此,縱使閱讀未能讓加比免於被暴力淹沒,仍促使他想像一個超越邊界種族,更廣袤的世界,保留生存的希望,得以在多年後鼓起勇氣返鄉,面對因親人被集體屠殺,困陷在嚴重創傷症候群的母親。
最終加比回到蒲隆地,母親將他錯認成屠殺中死去的表哥,顯示戰爭創傷之深,不僅積累了駭人的百萬死亡人數,也使倖存者的生命歷程就此斷裂。是否普世精神真能超越族群差異,彌合非洲大陸上縱橫交錯的裂痕?艾柯諾摩普羅斯夫人曾抄寫海地詩人賈克.胡曼(Jacques Roumain)的詩句送給加比:「倘若我們來自某個國度,倘若我們生於斯,在那裡土生土長,那它就會浸透在我們的眼睛,烙印在我們的肌膚和雙手;林木成了它的髮,大地成了它的筋肉……還有它的天空,它的氣味,它撫育的男男女女……」
透過詩句,法伊強調他所認同的普世精神,不是在西方歷史脈絡發展出的抽象價值,而是人與土地實在的連繫,不僅珍視自然景觀,也寶愛其上活動的人類構築的情感氛圍。正如10歲的加比將他在社區摘採的芒果樹、泅泳的溪流,在祕密基地的哥兒們都視為一體,只有當人能將存在於同一空間的其他人,無論血緣、宗教、族群認同,都當成土地的一部分,自我的一部分,歷史的罅隙才可能不再裂張,累世血仇停止輪迴,樹與孩童繼續生長。
加比已回到「小小國」蒲隆地,修補他與母親的連結,他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他記得微小的裂隙是怎麼開始的。同樣擁有多族群,同樣有各種力量撕扯角力,小小國台灣或許也需要回望裂隙最初的形成,那決定了樹與孩童,生長的方向。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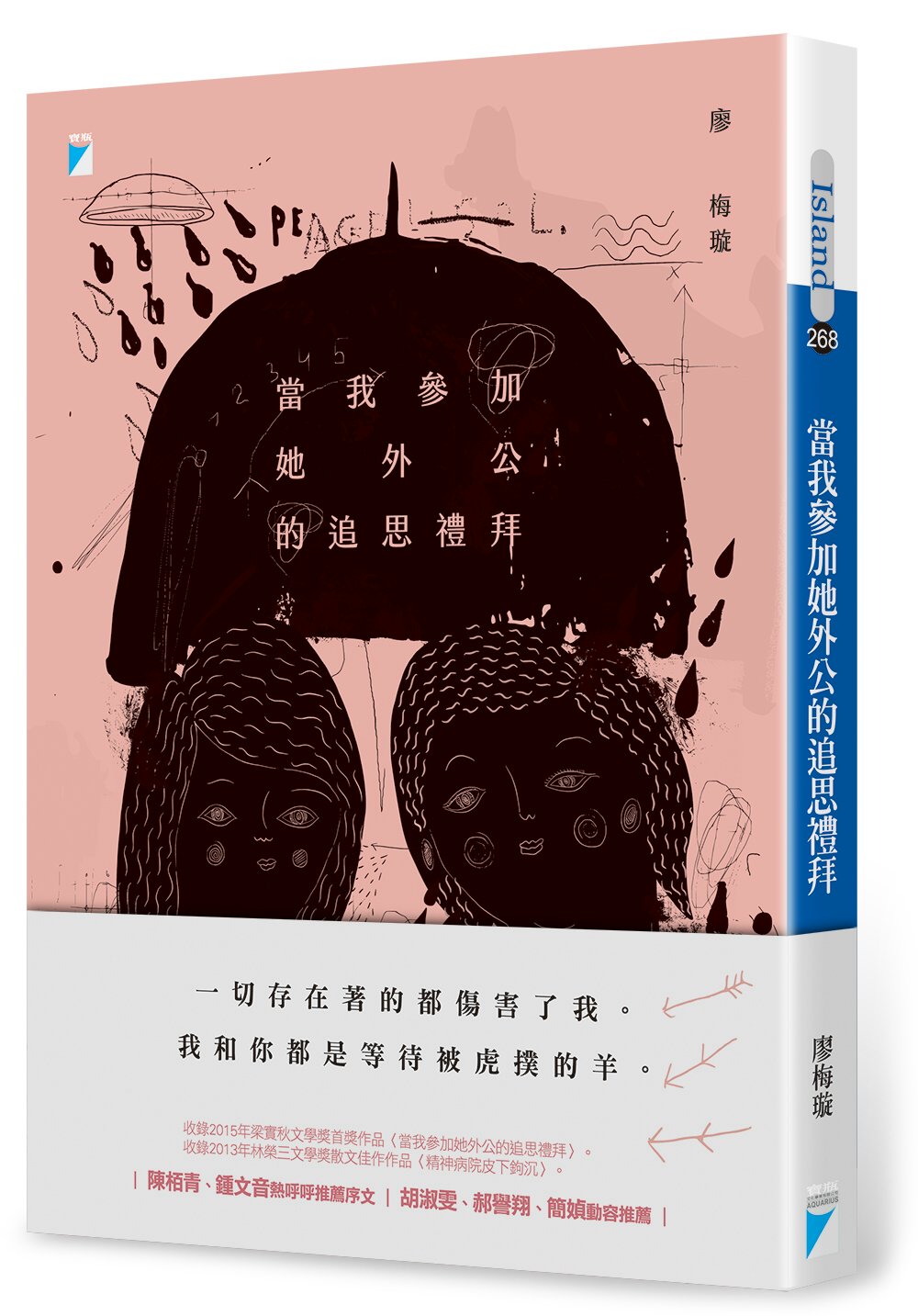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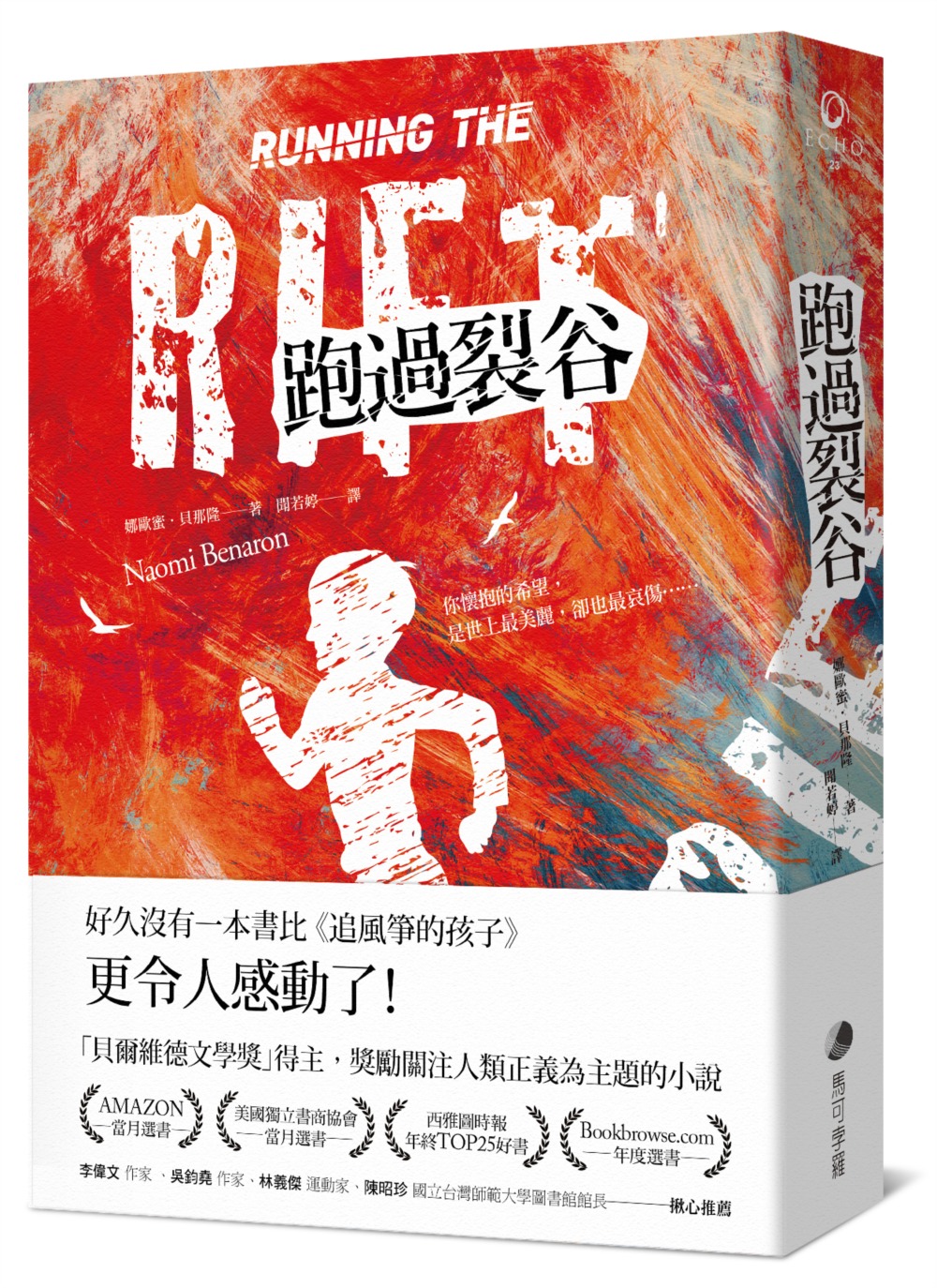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