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對世界華人來說,更重要的,是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也是第一屆唐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在此春風化雨;他不但是人文學術的指標,也居人格者的高位,多年來堅持反共,始終如一,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沒再踏上中國故土。這樣一位風骨超卓的學術名家,要出版回憶錄,又豈是勝事一詞足以形容?
他說他從沒想過寫「回憶錄」
余英時教授說他從沒想過寫「回憶錄」,我相信。然而,有一天,記者作家李懷宇,開啟了因緣。2007年,李懷宇從中國出發,前往美國東岸,訪問了余英時,夏志清,張充和,孫康宜等多位重量級教授,他們不管在歷史,文學,藝術諸領域的探索研究,都是望重一方的碩學鴻儒,這些訪談後來結集成《知人論世》出版。
然而,李懷宇在普林斯頓大學停留的五天中,與余教授三次長談,返回中國後,又多次電訪,寫成了二十萬字的《余英時訪談錄》初稿,這份初稿我始終未能一睹。就是這份初稿,觸動了余教授自己寫下回憶錄的契機,這樣的出版旅程和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可謂前後呼應。
多年來,出版余教授的學術著作,和他介紹的書稿,如康正果的《出中國記》,巫寧坤的《一滴淚》,以及陳穎士的《蠹餘集:汴涼陳穎士先生遺詩稿》外,我鮮少和他多說話,通常是藉由傳真,簡單報告編務上不解之處。
他是華人心中的人格指標,一種文化典範的依規,常有許多人找他,便也不想佔用他太多時間。我雖然焦慮著「訪談錄」的出版命運,不知余教授何時可改定,但又不好直問,只能暗自苦惱。
你不要著急,我的回憶錄會交給你出版
去年間,忽然接到余教授打電話來,開口就說:你不要著急,我的回憶錄會交給你出版。這通電話讓我空懸的心著實了起來,那種幾乎要感動落淚的心情,是我出版生涯中難得的體驗,此生難忘。
余教授既然說出口了,我也不好續問何時可以出版,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年。余教授的稿子是催不來,急不得的,當年他為朱熹八百歲冥誕所出版的點校本《朱子文集》寫序,一寫三年,寫成了一套三十萬字的學術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意猶未盡,續寫《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是學術界的驚奇,更是讀者之福,我只能等待時機。
今年三月間,余教授已有四大篇憶往文章先後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明報月刊》上刊出,感覺出版似乎有了眉目。之後又接到中研院黃進興副院長轉來余教授最新的手寫影印稿,我估量一下字數已有十一萬餘字,段落又剛好落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結束,於是徵求了余教授的同意,先出版上篇;下篇再等余教授蘊釀寫成。
赴美拜見余教授之前,十分忐忑,當我終於有機會單獨面謁時,我應該要說些甚麼?聽說余師母要開車到車站接我時,更是嚇壞了:這……怎麼可以?行前接到余教授電話,我把自己的疑慮告訴他們,余師母說是小事。當我終於抵達普林斯頓時,整個心奇怪地放鬆下來,也許是滿眼綠意,更也許是濃重的人文氣息讓人心靜。

踏進余教授的家中時,他已站在門口等了,心中忽然湧上了阿姆斯壯的名言:這是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感慨無限。我脫鞋子進屋,他說:我們家不脫鞋。於是,我又穿上鞋子,直接踩上他家的地毯,踩得心虛。清雅明亮的廳堂,被綠蔭圍繞,十分舒適,坐下來就不想動了。書稿已經校好了,稿子了上面貼滿師母所謂的「小國旗」。
我也會寫幾個字給你留念,我知道你自己不會開口的
我們都覺得書名用「余英時回憶錄」直接又明瞭,不過他還沒題好字。他說:心情不對。我說;沒關係,滿意了,再給我。他突然說:我也會寫幾個字給你留念,我知道你自己不會開口的。我當下愣住了。沒想到他會這麼說,那一刻覺得彼此的距離很近。
余教授通常下午見客,但不能聊太久,聊久了,氣不足就有些氣喘,讓人心疼。他笑說:我現在是英雄氣短了。所以要開始兒女情長了,我接著說。「兒女情長」,他呵呵笑著,重覆講了一次。余教授雖說自己英雄氣短,但文章寫來文氣酣暢,底蘊深厚。余教授當年為《一滴淚》寫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勵巫寧坤先生繼續書寫。然而,「心史」的概念正是《余英時回憶錄》的敘述主軸,少寫生活細節,而更著重在知識分子學思之路的精神轉進中,含金量十足。
他不懂張愛玲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談,而且談這麼久?
我們雜談魯迅, 張愛玲,錢鍾書;也談臺靜農,殷海光,談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選擇。他最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覺得十分深刻;他不懂張愛玲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談,而且談這麼久?我說;您問王德威教授會更清楚。祖師奶奶的部份,我還是別亂說的好。他認為張的《秧歌》寫得好。大學時曾讀錢鍾書的《管錐篇》、《談藝錄》,但根柢不足,只當閒書看,領會不多。
那幾年,我們就住在宋朝裡
我們天南地北閒聊,離不開中國,台灣,放開心來談,談得自在。他很意外我們居然沒這樣聊過。他說:我現在的力氣只能專注在學術論文的英譯和回憶錄的書寫了,當年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意外,本來我的老師錢穆寫過的,我是不想再碰的,沒想到一碰,工程浩大,借了許多書重讀,書多到舖滿地上。余師母接口說:那幾年,我們就住在宋朝裡。
我們從下午聊到晚餐,進到餐廳繼續聊,余教授夫婦心情很好,竟點滿了一桌菜,難怪,一進餐廳,雖然只有三個人,也堅持要坐圓桌。真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如果沒有過去埋首紙頁地編書,恐怕也踏不了這一步;然而,這一歩,我走了將近三十年。
這趟旅程其實是一個編輯的朝聖之路。我重新洗滌自己,滿懷感恩。
文章:經允晨發行人廖志峰先生授權刊登(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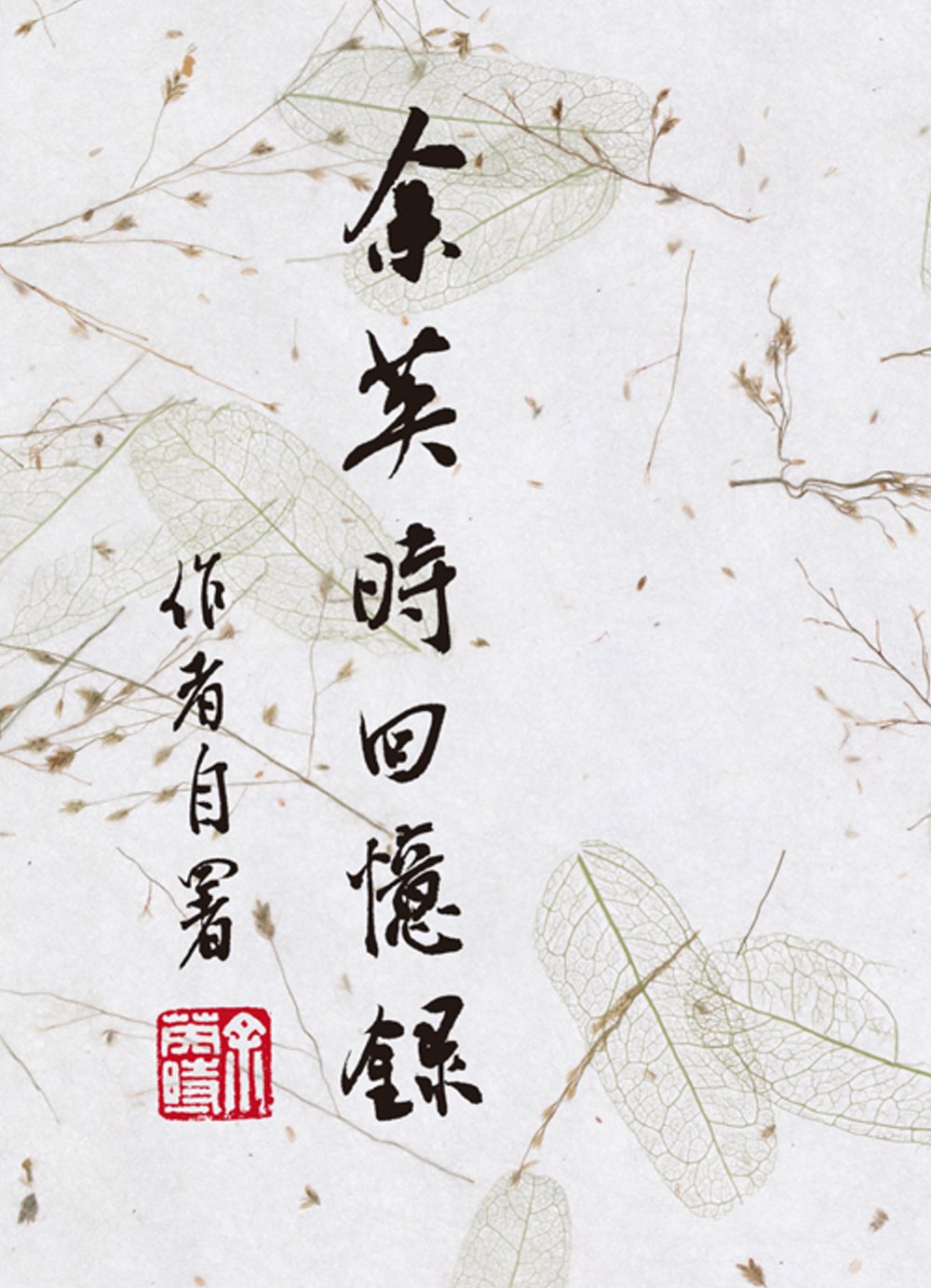





![秧歌[張愛玲典藏新版]](https://www.books.com.tw/img/001/047/82/00104782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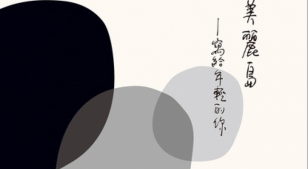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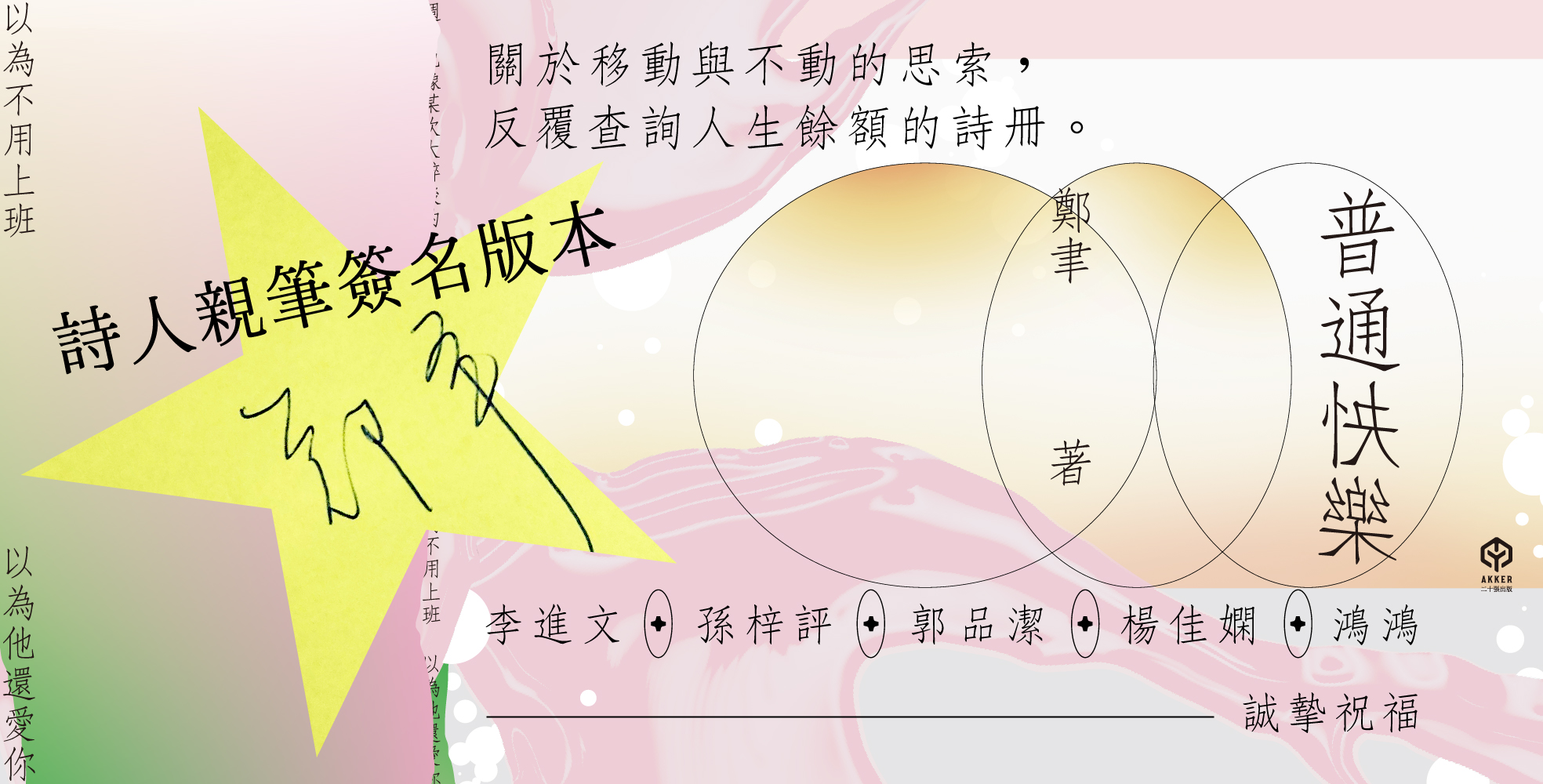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