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為生活所逼迫,以窮困的肉身直面社會與自我的近代日本天才詩人石川啄木,1909年在《東京每日新聞》發表評論:〈可以吃的詩〉。在該評論中,石川回顧自己的文學之路、考察當時文壇的狀況,以及對當下文學運動的期待。他希望詩人不要成為身分特別的人,詩也不應是裝飾品,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宛如每日的飲食。兩腳立定站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詩,是用和現實生活毫無間隔的心情,歌唱出來的詩。把原本在我們生活中有或沒有都沒有關係的詩,變成一種必要的東西,這就是詩存在的唯一理由。不是什麼山珍海味,而是像日常食物一樣,對我們來說是必要品的那種詩。
那麼,現實生活又是什麼呢?
啄木寫〈可以吃的詩〉的時間,大約是明治末期。從幕末開始,已經經歷了四十年了,不顧一切地近代化急行軍之後,明治維新的開國理想已初步實現。近代國家確實形成了。對外,在日清、日俄戰爭之後,擠身大國之列,與西方比肩。從明治初期的國家擴張過程中,也取得了殖民地,並在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國內在政治上的發展是天皇制的形成與國家權力的鞏固。但社會又如何呢?人心的變化呢?在急進近代化的途中,既有的社會、義理,乃至心情,如何面對這麼急進的變化?這是明治末期的日本人所面臨的課題,不單單是思想、意識上的挑戰,更是現實中日常生活的挑戰。
《「少爺」的時代》全五卷,以多線、層疊的說故事模式,透過夏目漱石、森鷗外、石川啄木、幸德秋水等主要人物、環繞在這些主角周邊的各種社會位置的不同人群的匯集聚散,以及代表性作品的形成,在東京的都市空間中,呈現此時的日本人對時代的摸索、生活的苦鬥、與自我的探求。
在東京的都市空間的各種裝置,如車站、公園、新橋、電車、街道、酒館、宿舍、官署、報紙、文學社群間的交會,形成了《「少爺」的時代》全五卷的空間紋理。登場的文學家、政治家、軍人、學生、俠客、小偷、祕探、記者、女性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勞工、女傭等人,處於同一時代的都市空間中,實際上卻是異質且複數時間並置於現實生活中,是理念上的西方理想與日本獨立之間的對立;是國家秩序與理想社會之間的衝突;是性別角色的協商;是家族與人情的重量;是人與人之間的義理;是生活本身與自我的探求。如此的時間操作,甚至延伸到虛構角色與實存的歷史人物共處於同一都市空間,虛實並進。愛麗絲的登場,舞姬從作品中走出來到了東京,直接衝撞森鷗外所代表的個人、社會與國家。
 《「少爺」的時代》中,讓各種身分、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時空者齊聚。(圖/出自《少爺的時代》© Natsuo Sekikawa, Jiro Taniguchi/Papier 2014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少爺」的時代》中,讓各種身分、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時空者齊聚。(圖/出自《少爺的時代》© Natsuo Sekikawa, Jiro Taniguchi/Papier 2014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然而明治時代又是怎麼結束?在急速的變化中,石川提出了另一種反省。在《「少爺」的時代》全五卷中的《明治流星雨》,做為主題的大逆事件,是當時國家權力擴張的頂點。事件發生後不久的1911年,石川啄木發表評論〈時代閉塞的現狀〉,並在日記中開始寫下親近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字。在評論中,啄木批評當時陷入混亂狀況的文壇,特別是種種宣稱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家與作品,其缺陷在於不敢直視國家的暴力,亦不敢回顧明治以來的種種轉變。此前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雖以直視現實、描寫實際的狀況為宗旨,卻無視此一閉塞感的主要原因,乃是國家機器的直接暴力,以及內在於當下社會制度的壓迫。在閉塞的現狀中,啄木呼籲朝向「明日的考察」,把全副精神傾注於明日的探索上。明治時代終於還是結束了,但對於「明日的考察」,仍在持續進行中。
漫畫是什麼?可以吃嗎?
在1980年代末,時代來到了昭和末期的日本,透過漫畫重建1910年代前後明治末期的日本,谷口治郎與關川夏央聯手創作的《「少爺」的時代》全五卷,或許就是石川啄木所說、「明日的考察」的一種形式。在昭和末期泡沫經濟的歧路上,思索明治人面臨的生存狀況。在「過去的未來」的時間中,是當代的日常生活使得這種「回到過去考察明日」的思考成為必需。而在平成末期的現在,跨越了語言文化的藩籬,衛城出版重新翻譯、出版了《「少爺」的時代》全五卷,在臺灣的時空下閱讀這套漫畫,或許能引起讀者們的共感吧。借用石川啄木「可以吃的詩」的意涵,《「少爺」的時代》也是屬於我們當代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生活、面對存在狀況的問題時,可以吃的漫畫。
陳偉智
臺大歷史學博士班、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延伸閱讀
1.文學與漫畫的完美結合──董啟章讀漫畫《「少爺」的時代》全五卷
2.每個人都要擁有一本谷口治郎──阮光民讀漫畫《「少爺」的時代》
3.明治時代的光與影──盛浩偉讀漫畫《「少爺」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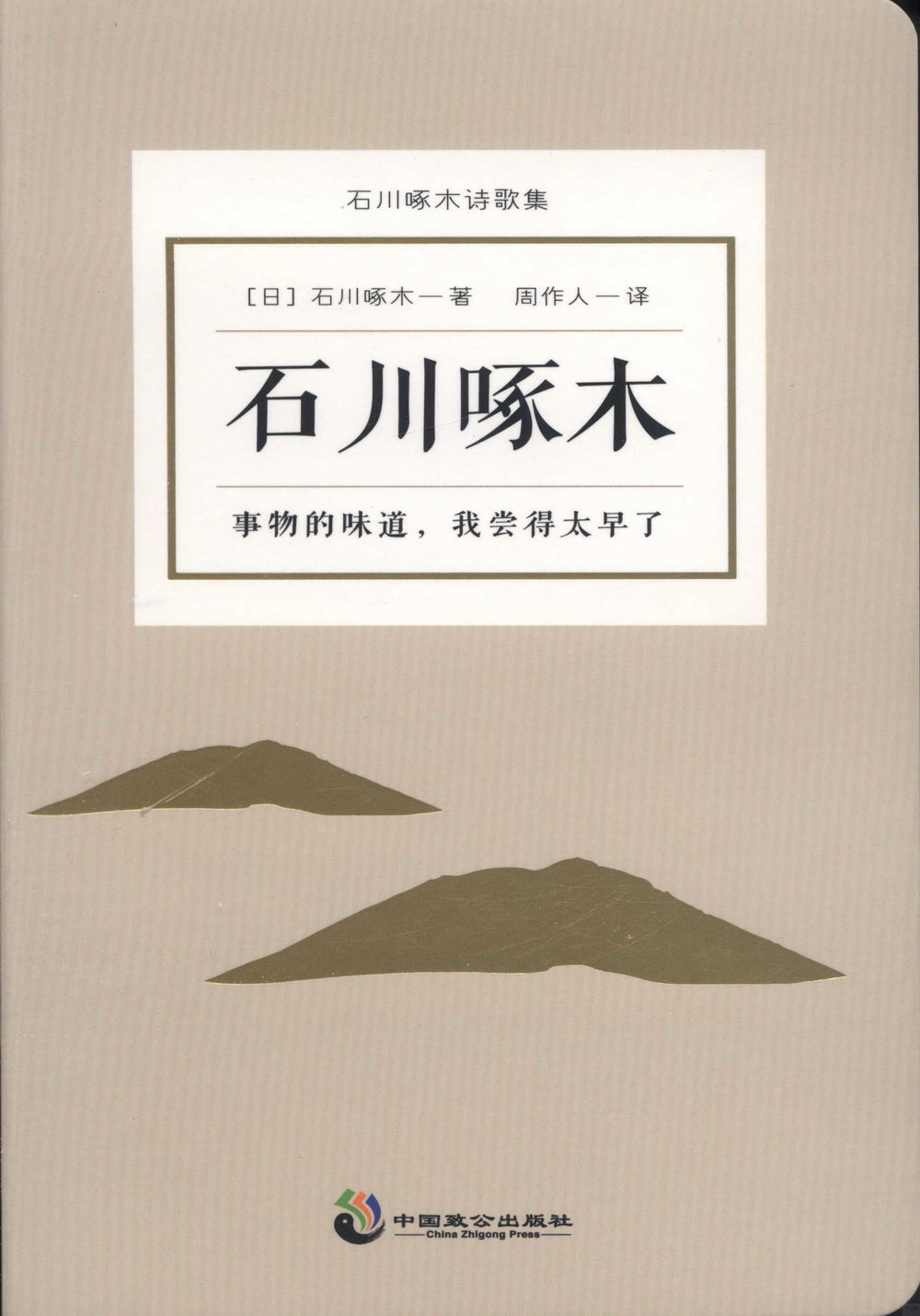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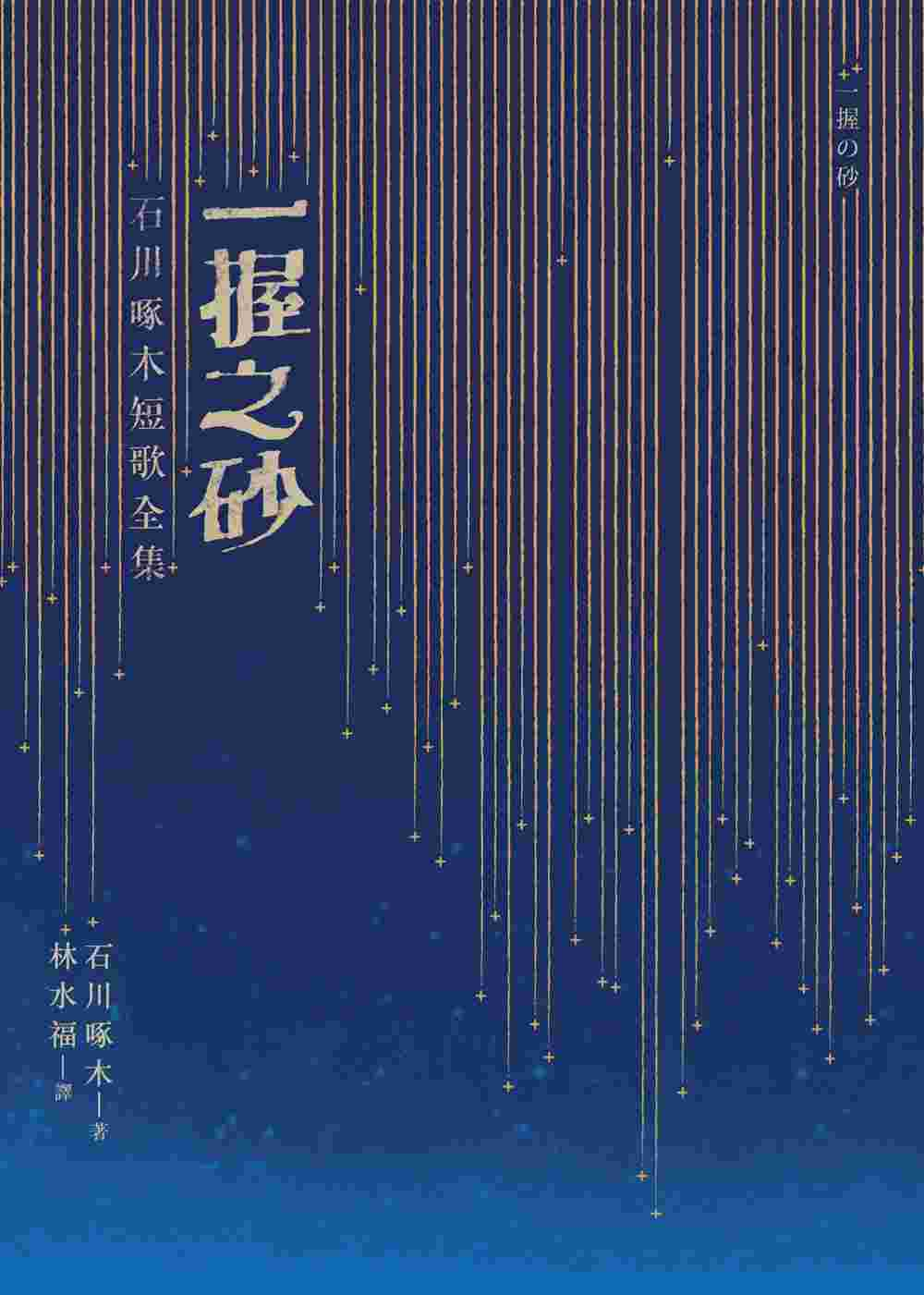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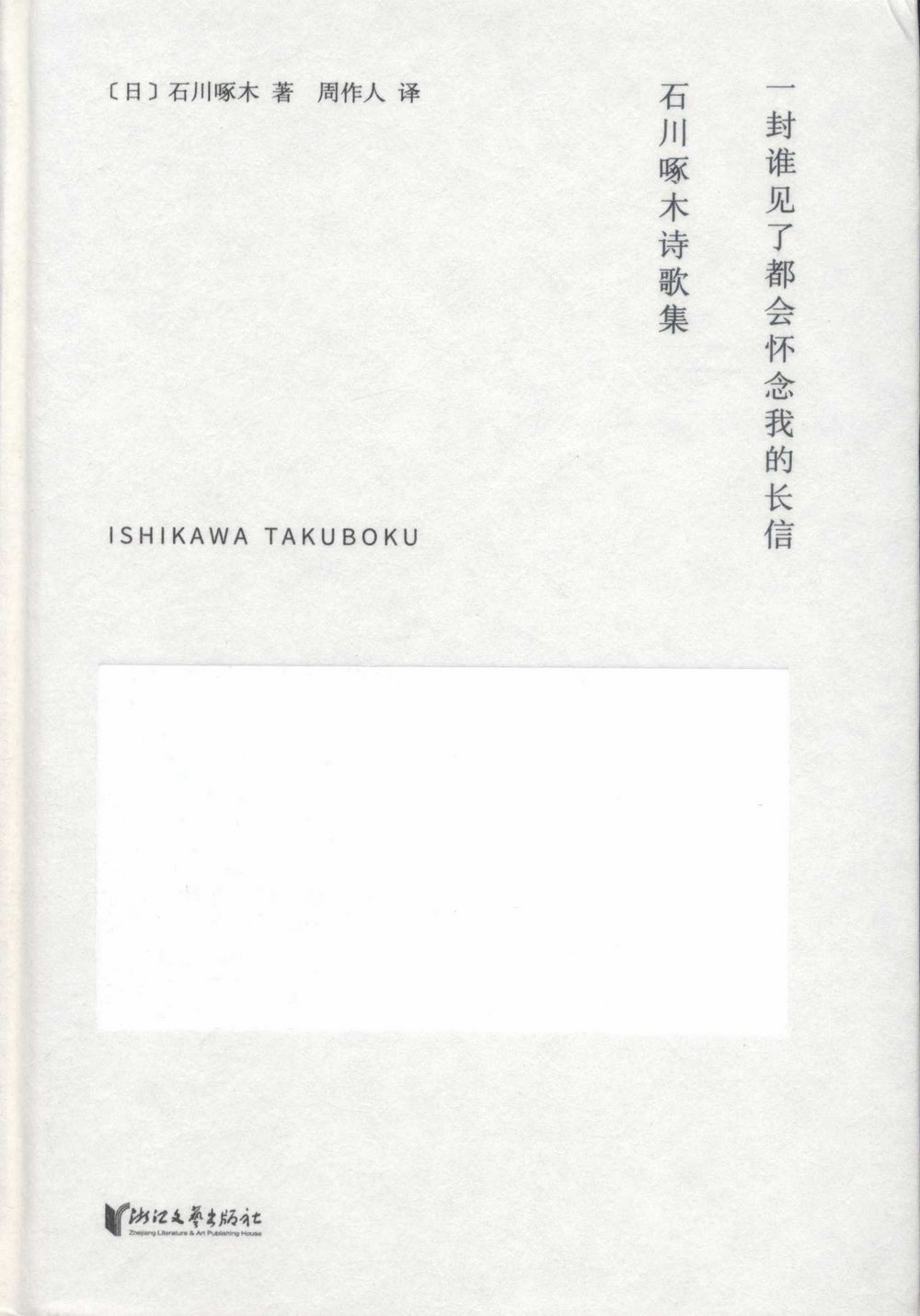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