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80、90年代台灣曾餵養女孩們過多的夢,哭死尋活的愛情戲,都像是有人在賣畫眉鳥,佈了一個局,木盒子只開一個口,畫眉鳥伸出牠的頭,露出牠額上的毛色給人鑑定,牠以為那就是全部,就是愛了,順雲為此守在沒有門的籠子裡,母女倆怨罵著對方是自己最後的真實。
80、90年代台灣曾餵養女孩們過多的夢,哭死尋活的愛情戲,都像是有人在賣畫眉鳥,佈了一個局,木盒子只開一個口,畫眉鳥伸出牠的頭,露出牠額上的毛色給人鑑定,牠以為那就是全部,就是愛了,順雲為此守在沒有門的籠子裡,母女倆怨罵著對方是自己最後的真實。
某一天下午,幾個警察到順雲住的社區,那裡山腳猜想還有舊時模糊的「新城」字樣,當時漆在那裡應該是紅豔豔的字吧,可以安身立命的。但現在也沒剩幾戶人家了,警察跟管理員說:「昨天抓到幾個闖空門的,他們說性侵了你們這裡18號的韓小姐。」隨即要往山坡上的住戶走去,管理員愣了一下衝去才說:「韓小姐已經60歲了,你們這樣問她不好吧。」
那一天跟別的日子也沒什麼不一樣,這裡的野貓都比人活躍,平常經過除非看到曬衣竿上的幾件寥落,不然你會以為這邊沒住人了,這區跟幾個早期眷村聚落一樣,人幾乎都凋零或遷走了,貓還在休憩,微雨陰天,那裡最適合這樣的天氣,到處都長了苔,好像每門每戶都可以這樣睡著了,不管以前有多熱鬧,就這樣任性地睡進時間去。
人心一長苔就搬不走了,如果你想要問韓小姐以前與她老母親為何還住在那裡。
那裡就是她的人生了,她卡在那裡的、經年攤在那裡的,比她活著的部分還要多,有些人的回憶如果任由它蔓延到生活裡,那有可能就出不去了,這對母女就是這樣,回憶沉沉的,你有時只需浸泡,再睜眼就一輩子。
關於韓順雲這人,電影裡倒是交代得剛剛好,原來在學校任職,安分守己樣,剪了一個俐落的學生頭,衣著盡量是拘謹的,但帶點夢的式樣,比方領口的花邊總在舊式開襟毛衣中,窮其所有地冒出來一朵朵來,不敢張揚。這人管著她的夢,又收得很緊,且異常珍惜著。讓人聯想著那些領結與繡花,活得像標本一樣,死氣沉沉地堅持著那點粉色,而陽台上曬著的那件白洋裝,是她要昭示給那個荒廢的社區看,她鮮活動人的海灘回憶(或憧憬),配上一個草帽就是當時美女歌手都流行的惺惺作態出走照片。
你看到那輕飄飄的洋裝,你知道她生了根,盤根結錯的,但這根長的土地是連著她病母的脈息。
因此當她出現在她任職的系主任家中,你不驚訝,猶如那系主任坐在飯桌前卻像在高台上被供奉慣了的姿態。儘管是蝴蝶被釘成標本也可以象徵戀愛的,她為他帶飯、整理衣物、為他計較營養、替他長年作帳,好像那屋子裡的暗影一樣走來走去的,安分又不過分,她在演練是這屋的妻子,一看就徒費心思了多年,在她要離去,正滿足心願般地穿上鞋,系主任一聲:「等會兒妳回家路遠,先上個廁所再走吧。」這樣彷彿就被留下的欣喜,讓她背影有幾分雀躍,鞋子又不敢脫太快。
 她在演練當這屋的妻子,一看就徒費心思了多年
她在演練當這屋的妻子,一看就徒費心思了多年
這「女孩」的夢別醒,儘管這蝴蝶標本保養得不好,翅膀都粉掉了,乾涸的夢偶爾靠男方這一句家常,乍看又飛了一下。至於韓順雲這「女孩」怎麼留在這大人身體的?她生活都不忘落下痕跡,邊走邊掉落得自己都無法察覺了,日常磨得人太累了,她飛起來的慾望跟沉下去的絕望一樣多,本人是沒有剩下多少實在的力道,心思都剩散散落落的。
看得人心碎,你知道她在消失的過程中。
片中有一席飯,她與久病的母親吃著,是她們之間少數平靜沒開戰的時刻,她母親說:「妳總覺得自己最委屈,誰叫妳是最能幹的,自己的小孩,我們都是看在眼裡的。」順雲一口飯含在嘴裡,只能硬吞下去。
她與她母親在那房子裡,跟那待改建的小區一樣,時間是凝結的,只有他們家還在訂報、還有成排的VHS錄影帶,電視機與放映機都是三十年前的機型,只要壞了就是報廢,沒有零件可以修理,老母親總坐在那椅子上聽著京戲,跟著唱著,這家的流水聲不斷,為母親洗滌、清理便溺的沖水聲。除此之外,只有她母親呼喊叫罵的聲音,順雲以碎碎的埋怨代替著回答,除此之外,那裡哪家都沒聲音,只有鄰居的小孩丟著石頭求救,但老母親都聽得到,順雲也不會聽到,她生活沒有明確的注意力,偶爾乍醒時是發現報紙沒送到,十萬火急地催報與惡狠狠借題發揮,把之前被雨淋濕的報丟給管理員,還有離職前她聽到自己要歸還的文具當初竟然沒清單可查證。「她有多守規矩」這點若沒人看到,歸還就沒意義似地又一把火地把文具拿回來。
她的神魂活在「哪裡?」,你在想,原來在那個系主任陪她等公車的站牌下,系主任叮嚀她注意身體,那一刻是永恆似的,燈光昏黃的夜裡,她的開心被她的低頭婉約偷渡著,沒留意那一句:「你最近閒了,可以看醫生。」那「閒」,是男方一直不了解她的家是某種程度的戰場與壕坑,他無心,她卻總抓著他幾句話當浮木。
她乖到沒想到自己為什麼要乖,母親提到她小時候愛吃麻花捲,她埋了很久的怨說出來:「那是姐姐愛吃,跟你拿錢,卻拿我當藉口。」為何當年不說?做了那麼多年乖小孩,就是希望人看到,結果換來後半生的六神無主。她兄姐在她母親生病後是缺席的,鮮少問候,她為母親洗澡,隻身扶著母親上舊社區山坡陡峭的階梯,但這時她的寂寞還是有個來由的,那形式上的「家」,就算整個社區都破敗了,她還有著她母親「女兒」的身分,不至於無根無著的。
順雲這人,怎麼感覺讓人好生面熟,你可能也覺得。成長在一個告訴你夢可以吃的年代,而且可以吃到飽的羅曼史年代,那時畫報上的女孩們穿洋裝,手托腮,含羞帶怯,看著愛情小說與上檔不完的愛情國片,她母親雖是跟著戲班子長大,但兩個人都沒把女孩時的夢做完,好像有誰賒欠了她們般惡狠狠。母親一有機會就跟人說她在海外發達的兒子要來接她,去看英俊醫生時會著一身喜酒裝,是每個月的大事。而女兒則在餅乾盒中拿出一張系主任給她的合影,後面寫著「讓我們看雲去(當時的流行歌名)。」對她而言如千萬斤重的承諾,後來才發現她也不算對方婚姻的第三者。
 兩個人都沒把女孩時的夢做完,好像有誰賒欠了她們般惡狠狠
兩個人都沒把女孩時的夢做完,好像有誰賒欠了她們般惡狠狠
這夢做太久,砸下來粉身碎骨的。近乎無人的社區,小偷來去自如,闖空門的人被同伴慫恿強暴了她,正好那天她穿著彷彿要去海灘的白洋裝。她石化的少女夢、依附在他人身上的存在,在她母親走後,最後一條維繫她如木偶般行動的線消失了,這個木偶才發現自己是團布絨絨做的,沒有形狀的終於攤成了各種扭曲。
當我回頭看,80、90年代台灣餵養女孩們過多的夢,哭死尋活的愛情戲,都像是有人在賣畫眉鳥,木盒子只開一個口,讓畫眉鳥伸出牠的頭,露出牠額上的毛色給人鑑定,牠以為那就是全部,就是愛了。
那麼粉紅的傷感,殘缺的都噴出血來了,這故事就這樣淡然的結束,順雲像被關的畫眉鳥無法承受看到天空,一生都在找一隅顧影自憐,形同把自己逼到了絕境。
母女二人身影漸遠,跟那個社區一樣,不冷微涼的在歲月的浸泡裡,夢被拖得像氣球軟爛在路邊,剩下塑膠色而已。女生常被一個地方給困住,情緒隨時間這水流卻怎麼卡也過不去,斑斕甚或張牙舞爪的解脫有天會從粉色中奔流而出,那是女人們的真相,只是順雲一個不留神,夢一早就吃了她。
 母女二人身影漸遠,跟那個社區一樣
母女二人身影漸遠,跟那個社區一樣
《順雲》(Cloudy)由王明台執導,獲文化部優良電影劇本、2017台北電影獎劇情長片入選、並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年屆六十未婚的韓順雲,為了照顧母親,提早從大學行政人員離職。她們的關係看似彼此依賴,又像是相互折磨,監製王小棣說:「做女兒的柔軟會一路塗抹在你看完電影回家的路上,讓你心痛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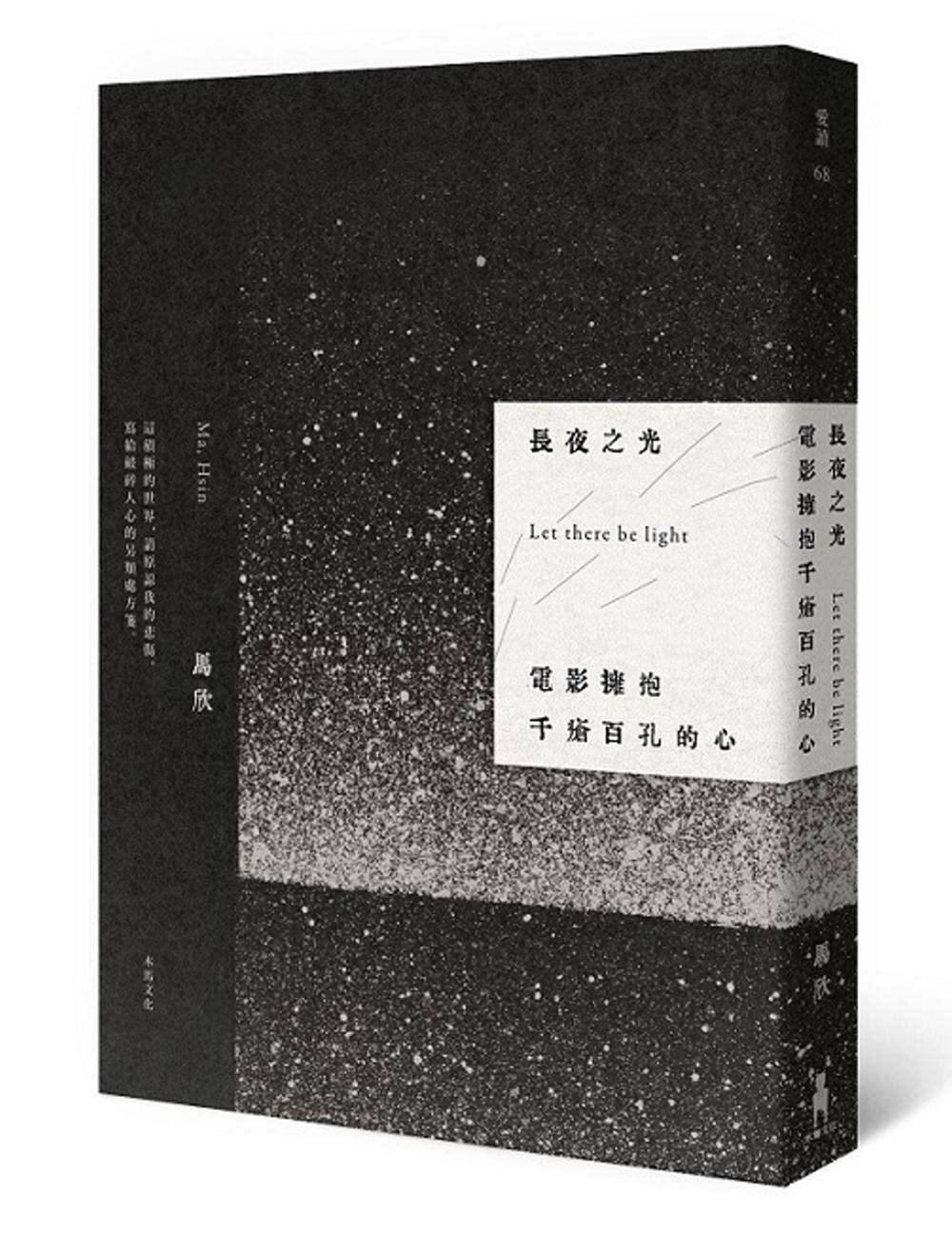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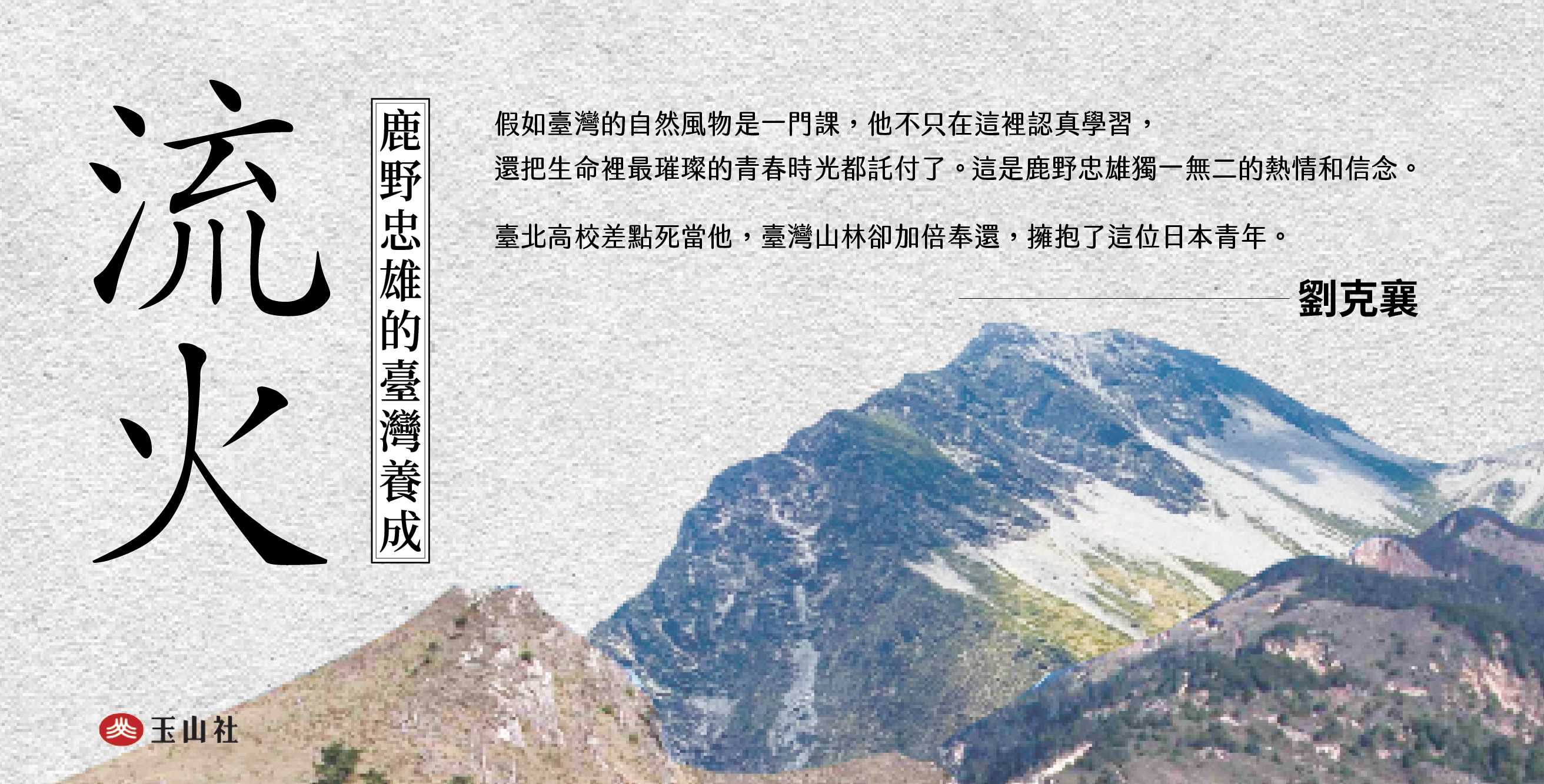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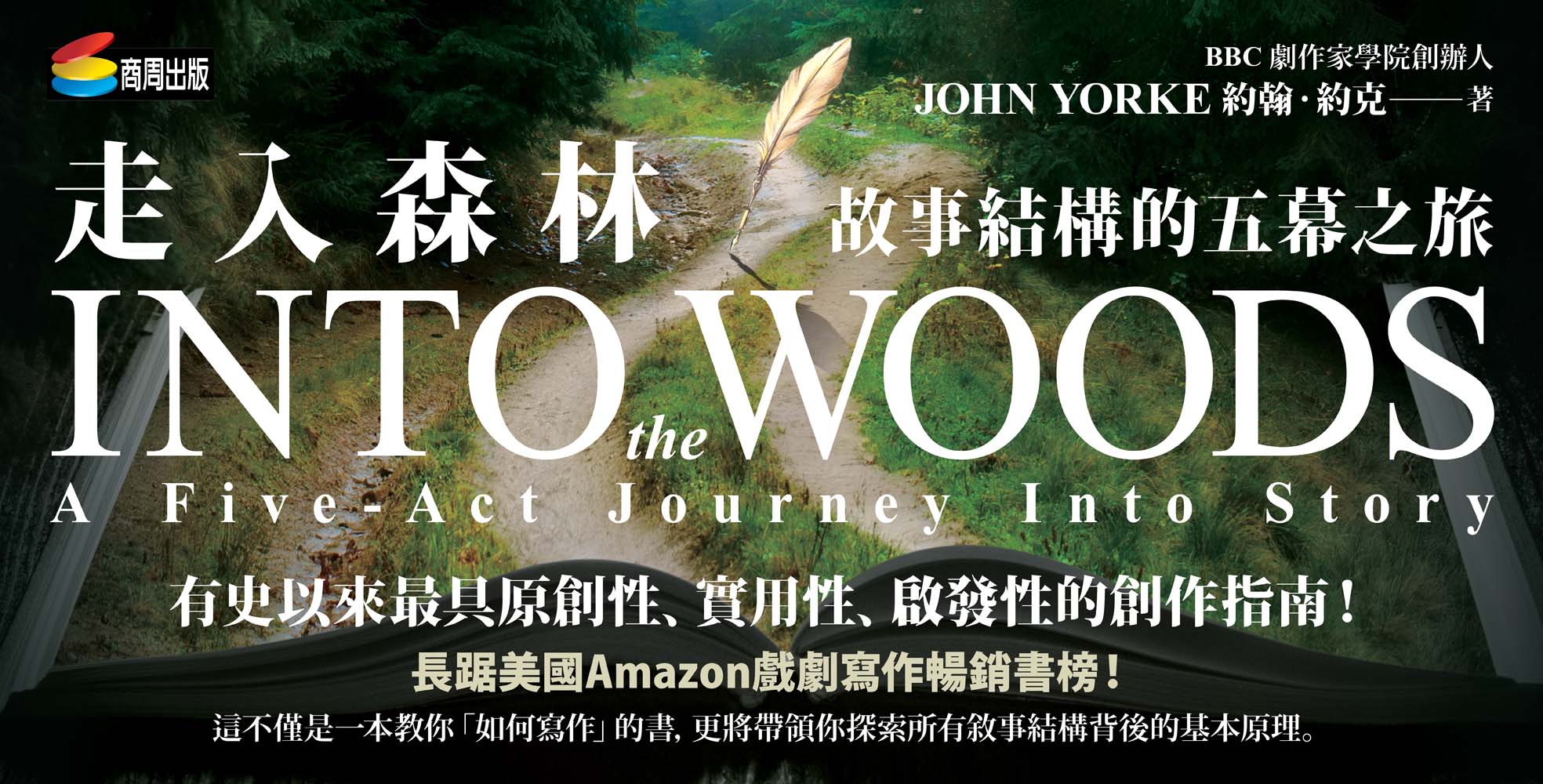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