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母虐嬰、隨機殺童、陌生人擄走小孩……這是任何育有子女的人,都曾想像過的惡夢,而《溫柔之歌》小說一開頭,就讓惡夢成真,一對如花苞般溫軟的小姊弟死了,保母在殺害他們後,給了自己一刀。下班回家驚見慘狀的母親,崩潰發狂嚎哭,徒留迴盪屋內的陰魂,與鄰居的議論紛紛。
雖以謀殺為始,但記者出身的蕾拉.司利馬尼(Leila Slimani) 興趣不在推理,她花了全書篇幅推敲的不是什麼行兇謎團,而是一齣逼真的社會寫實劇,且許多細節都真實到讓人快忘了這是一部法國小說、場景在巴黎——那個時尚與優雅之都哪,但竟然母親卡在工作與育兒之間的兩難、尋覓面試保母的過程、偶爾上演的婆媳不合,乃至公園內保母與嬰孩群聚、外傭眾鄉音喧嘩的畫面,都與台灣驚人的相似,讓遠在此端的台灣媽媽,邊讀邊點頭如搗蒜。
 蕾拉.司利馬尼以《溫柔之歌》拿下2016年法國龔固爾文學獎。(圖片來源/wiki)
蕾拉.司利馬尼以《溫柔之歌》拿下2016年法國龔固爾文學獎。(圖片來源/wiki)
關於台灣地方媽媽的育兒日常,這幾年,我們有諸多媽媽作者的分享。不論是搞笑版宅女小紅《好媽的》、文青版蘇美《文藝女青年這種病,生個孩子就好了》、暗黑版馬尼尼為《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或散文作家李欣倫《以我為器》等,都與這世代讀者共時共感,讓媽媽們感到無比療癒。
畢竟,現在已經不是當年簡媜寫《紅嬰仔》的單純時代了,新手媽焦頭爛額依舊,但我們多了網路無所不及的細碎資訊,從健康照護到教養實例,我們有團購、有共學,我們的紓壓管道也多元,自勉之餘還可發個暗黑文;我們罵罵髒話無傷大雅,也能讀到例如西方媽媽的《幹嘛要有小孩?》、《第二輪班》,從社會學角度控訴母職之過於沉重。
同樣地,司利馬尼寫下《溫柔之歌》,部分也源自為人母後的抒發,她在受訪時坦言:「我發現,從我們成為母親的那一刻起,我們從某部分來說,就永遠不再完整了。」因為時間、身體都被分割了。但自知「沒什麼興趣常常帶著孩子在廣場或公園閒晃」、視全職媽媽為畏途的她,也得面臨「既要工作,又要看顧得到孩子」這道職業婦女難題,在如此緊繃的心情下,她用小說直接切入了母親所能想到最恐怖殘暴的結局。「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解脫。」她說。
「保母」可說是母親在育兒路上,最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一個角色。她必須有宛如母親化身的特質,我們期待她愛兒如己,卻免不了教養立場衝突,何況還有一層曖昧的僱傭關係梗在我們之間,時而並肩時而相對的界線永遠畫不清。
《溫柔之歌》便細膩描述這種猶如跳恰恰的微妙平衡,從這對年輕父母決定尋找保母,好從混亂乏味的育兒生活脫身、投入剛起步的事業,到對於完美保母路易絲的讚嘆和依賴,儘管偶有隱隱的不對勁感,卻被大致平和的日子給撫過。輕快的筆調一路鋪陳,就這樣帶著讀者失速地跌進日常所不察的危險,直至保母終被自身的貧窮悲傷壓垮,發瘋地毀了這一切。
相較於母親的處境,司利馬尼的筆,毋寧更聚焦在保母身上。透過描繪路易絲,小說格局從一間家屋,擴大到都會的階層分工,雇主米麗安與路易絲各自成了所屬群體的縮影;她們在同一個客廳內促膝相伴,度假同遊,卻諷刺地分處社會階層的兩極,享有懸殊的經濟與生活條件。
當前者正處於事業與人生的爬升階段,後者付出勞力的這身臭皮囊,則承受了無止盡的幫傭勞動,婚姻破敗、沒有朋友,身心皆已乾枯。扛著丈夫逝後留下的一屁股債,和女兒離家不回的傷痛,路易絲在這城市中孤身一人,連屈身的破房子都將被房東收走。
路易絲的苦命身世是怎麼開始的?刻意或偶然,小說回溯她的過往,是從廿多歲懷孕起,孩子的生父不詳,她因此離開當時幫傭的人家,而厄運的種子就像那顆受精的卵,從此長駐她體內,吸取她的骨血,死命滋長。從她成為母親的那一刻起。
這是個令人同情的兇手,一個曾真心愛護幼兒的保母,她只是,太不幸了。不過,就算小說對讀者揭開路易絲的悲憐際遇,讓我們比在場的米麗安更理解她的處境,這仍然是個封閉的圓形劇場,我們無從插手,如同路易絲在漫長的人生並沒有遇見救贖。我們好像知道了什麼,卻什麼也不知道,如果我們是公園裡常和路易絲談話的非法移民瓦法,能做得更多嗎?我們會像那位鄰居太太,事後向警方泣訴「早知道我就如何如何」,好阻止兇案發生嗎?
痛苦是無法比較的,被殺害的血腥暴力,與生活本身就是凌遲,哪一種承受的惡意更多?司利馬尼所稱的「解脫」,會不會在於藉由寫作,脫離自身的母親劇場,想像恐怖之外的另一種恐怖?
《溫柔之歌》讓我同時想起了曾經讀過或戲謔、或酸楚、或文青感懷的,那些關於母親的日常;書中描寫公園裡的外籍保母,讓我腦海浮現每天路上見到的東南亞幫傭群像,與記錄他們故事的書籍;作者還著墨中產人士對第三世界移民的鄙笑、惡房東唯利是圖的嘴臉,雖稍嫌簡化,但也提醒了我們關於窮人、窮忙這類全球議題的思考。
小說企圖用各種線索將這場弒嬰悲劇連結到我們身處的社會大網,只是,孩子死了,是肇因於父母的疏忽嗎?是對家長推卸育兒責任的懲罰嗎?即使在21世紀現代國家,這種彷彿來自中古世紀的回音,都不會停止敲打我們的腦袋,尤其是母親的腦袋。
然而我們必須說服自己,某種程度上,把孩子交給保母,和我們每日出門在外、穿越車流,搭上一台不相識的車,吃著不知誰煮食的飯,不都同樣是「把命交給陌生人」。為了維持世界運作的和平,我們都得信任彼此。兇殺案猛地刺穿了日常和平下的脆弱,那無法被文明收束的瘋狂與惡,但這不只是單一兇手、某個陌生人所能承擔。對彼此來說,我們不也都是時時握著對方性命的陌生人?
書中,司利馬尼藉米麗安之口說:「只有當彼此不再互相需要,當我們可以過自己的人生,過一個與他人無干、完全屬於自己的人生,而讓我們因此獲得自由時,我們才會擁有真正的幸福。」我想,這是屬於她的解脫之道。當我們不只是母親,我們才是個完整的人,學會完整地對待他人。即使是擦身而過的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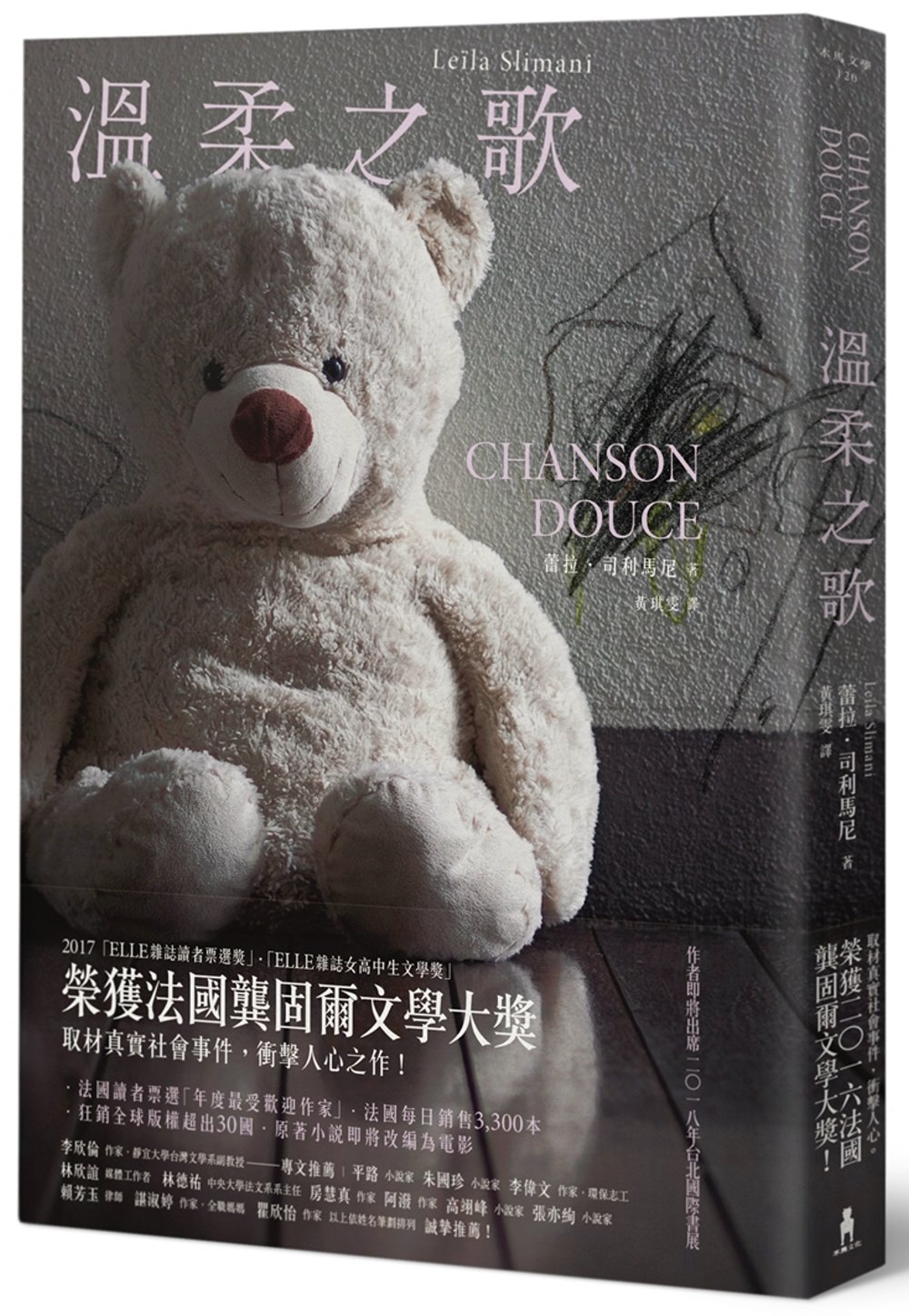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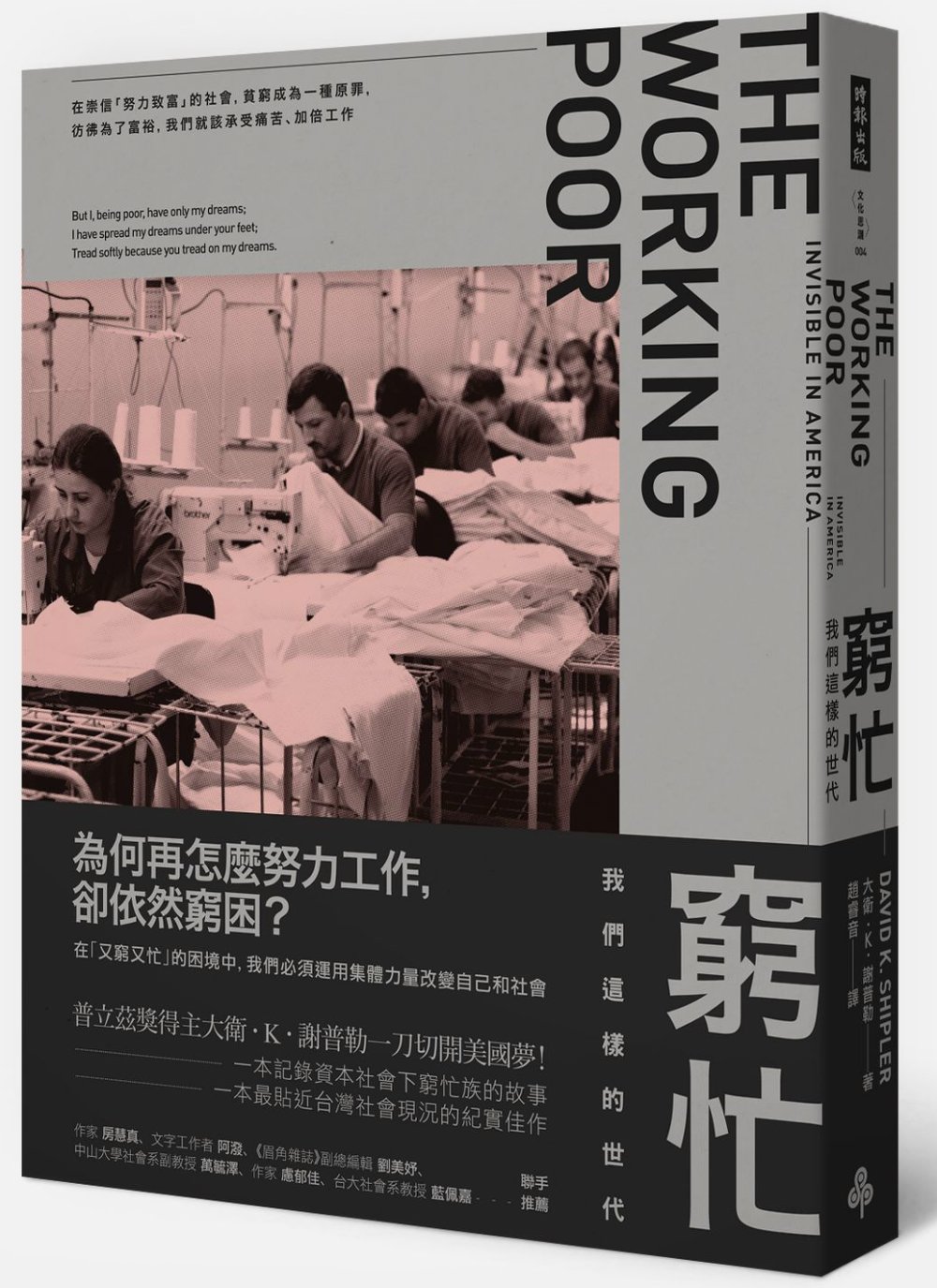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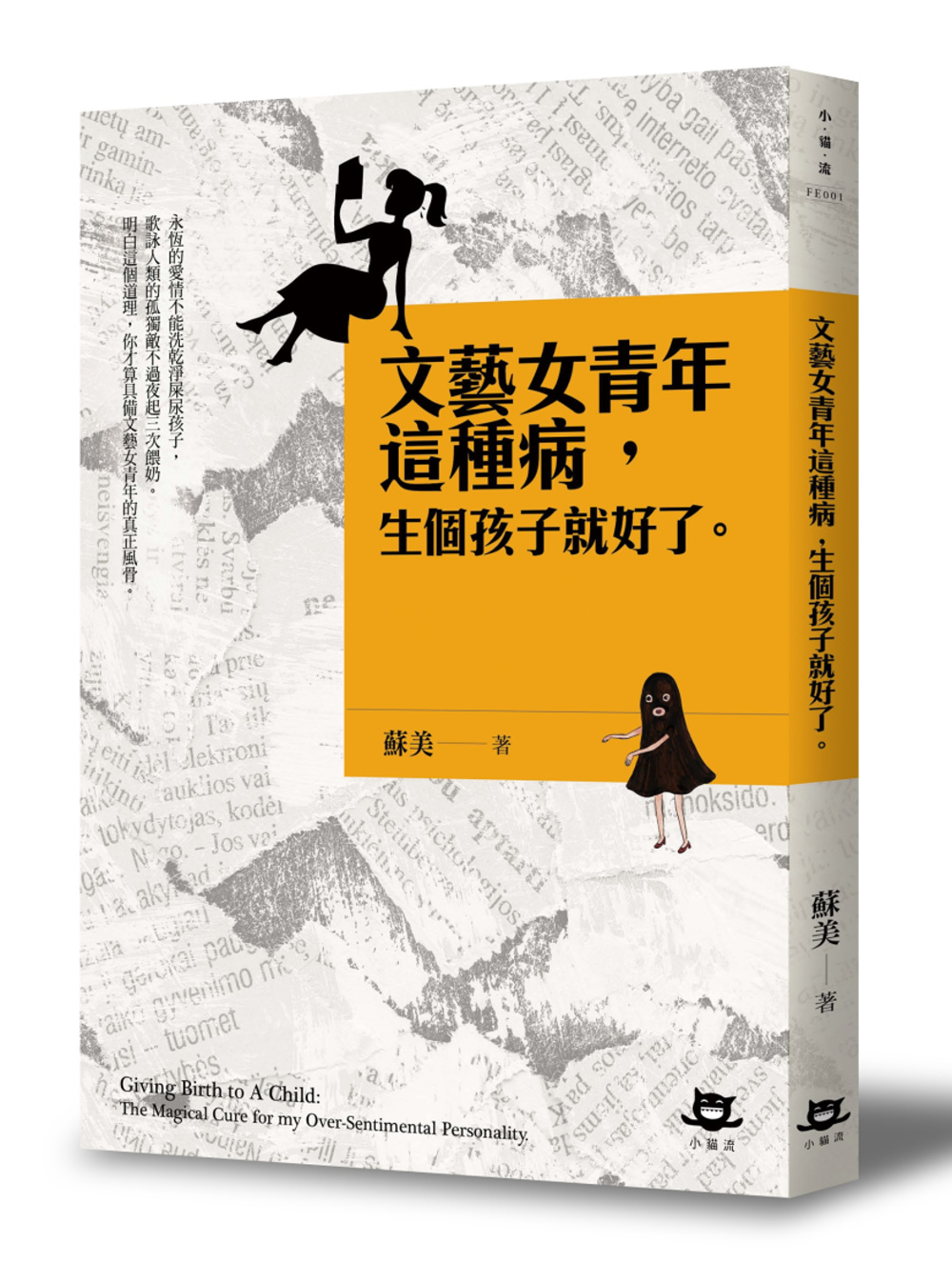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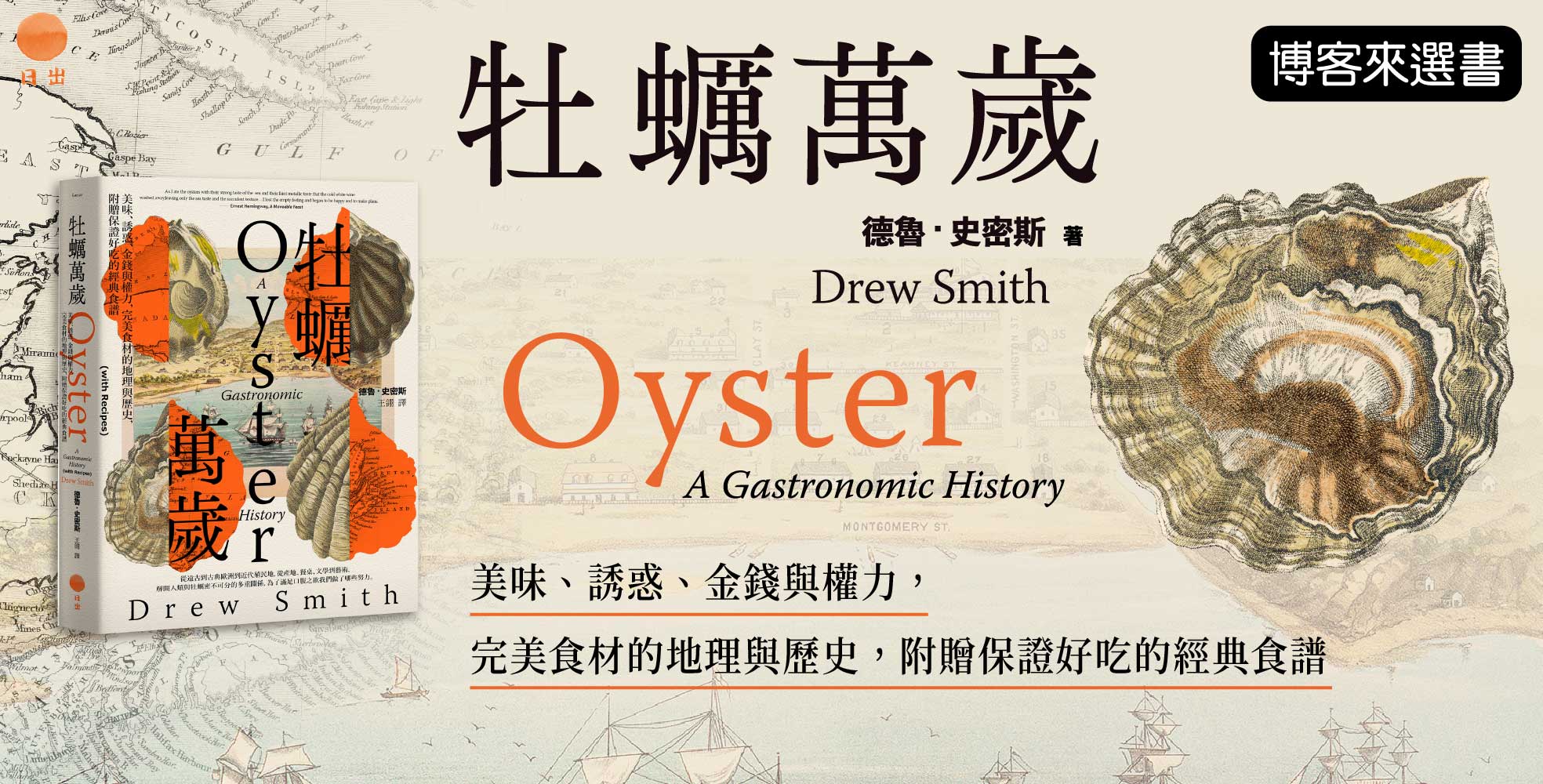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