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直到日昇之地
「生命很短暫,」中年人吃完手中的檸檬冰淇淋,緩緩地說。這是一句再簡單不過的話,我卻像被電到一樣震撼不已。

離開城市,騎在路上,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圖/張子午)
吃過晚飯正準備回旅館路上,一句「哈囉」冷不防從暗處冒出來,隨即面對我伸出一隻手。在伊朗兩個星期,除了人煙稀少的荒涼公路上,人們會請我喝茶吃東西,在城裡就鮮少遇見主動的好客熱情,而這在土耳其是屢見不鮮,相較之下,伊朗人頗為內斂,甚至謹慎,但並不代表他們吝於給予旅人照應或關切,只是不會一下子排山倒海的無保留傾瀉出。
如果說每來到一個新的國家都像從頭經歷一個人一生,重新接收一次循環,時間、季節、溫度、語言、味道,甚至最微小的塵埃,從空中起始,飄落,盤旋,到底,就結束了。
我有些驚喜的伸出手與他相握。「下午我在哈菲茲的墓園外看見你,就想與你打招呼。」哈菲茲(Hafez)是古波斯最偉大的詩人,至今仍受到每個伊朗人的尊崇,家家戶戶都有一本他的詩集,人人能引述一段他的詩句。他在設拉子這座城市的陵墓,幾乎已成為朝聖之地。
我未讀過他的詩作,但在金黃的夕陽餘暉底下,看著老老少少漫步,三三兩兩在花園周遭席地而坐,讀著、討論著腳邊攤開的詩集,或靜靜走上花園中央的陵墓,用發光的眼神諦聽四周傳來的空靈音樂與吟誦,雖然只是音響傳出的聲音,但我也不知不覺被當下的氛圍感染,心中像有一條平靜的河流過,洗去自然環境的乾枯與城市的喧囂。

懊熱午後,男人在清真寺門口睡覺(圖/張子午)
「但當時我坐在車上來不及停下來叫你,來,請你吃冰!」繞過市中心厚實的城堡外牆,他領我到一家生意興隆的店門口,買了兩杯檸檬冰淇淋,「我們這裡最有名的!」他不無自豪的強調著。人手一杯,我們就在無星夜空下,坐在草地上吃冰、閒聊。
三個星期之前還在喬治亞,然而一到伊朗,馬上就像回到火爐,只有在這口含細緻碎冰的短暫片刻,才能稍稍化解體內不停噴發的火山。但隨著杯底漸空,我明白今晚仍逃不過回到旅館房間被炙燒的命運。
「生命很短暫,」已記不得當晚他重複了多少次,但這幾乎是每句話的發語詞。「我們的古詩人奧瑪開儼(Omar Khayyam)說過,生命就像一盤棋,每一步都操在看不見的手上,身不由己,你不知道下一步會到哪裡。」
眼看乾坤一局棋,
滿枰黑白子離離。
鏗然一子成何劫,
惟有蒼蒼妙手知。
他的故鄉靠近伊拉克邊境,兩伊戰爭期間被戰火波及,他當時受傷住進醫院,之後舉家便遷居設拉子。
「每個宗教都說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真理,然後用這個真理控制人。我一點也不相信伊斯蘭教,也不相信現在的伊朗政府,它說它是世上獨一無二的伊斯蘭共和國,這是完全錯誤的,沒有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都是人類的一份子。蘇格拉底不是說過:『我既非雅典人,也不是希臘人,我是世界公民。』」
我來到伊朗的這一年,六月,只不過兩個多月前,爆發該國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動亂。總統大選結束後,改革派支持者認定當權的保守派舞弊、操縱選舉,發起大規模抗議行動,一舉點燃許許多多人長期渴望民主的熱血與不滿保守政教階層長期把持國家的怒吼。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與國際新聞,當時的動亂引起舉世震撼,似乎每個人都屏息以待,等著看長期與西方諸國作對的伊朗,會發生什麼天翻地覆的改變。
經過流血與逮捕,改革的希望依舊被鐵腕碾碎。當我走在街上,除了零星被撕裂的印有改革派候選人的海報,一切如常,人們工作與生活的腳步、毒辣的太陽、像是漂浮著沙粒的空氣。

伊斯法罕(Esfahan)的大清真寺(圖/張子午)
「那些人(當權者)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抗議者)被抓、被關,很慘。」吃完最後一湯匙的冰,除了這句話,他並不想多談才剛結束的動亂。
「我相信什麼,我相信人的良善,我相信幫助別人便是幫助自己。」
「這世界上的書本、知識,太多太多了,窮究一生,根本不可能讀完。所以其實不想什麼的人是很好的,沒有太多煩惱,只要汲汲營營眼前的利益……」
「我們能知道的太有限,而生命太短暫。」我感到他的字字句句都像是替我而說的。
「對,我了解,就像睡了一場覺,一覺醒來,你發現這趟人生旅程已經抵達終點。」聽到我回他這句話,他有點憂鬱的臉龐展開笑顏,在設拉子的夜空底下,我們再次握手。
〔延伸閱讀〕
《魯拜集》是12世紀波斯詩人奧瑪開儼的傳世之作,後經英國詩人翻譯而為世人所知。中文有多種譯本,其中以黃克孫先生七言絕句的版本公認最經典,文中所引詩句即為其譯筆。
張子午
生於台北。在力有所逮時,希望以自己的身心,紀錄下世界的真實與差異。2007年獨自以自行車橫貫歐亞大陸,從中國出發,一路向西,抵達陸地的盡頭葡萄牙。2009年帶著同一台自行車穿越中東,旅程結束於埃及開羅。
曾獲第三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四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評審團特別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補助、行政院客委會98年度築夢計畫。 著有《直到路的盡頭》,同名部落格不定時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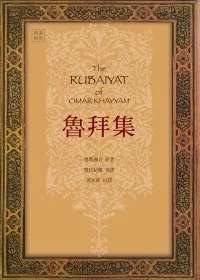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