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抵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空氣中浮盪著乾淨清寂的氣息,似乎剛下過雨,涼風撫過臉龐,我望著寬闊街道兩旁的高大建築,華麗的浮雕與柱頭在早晨的光線中閃亮,一棟接一棟,如同巨型的石碑巍峨佇立,俯瞰著人行道上稀疏的人影。人們臉上表情不多,形單影隻的走著,沒有對我投以過多好奇的目光。
這是徹底不同的世界了,這種感覺,就跟我過去的旅程中從中國進到中亞,從土耳其進到歐洲一樣,熱絡擁擠的(東方)生活感被冷靜的(西方)距離所取代,當然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全然非此即彼,而是擺盪在光譜兩極,有著程度上的差異。這第一眼的街景,混合著對歐洲、俄羅斯、哈薩克的記憶,使我從已成為某種「習慣」的土耳其經驗中醒來。

巷弄裡的典雅房舍大多飽經風霜,猶如遲暮美人。(圖/張子午)
小巷子裡,巨大而堂皇的整齊建築忽然變得可愛許多。木頭與石磚交錯著淡雅色澤,雜物與晾曬的衣服隨意伸展在陽台外,剝落的色彩與磨損的牆面處處是精緻細節,透出和煦的溫度,像是一個年華老去、飽經風霜的美人,在殘破建築與凋敝巷弄間,似乎仍可想像她最美麗的時光。而她也就任由無情的時間留下痕跡,沒有想要再次妝點容貌。
等到離開首都,那第一眼的驚艷,迅速銹蝕蒙塵。一座座城鎮荒疏破敗,了無生氣,除了古老神聖的大教堂,永遠修護得最完善。我去過荒廢在土耳其東北山林間的喬治亞東正教教堂,再來到那些廢墟遺跡的「故土」,從那相似骨架裡,豐厚血肉終於完滿的長出來。在周遭異教徒的強勢威脅下,國家的宗教殿堂被以最高規格持守著。燦爛壁畫繪著一排排帝王將相、聖子聖徒,周身華麗織錦,教堂內外氣勢雄混,精細而對稱的浮雕宛如光線外緣藏不住的鋒芒,耀眼懾人。幾道光束透過細長的窗格灑進教堂,人影一如光線般的凝定、透明,包著頭巾的虔誠婦女親吻聖像、跪地拜伏,結髮蓄鬚的教士低喃經文、新婚夫妻手執蠟燭立於燭祭壇屏風前,甚至是首都裡落魄潦倒的乞者,來到教堂門廊邊,躺在被無數信眾磨得光滑圓潤的石磚上,都顯出較多的尊嚴。

喬治亞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基督宗教國家(第一是位在它南邊的亞美尼亞),據首都二十公里的Mtskheta的大教堂是全國最重要之一。(圖/張子午)
回到蕭條的街頭,則又是另一回事。街道人影疏落,歌劇院、博物館、市政廳等公共建築門前冷清寥落,雜草從石縫裡鑽出,騎在馬上的國王雕像迎向積雲深重的日暮,冰涼的空氣穿行在馬路與河邊,完全感受不到現在正是八月溽暑。走回民宿的路上,兩旁的宅院花園寬闊,卻荒疏凋敝、缺乏修葺,入夜前的最後一絲光線照著滿溢出來的植物,枝幹、葉片、花朵旺盛而張揚的蔓生出枝葉,巨大的對比下,屋宇遺落在時間殘骸堆裡,無人聞問般的靜止、風化。很難想像如今已無緣見得的活力,曾使造訪過這個國度的旅者不禁讚嘆,「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著有《憤怒的葡萄》的知名美國作家史坦貝克,曾經寫道:「從沒到過的人和一輩子不可能去的人,提到喬治亞時莫不帶著思慕和敬佩的口吻。在他們口中,喬治亞人是超人、大酒客、出色的舞者、卓越的音樂家、傑出的工人和情人。」
「絕大多數的俄國人都希望,在世時守分為善,死後往生喬治亞,不要上天堂。這是一個氣候怡人、土壤肥沃、本身有個內海的國度。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人,犒賞他到喬治亞一遊,久病不癒的人到這兒休養生息……」

教堂內壁畫除了聖經故事,就是歷代統治者的身影。(圖/張子午)
對這個國家過往的歷史再怎麼陌生,都大概會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俄羅斯與喬治亞發生了一場戰爭,雖然很快就結束,卻令陶醉在慶典氛圍裡的世人著實嚇一大跳。種種複雜的歷史種族糾葛外人看不怎麼分明,就像大家族裡的內鬨,這場戰爭戲碼被視為親西方的喬治亞與過往的老大哥間的爭執,前者想離開關係密切的傳統大家族,後者則無法容忍小老弟投奔敵營,是故關起門來好好教訓一頓。世人震驚於俄羅斯軍隊勢如破竹的攻勢,輕而易舉就兵臨城下,隨時能將這個小國吞下。沒有別的選擇,小老弟只能灰頭土臉投降。
青山綠水依舊在,只是樂園已失落。
〔延伸閱讀〕
《史坦貝克俄羅斯紀行》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冷戰時期之前,美國作家史坦貝克與傳奇的報導攝影師卡帕(Robert Capa)連袂造訪廣大的俄羅斯、烏克蘭及喬治亞,不論文字或影像,都留下生動非凡的記錄。
張子午
生於台北。在力有所逮時,希望以自己的身心,紀錄下世界的真實與差異。2007年獨自以自行車橫貫歐亞大陸,從中國出發,一路向西,抵達陸地的盡頭葡萄牙。2009年帶著同一台自行車穿越中東,旅程結束於埃及開羅。
曾獲第三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四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評審團特別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補助、行政院客委會98年度築夢計畫。 著有《直到路的盡頭》,同名部落格不定時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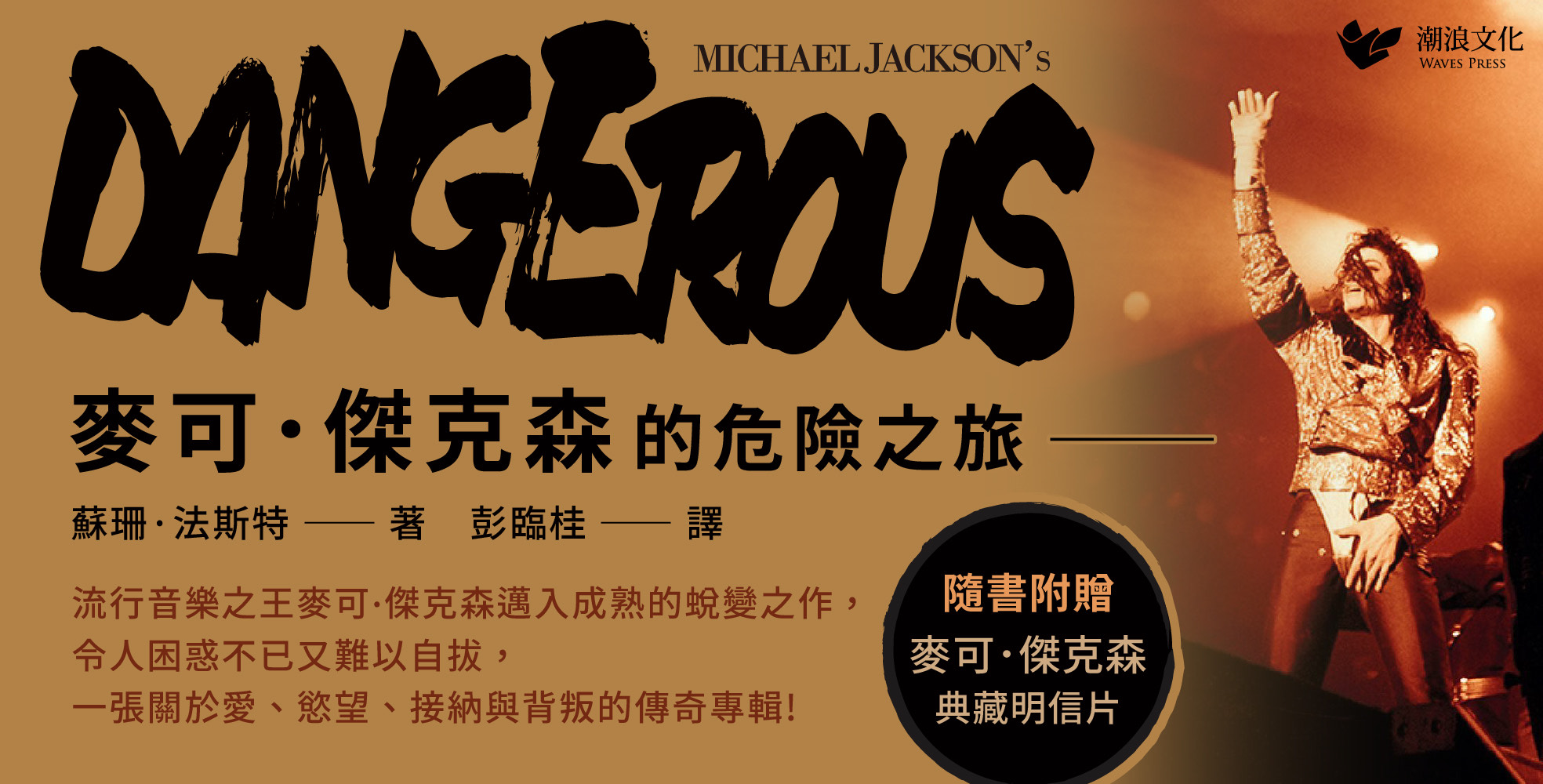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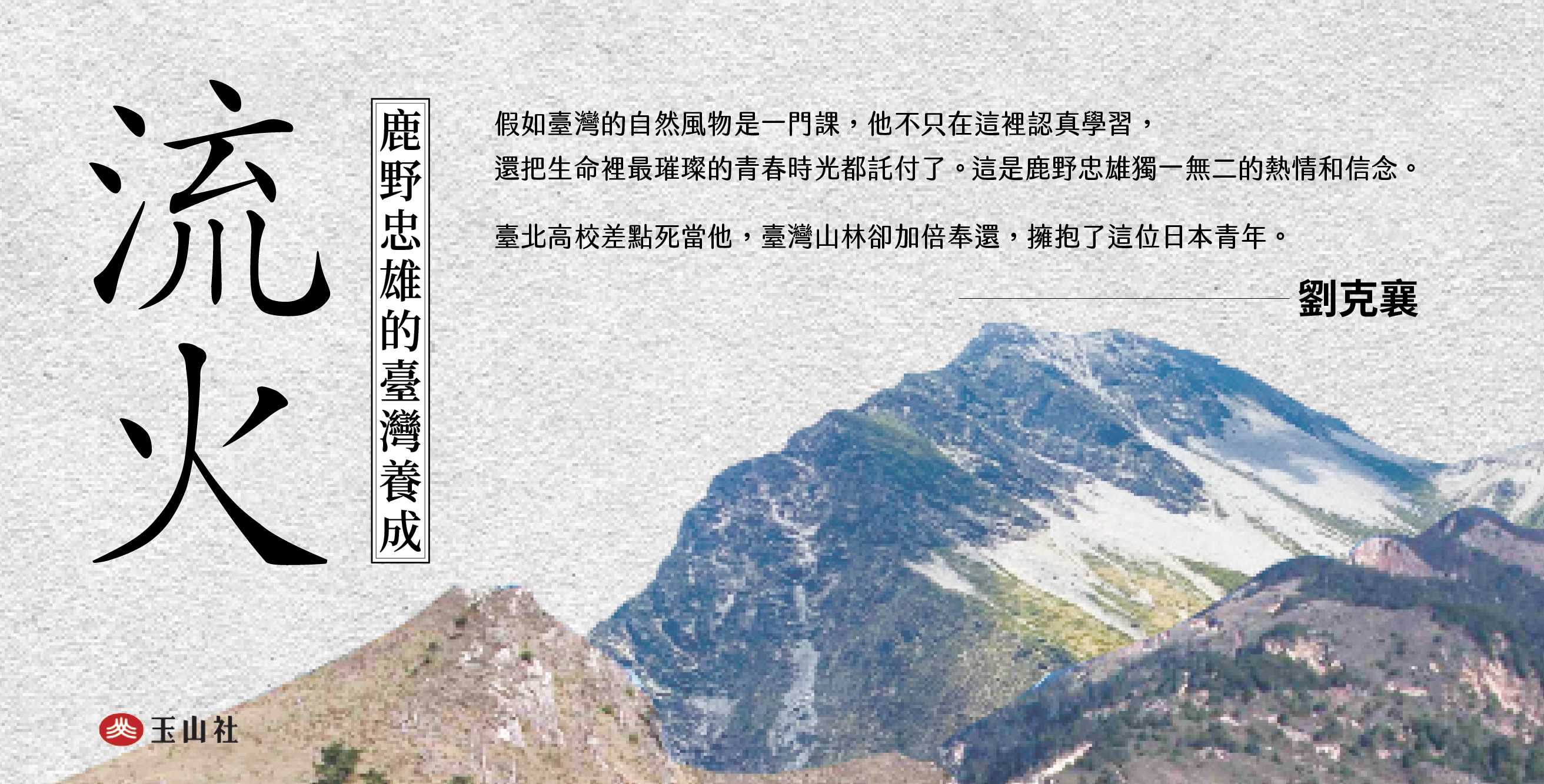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