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光倒轉四個月,3月24日凌晨兩點,許多人沉沉睡著時,黃孫權正和三名學生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著,趕著前往行政院,支援占領行政院、面臨被警察暴力驅離的群眾,學生開車,他就著電腦螢幕發出來的慘白光線,開始敲著鍵盤,輸入:「我持有對現實的欲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實現!」
那時候,許多沉睡的台灣人還不知道鎮暴警察、警棍警盾、水車會成為接下來一個月台北街頭的常見風景,但黃孫權對警察暴力毫不意外,反倒驚訝台灣社會未預期警察暴力的心理,「2005年我們在香港反WTO部長級會議時,警察把催淚彈丟到民眾身旁,或是直接朝著你的眼睛噴胡椒噴霧。」他說,「占領行政院後,許多人一直強調警察暴力,但警察本來就是暴力的,反而模糊了抗爭主要目的。」
黃孫權的擔憂延續至學運結束後,許多人把「割闌尾」掛在嘴上,卻不再談服貿,「原本是一股綜合了民生經濟的力量,遍地開花後只剩下政治力量,有點可惜。」他以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為例,參與者分成兩派,一派走入政治,欲靠政治權力改變社會,另一派走入社區大學、NGO、媒體,以推翻社會結構為目標,不對政治人物有過多期待,「如果經濟、社會結構不改變,誰執政都是資本家的代言人。」
那日凌晨,他在車上寫出〈除非我們尋找美麗〉這篇文章,寫著:「不要將學潮與公民行動當成是病徵的反應而已……,應該是要創造,創造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制度安排詭計之機會,創造堅決反對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創造台灣的發展乃在確保國土而非僅只是國界上的防線,創造市民更關心都更條例、農地再生條例、稅制不公、醫療教育文化住宅私有化危機等等的契機。」這篇文章後來也成了《除非我們尋找美麗》一書的首篇,提醒著在無能改變現實之前,先與之搏鬥的重要。
「我反自由貿易協定,但不可能反自由貿易,重點不是參加ECFA或TPP,美國主導或中國主導沒有差異,重點在於政府如何確保公共利益的存在,避免水、電、能源、電信業、大學太快法人化,一切改以營利為導向。台灣的公共事業常被認為是國民黨的事業,其實公共事業是國產、公共財,要有保護措施,來守住公共利益。」黃孫權說。
例如,法國有文化保護措施,電影市場只有四成是好萊塢電影,全歐洲最低,台灣卻幾乎全面開放;法國的都市更新規劃區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公共設施和機構、綠地面積,或是藉由設計修補改善空間,取代毀滅性的重新建設,讓居民不必舉家遷居,台灣政府則授權給私人土地開發商建設,不管都市紋理和歷史,只是鏟除原建築、盡其所能蓋更高的樓層。
政府要求國民接受自由貿易、迎接自由貿易協定,卻毫無公共利益防禦機制,黃孫權認為,這次的318學運創造一個新的機會,讓部分民眾重新審視公共事業概念,就像台灣文創產業「出租空間」的問題,獨具風味的歷史街區開起一間間文青咖啡店,拆毀眷村後舉辦眷村文化節,文創園區成為展覽空間兜售,「例如松菸,政府將全民資產交給一個公司,民眾獲得什麼利益?該公司又創造了什麼新的產業?」
他提起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亞維儂是一座小城市,除了幾個設備較佳的表演場所,其餘無論是教堂、修道院、咖啡廳、校園或街頭、廣場,都有戲劇、音樂、舞蹈、展覽或研討會在進行,相較之下,今年邁入第16屆的台北藝術節,始終沒有創造出更多可用空間,在泡沫式的活動結束後,劇團依舊缺乏便宜的排演場地,如同台灣獨立樂團沒有足夠練團室的困境。
或是日前誠品被批評下架西藏人權書籍、限制員工言論自由,黃孫權也直言,「誠品本來就是個商場,為什麼我們要對商場失望,卻不討論台灣圖書館功能不足,陳設弄得像K書中心,卻忘了讓愛書人討論讀書、討論書、諮詢書的核心功能?」

真正重要的議題想被仔細思考辯證,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下幾乎不可能了,許多煩悶紛擾都在大黃鴨前消失了,有人歡樂喬角度合照打卡,有人批評巨大PVC製造污染,有人罵作秀,有人推出更多山寨版加入作秀。大黃鴨的喜愛者與批評者的對抗如此輕微又不傷感情,成功置換了人們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與衝突,黃孫權說,「台灣這幾年愈來愈往內看,無法想像其他可能,服貿、公平貿易、有機農業的議題,只要表現某種程度的關心就可以,真實生活就不必考慮那麼多了。」
《破報》停刊了,這份誕生在野百合運動後,象徵反抗、非主流之聲的媒體結束於太陽花學運前,從創立至停刊皆擔任總編輯的黃孫權,這段時間努力與世新董事會溝通,讓《破報》20年來資源上網公共化,直至採訪當日仍未果。
今年4月22日,林義雄為反核四禁食,過往無役不與的《破報》,再也沒有版面可寫,在最後一次的編輯會議裡,團隊決定一起剃光頭聲援,「我們就像關廠工人,只能利用身體吸引大眾注意,但我們又沒有guts去臥軌堵捷運,只能貢獻一顆頭。」
「只是我二十多年來沒看過自己的頭型,反而有點不認識自己了。」黃孫權笑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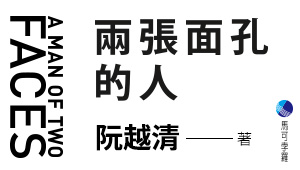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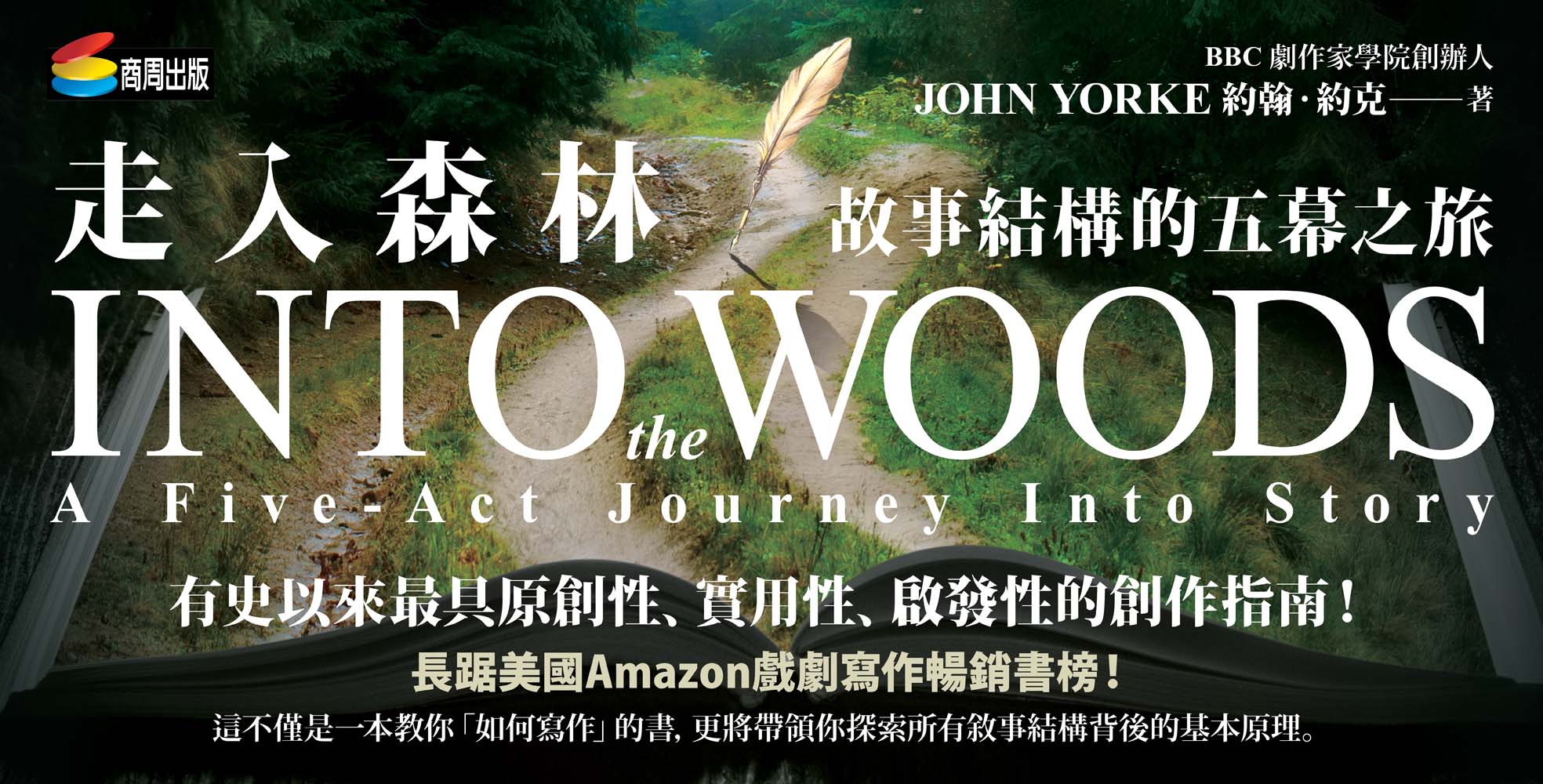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