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穴居動物的眼睛,總是離群,時而銳利得讓人無法逼視。
房慧真任職媒體已兩年半,名片張牙舞爪,本人溫良敦厚,至今前往採訪的時候,仍常被說不像記者。在記者與寫作者之間,彷彿有一層堅實的細胞壁,足以抵抗看不見的滲透。首本散文名為《單向街》,行到《小塵埃》需時五年,塵埃落定之後,開展出一片水域,那是新作《河流》。書的編排分為下游、中游、上游三輯,從一開始,就暗示了一場溯流而上的旅程。這個世界更新得太快,很多事物都被遺忘,必須找出邊緣,才能撿拾回那些失落的。
「我很喜歡去靠近河邊的國宅。台北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明明是靠水的城市,卻築起堤防,產生一種內陸的感覺。堤防圍起來的好像不只是河,而是隔絕對岸的三重、板橋,甚至中南部。」房慧真說,「可能我想尋找,邊界是怎麼回事吧。」她從城市中心一路走到堤防,抵達堤防之後,還有堤外,堤外仍有沙洲,仍有浮島,城市的邊緣,是邊緣與邊緣的總和。
她一直住在台北城南,幾乎沒有租屋經驗,更沒有住過對岸的三重或板橋。如果只看外在條件,就是個典型台北人,不會騎車、不會開車,甚至不會游泳,走路是她最擅長的移動方式。「我的經歷是很匱乏的,只能以大量的走路,來看別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她常常半夜走路,身上幾乎不帶東西,「我有時候可以走七、八個小時,一直走路,走到不能走為止。」以前是走市中心的道路或小巷,後來喜歡沿著河走。「《單向街》本來是走一個街道,這本《河流》則是純粹的觀察,更外圍、更邊緣,探討邊界的感覺。」
以前水邊的國宅是比較老舊的,不像現在建商推的景觀豪宅,房慧真描述,「走到社子島或關渡一帶,就會看到有人在種田。我沒有鄉愁,沒有鄉下可以回去,看到那種景觀就會覺得很特別。也許是我一直在尋找台北的鄉下。」壓縮了她的十年走路與許多其他而成的這本《河流》,更像是沉積岩,經過歲月的堆積與侵蝕,獨留最後的秘密結晶。
「可能我不是一個太引人矚目的人,看起來沒有攻擊性。」房慧真有一種像是隱身術特質,讓她穿行過那些小巷小弄、近距離窺看他人之生活,如入無人之境,例如南機場國宅,或是台灣早期的國宅聚落,因為每戶坪數極小,住戶會將瓦斯爐、洗衣機等家庭物件擺在走廊,「我很喜歡走去那裡面,中午去他們就在炒菜,有一種半隱秘半公開的感覺,是種流動的生活。不像自己的生活,是隱蔽的,東西收好的,不跟人交流的。我自己出門如果遇到婆婆媽媽在聊天,我會低頭快步走過。」走路的時候,觀察的時候,房慧真成為另外一個人,她是隱形的,卻也是融入的;她不在那些人之中,卻也不是外人。漫長的,緩慢的,那些無人知曉的時刻,她總是看著,長鏡頭一般,溫柔獨特的凝視。
對於底層與邊緣的關懷,或許來自身為印尼華僑的父親,因父親懷抱著強烈的不安感,最終成為獨斷的暗影,將小家庭與親戚鄰居之間的聯繫切斷。「《河流》裡我有去拍一座浮島,地點在台北往三重的橋下。就是一個島,沒有接上任何陸地,像是我身世的隱喻一樣。」而另一種可能是,從國中到高中,房慧真放學不直接回家,總在街上晃,那六年讓她與街道產生一種情感,「當時的確會想,有一天我受不了真的要離家出走,那我如何在都市叢林中生活。」如果可以選擇,她想住在浮島,可以隨時靠近她感興趣的人群,保持忽遠忽近的安全距離;位在城市周圍,卻不屬於任何城市,
《河流》是記錄走路十年的壓縮檔,要再有這樣的作品,需要繼續積累十年,房慧真說,「寫字好艱難,那些東西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這本好像是盡頭了。」當自身的散文書寫形成一種文體之後,她還想嘗試文體的轉換,小說成為一個令人驚喜的選項,「在小說的世界裡我是一個生手,可以不怕犯錯。」從《單向街》一路走來,房慧真走得愈來愈遠,也從敘事者的身分,漫漫逸出到鏡頭外。儘管如此,鏡頭之後,那個持攝影機的人,仍舊投射出堅定的目光。
〔房慧真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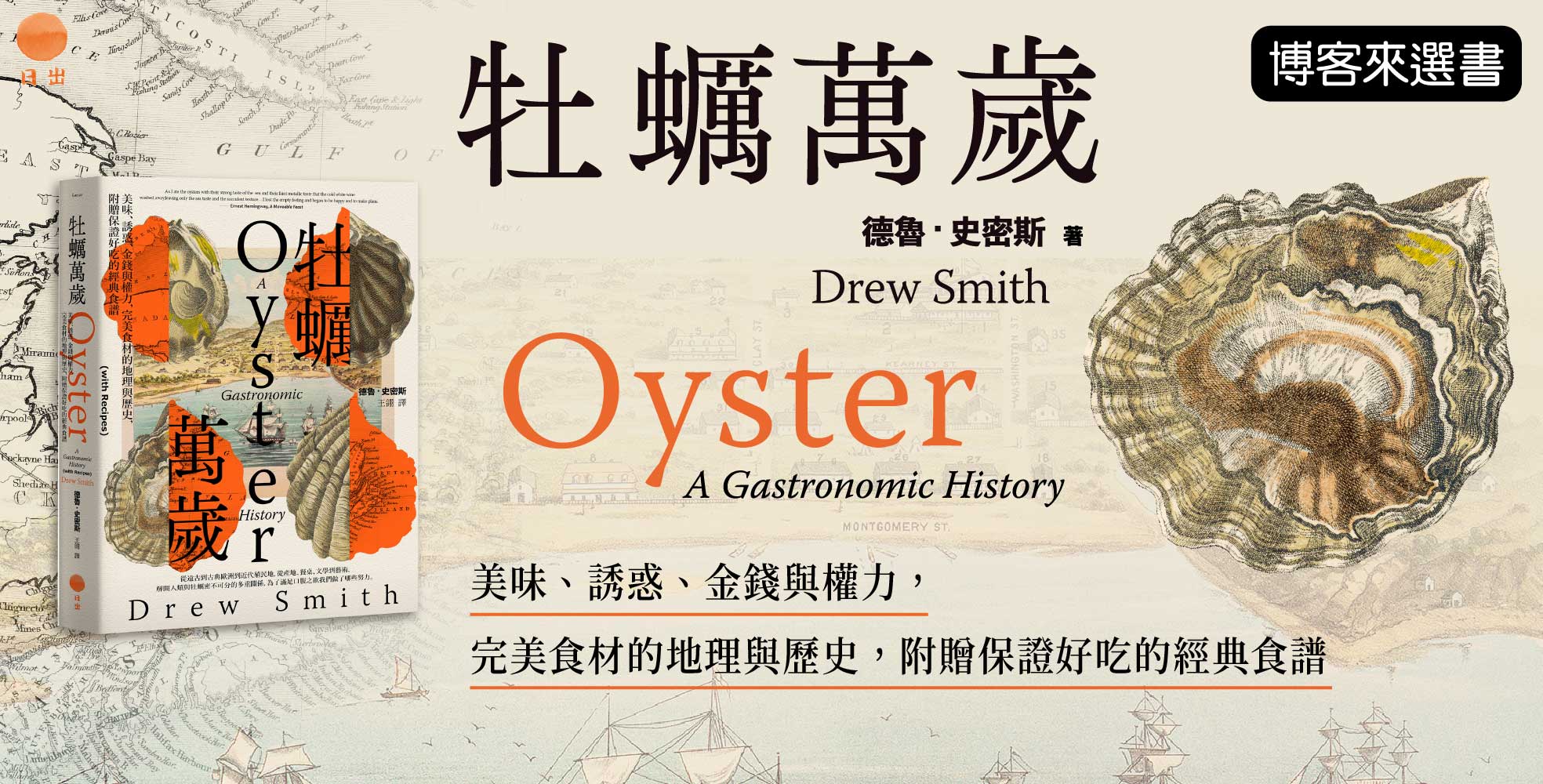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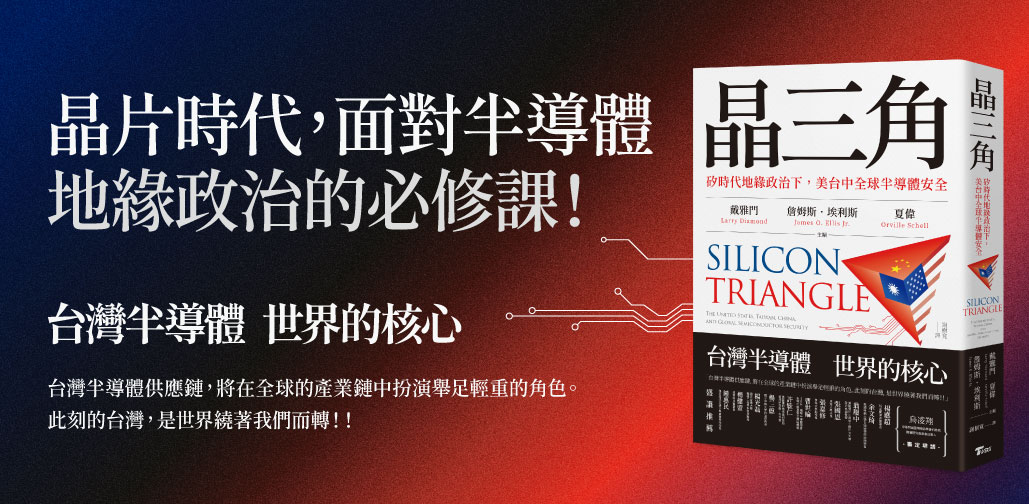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