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都是多重的編織,沒有單一的意義能夠獨立存在。多重編織造就了像花蓮這樣一個小市鎮的巨大。在一心街看見吃芝麻糊的林老師。在幸福牌腳踏車行看見勤學日本料理的母親。在中華路看見三十年前教過我爸英文的美國黑人博士。在立霧溪河口看見淘洗沙金的葡萄牙人。在花崗山聽見威權時代集會遊行時從喇叭竄出的訓斥聲。在復興街的一個巷子裡看到當年春日通某個來自朝鮮的時髦女子。
讀林宜澐新作《河岸花園了》,有時很難分辨,自己讀著的文字,究竟是散文或小說。事實上,除了長篇小說《海嘯》,他多年來累積的作品如《晾著》《東海岸減肥報告書》《耳朵游泳》《人人愛讀喜劇》等,當中縱有散文,總也讓他以擅長的短篇小說技巧飾加其上,虛實難辨,彷若戲法。
「《河岸花園了》雖然歸列在小說裡,基本上還是比較接近散文。但重點是我自己不太喜歡分類。」怎樣是小說、哪樣又才是散文,在哲學出身的林宜澐眼中,不過是圖個討論方便而已。「太拘泥在類別裡,反而會犧牲掉很多細節。」是以無論他說著什麼樣的故事,幾乎從不刻意去想,這次要寫成小說或散文。「可能因為某些習性,我都會隱然有個小說的底在裡頭吧。」
從事教職多年的林宜澐言談爽朗,不難想像他在課堂上是如何地妙語如珠。幾年前他自校園退休,轉而投入出版行列,先後成立東村出版與蔚藍文化,關注的始終不脫華文創作與台灣議題兩大要項。兩地奔波、忙於挖掘作者之餘,林宜澐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作者身分,以及他最熱愛的鄉土——花蓮。
「通常人在花蓮時,就會特別想寫。」《河岸花園了》當中的篇章,林宜澐前前後後寫了五年左右。一開始並未設下什麼特別的規範,信手拈來,藉著書中角色重現己身過往,像是記錄。「我是老莫,也是那個M。基本上裡面的每一個都是我自己。」而那些人們穿梭其間的街巷,那些食衣住行的日常勾勒,也都是一幕幕花蓮生活場景。讓整部小說更顯真實,也更加散文化。
「小說或散文就像是你要進入一個房間,想走大門還是要爬窗戶都可以,反正目的就是要進去;你若有本事從煙囪爬下來,那叫現代詩。」林宜澐放聲大笑,「反正主要描寫的就是人,人的感覺、人的情緒,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林宜澐要讓讀者看到的房間裡,有著些什麼?「法國葡萄酒界裡有個名詞是『terroir』,中文譯成『風土』,意思是每一座酒莊,都有各自的土地坡度、濕度、溫度、土壤性質等等,形成其專屬的terroir。」酒莊與酒莊間可能相距不過三、五百公尺之遙,就有著不同的terroir,讓法國酒莊以各自獨特的姿態林立在廣袤的田野當中,像是天上的星宿,彼此照耀競美,又互不過分干涉。

每天早上,林宜澐都會帶著一杯咖啡,拎著一份簡單的早餐,前往他固定的私房海邊所在,享用一大片蔚藍,「那就是我terroir裡的一部分。」看著眼前的海洋,可能什麼都不想地放空,可能思考下一步「花蓮三部曲」的寫作計畫,聽見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透過翻騰萬里而來的海浪,傳遞著什麼樣的訊息。
「每一個人應該都要有自己的terroir,對我來講就是花蓮。」你要讓哪些元素穿過你的輪廓、進到你的領域,空間定義的權力在你身上,你可以自己決定terroir的點點滴滴。好比書名「河岸花園了」,「河岸花園」即是空間,加上「了」字表示完成,林宜澐說,「所以整個意思是『我讓它變成我的terroir』,我的風土。」
在這片風土當中,林宜澐寫物,寫情,寫景,嬉笑怒罵地引入社會甚至政治種種,豐富了風土的樣貌。「但不管你寫生活、寫社會、寫國家、寫世界,到最後寫的都還是自己,處理的永遠是自己的問題。」正因為人根植於風土,所以也必須把自己的五感體會、生命成長,一併兜納其中,才是真正紮根、實踏在這塊土地上。「我的希望、我的熱情,我所看到的與感受到的,通通都在我的文字裡面了。」
有人十七世紀便來到了這片蔚藍海岸。有人清朝時跋山涉水到此地屯墾。也有日本女子因為愛上台灣男人,戰後選擇留下,而有了一群說著台灣國語的子孫。有遠離巴黎東來台灣的傳教士,年紀輕輕便在民國路的教堂許下大願,要把一切奉獻給上帝,終老在這條小小的街路上。
〔林宜澐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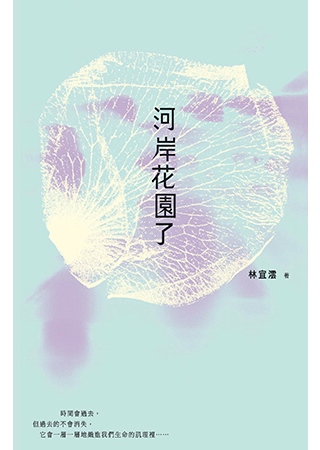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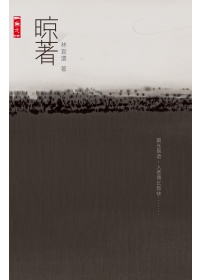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