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羅馬一處童軍中心,等待櫃檯人員給我正確的房間鑰匙,這裡潔淨、寬敞、採光充足、有秩序,不過人畢竟還是義大利人,他們凡事都需要預設兩次更正的機會。
在羅馬我遇見一個37歲的波蘭女人獨自旅行,她堅毅的眼神透露著多難母國孕育出的苦情色彩,她說她在20歲時跟一個騎「川崎」(kawasaki)重型機車的男孩戀愛,即使雙方家人都極度反對,他們卻堅信不移,男孩在一次騎行中將全身骨骼摔裂成數十個碎片,她在極度哀傷之下輟學,她原本的主修是文學。這位放棄文學的女孩在30歲搬到荷蘭之後,才開始學英文,現在已經十分流利,她強調雖然現在的男朋友每年都掏空存款地前往希臘駕船航海,但這個男人忠實地愛了她七年,而她現在終於有點開始墜入情網。
另一個利比亞人則從二樓的男子宿舍走下樓,在沙發上呆坐,他的阿拉伯長相稍偏兇悍,他的神情卻又憂鬱至極,他死命拜託我,聽他訴說一個後革命時代穆斯林男子的難處,他今年才30歲(令我十分驚訝,因為他看起來如此蒼老),在羅馬近郊一個我不記得名字的小城市念書,主修是機械。他知道就算順利畢業,即將破產的義大利就業市場,比起他動盪的北非祖國也好不到哪去,何況他既不是最優秀的學生,也不是最不要臉的生存高手,而他最大的憂慮就是沒有錢,一個沒有錢的穆斯林男子是討不到老婆的,一個都沒有,哪來的四個,更何況,現在還有「女性主義」。
「為什麼女人要出去工作就說不帶孩子?那到底要誰來照顧孩子?我是絕對不可能帶孩子跟做家事的。」他眉頭深鎖地說。
先不管現代人怎麼樣辛苦,大部分來羅馬觀光的人都是為了古蹟。而我跟古羅馬人有兩大共同愛好:一、愛去澡堂,二、愛看動物。
據說在西元455年羅馬陷落之後,全城慘遭肆虐,而後城裡只剩下七千多名羅馬人,但是去澡堂洗澡、去競技場看鬥獸的休閒生活依然繼續,帝國雖已不在,但是羅馬依然存在,澡堂、醇酒和美色腐化了偉大的帝國,但那些卻是羅馬生活最令人難以割捨的部分。無論戰爭與和平,新教或舊教,東方或西方,無論誰來侵略,誰來統治,誰來建設,羅馬,作為一個城市,它一直都在,所以羅馬被稱為「永恆之城」,但什麼是永恆呢?
漢語辭典對永恆的定義有二,兩者組合讓人心驚膽跳。
◎ 永恒 yǒnghéng
(1) [permanent;everlasting;perpetual]∶永遠不變;永遠存在
(2) [die]∶死亡
Virgil 的史詩裡,眾神之王朱比特這樣預言了羅馬的永恆:
I’ve fixed no limits or duration to their possessions:
I’ve given them empire without end.
神說祂不為羅馬定期限,祂給予羅馬一個沒有終止的帝國。
但是此時此刻,羅馬中央車站外並排的遊覽車引擎轟轟響著排出灰煙,來自法國、瑞士、東歐、義大利各地的列車紛紛進站,裡外遊人如織,吉普賽扒手與三七步歪站警察目光對峙,羅馬帝國,早已不在。
永恆的不是共和,也不是帝國,那是建築嗎?是信仰嗎?
到了羅馬當然要看古代遺跡,這裡的遺跡是看不完的,隨便地下一挖都有古蹟,所以羅馬雖然是歐洲人口第四多的城市,修到現在卻只建成兩條地鐵(在這裡我還見到了最不留餘地的地鐵車廂包版塗鴉)。羅馬競技場(Colosseo)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地鐵站,Ridley Scott 在為《神鬼戰士》勘景的時候曾經嫌棄競技場的本尊「太小」,但其實對於一個渺小的觀光客來說已經夠大,一出地鐵站就能看見那缺了一角的橢圓形劇場襯著天空的顏色,那缺口那麼完美,彷彿是上天故意為之的手段,當月亮升起的一刻,那破裂的斷面隱約透出血色一般的紅色調,彷彿正如那句「幾時有競技場,幾時便有羅馬」說的,它還滲出血光,它還活著。但其實現在所見那能把渺小人類一口吞沒的拱門,和密布在腳下的乾涸水道和通道,2/3都是19世紀重建的結果,現在將大理石凝結在一起的混凝土,是摩登時代的產物,而不是古代火山泥混入馬毛的骨董。
羅馬動物園也剛超越一百年的歷史,雖然在羅馬兩千七百年的歷史中,一百年實在如同九牛一毛。大約在光緒賢臣籌辦北京動物園、向德國商人買動物的同時,生意遍及三大洲的德國動物商哈根貝克,正為羅馬規劃一個嶄新的摩登動物園。跟當時其他以科學研究為主的歐洲動物園不一樣,羅馬動物園從一開始,就以服務市民、休閒娛樂為建設宗旨,所以讓動物「看似」自由自在地於園內綠蔭草地上漫步,這種Minimal Caging (牢籠最少化)的設計原則,也把羅馬市民那種享樂的天性服務得很妥貼。動物園位於Villa Borghese所在的蘋丘(Pincio)北坡,這是全羅馬第二大(一說第三大)的森林公園,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畢基(Ottorino Respighi)曾以此松林為題譜寫交響詩,描述一個晴朗的早晨,孩童在松樹間追逐著,一邊吟唱兒歌,一邊玩著扮演軍人的遊戲。那個晴朗的早晨,其實是一個法西斯的早晨,那一年是1924年,法西斯黨在義大利以2/3多數贏得大選。法西斯政權持續到第九年,對非洲衣索比亞發動了侵略戰爭,就在同一年,景觀建築師Raffaele De Vico在擴建工程中設計了兩棲館和大鳥園。
我試著從西班牙階梯延著登山步道翻越,寬敞的車道上時髦跑車和大型遊覽車不斷的呼嘯而過,拿著報紙閒晃的大叔和出租協力車的小哥都不斷地搭訕路人,慢跑者用耳機隔絕大自然的踅音與噪音,專心地征服前方的道路,我走了一個小時,經過那幾個收有提香、拉斐爾、卡拉瓦喬等國寶作品的美術館,標示不斷地告訴我,前往動物園還要翻過一座山。當我終於找到動物園入口,買了8歐元的票進入園內,這個近幾年才重新翻修的百年動物園,乍看跟其他新建的城市動物園沒有麼不同,綠色的圍欄、小家碧玉的入口、沒有廣場也沒有噴水池,只有現代動物園標準配備:一台不排廢氣的遊園小火車,我懷疑自己的信念不夠堅強,或是這景象太不羅馬,沒有關於古代的哲思,而是極力反映時代潮流。現在動物園的模樣,大致確定於1997年9月的全面翻修,除了外觀現代化,重要的是將動物園的宗旨從娛樂性強的「百獸園」轉型成一個肩負多樣性使命的「生態公園」,他們不再以珍奇動物或是物種數量為努力目標,而是有選擇的以瀕危物種為優先照顧對象,現在園內約有218個物種,據說為了送負傷動物進園治療的人不需要買門票。

(攝影/何曼莊)
新的設施還增加了許多非常體貼家庭孩童的設計,可惜我發現園內的孩童並不多,我所預期的校外教學團一個也見不到。義大利國民是否失去了他們優良的行動主義本能呢?雖然義大利男人永不厭倦的耍帥持續,將每一條斑馬線當成伸展台走秀,義大利女人依舊踩著四吋高跟鞋行走凹洞遍布的石板路,堅決兼顧性感與強悍。義大利男女從來不缺費洛蒙,但這樣一個熱愛生育的國度在2013年的出生率卻十分令人憂心,隨著經濟危機升高,義大利的出生率竟然下降到平均每位婦女生育1.41個嬰兒,在全世界排名203。
我走上一道木質階梯,階梯的寬度和坡度走起來完美舒適,登上高台,當你在高台上的長凳坐下,你的視線能與長頸鹿的眼神齊平。我坐在那裡看著長頸鹿緩慢地嚼食,發了一會呆,接近閉園時間四下無人,殘暑的南歐天依舊亮得令人炫目,這是我造訪的第14個動物園,我突然覺得,是說再見的時刻了。
我回想起展開這場動物園巡禮的當初,在倫敦,也跟現在一樣坐在長頸鹿的屋子裡,當然這隻長頸鹿跟那隻長頸鹿完全不同,我以後也許還會見到別的長頸鹿,但那一隻跟這一隻,又會是不同的長頸鹿。從來沒有兩隻長頸鹿是一模一樣的,也從來沒有兩個動物園能夠互相替代。
「你覺得呢?」我問兩隻長頸鹿之中頭比較大的那隻,他身邊的那隻小的是他的孩子,今年5歲,在羅馬出生。
長頸鹿邁開牠的長腿,小的緊跟在旁,牠們走路的步伐不慢,只是因為帶動了氣流,總讓人覺得是凌波微步。
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準備好,要回到人類的身邊。
在永恆之城說再見,沒有比這更適合的地方。
其實我大可不用流汗攀爬整座蘋丘,動物園後門處就有一個電車站,三號路面電車能把我從這裡帶往古競技場。古競技場曾經是集體飼養動物的地方,吃肉的掠食者和吃草的被掠者,同在那沒有天日的地窖裡吃喝、繁殖、茁壯之後,激烈地死去,牠們之所以在那裡生,就是為了在那裡死,光在競技場落成的頭一百天慶典中,就有九千多頭動物死去,而那些人類奴隸、戰士與被抓的教徒也是如此,數十萬人曾經先後葬身在這巨大的圓形墳塚裡。當現代觀光客花了12歐元排隊進入,掛在鐵欄杆上用手機拍照,那些曾經關押獅子、老虎、異教徒的格子間頂已被打開,裡面的石塊與草木完全暴露在空氣中,像是一個個枯骨失散的墓穴,死亡真的帶給死者永恆了嗎?
他們說在1871年重修競技場時,整個廢棄遺跡上,已經被四百多種植物給層層疊疊地覆蓋,為什麼能達到如此驚人的多樣性呢?那些從異國被帶到這裡的珍奇猛獸,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外來植物種子,而荒廢了幾百年的橢圓形劇場,就像一個溫室一樣,形成了不受周邊天氣影響的微型氣候圈,在這裡死去的生命留下了鮮血與骨肉,成為土壤中的養分,長成樹與草,往天空的方向竄去、開出花來、再結成果實、留下種子,永恆的其實不是城市,而是物種生生不息。
哪一個人不是因為對人類有點失望,所以轉頭面向動物的方向,我承認我也有那麼一點逃避的心情,但是到頭來,動物園是那麼好的地方,溫柔地,陪我走了這麼漫長的路。在永恆之城羅馬,其實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永遠不變的,但只要人類繼續帶著新生的孩子,來到這個地方探望動物新生的孩子,整個地球就會再往永恆接近一點點。

(攝影/何曼莊)
作者簡介
曾任《換日線》英語頻道Crossing.NYC 特約主筆。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以及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和散文集《有時跳舞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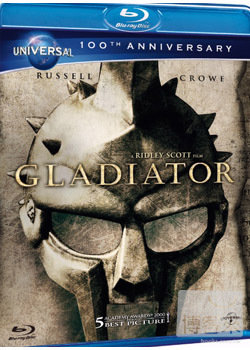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