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文譯者、資深編輯、作家吳繼文。
日文譯者、資深編輯、作家吳繼文。
聽吳繼文說話有一種平靜感。但聊的多半與翻譯無關。
編輯出身的他,一度寫詩,寫舞台劇,也寫小說。兩部長篇作品《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天河撩亂》於上世紀末出版時,其藝術性與半自傳的家族敘寫,對當代文壇造成不小震撼,在同志文學界占有一定地位。
倏忽近20年,這漫長的時光,吳繼文轉以一部部的譯作堆疊,吉本芭娜娜早期作品多出自他手,如《廚房》《哀愁的預感》《鶇TUGUMI》,以及中沢新一《看不見的人》、井上靖《初始:井上靖的童年與青春》《我的母親手記》、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 藤原新也《印度放浪》等,而最近期三本譯作《為何是植物圖鑑:中平卓馬映像論集》《雲水一年:行住坐臥永平寺》《直面生死的告白:一位曹洞宗禪僧的出家緣由與說法》出版時間相去不遠,吳繼文說,那是各社在安排進度時的巧合。

真要計較起來,無論是譯或寫,吳繼文的文字產量不算豐厚,似乎不太認真將自己往譯者、作家的路上推進。問他手上多半忙些什麼,他淡淡地笑說自己是真的不夠努力,「就生活吧。」
「(寫作方面)講直白一點,以前比較做作,因為愛好文學,就自以為是文青,事實上對人對事都還是平順地過,代價就是過得浮面了。」吳繼文自認少了考驗與累積,缺乏進步,寫的東西也不會比以前有意思。「等到自己知道得多一些,野心又大了,想完成一個東西的難度又加強了──結果每次寫的都不是真正想要的,只好一再重來。就這樣拖拖拉拉的。」
那翻譯呢?「翻譯就是,你不必停留,時候到就一定要完成,等於有個作品可以交代。」他約莫一年一本譯作,彷彿年度的行禮如儀。「加上不少作品也是自己喜歡的,譯的時候就會一邊學到很多。」
他的翻譯生涯從吉本芭娜娜開始。「說白了,因為吉本的作品不複雜,卻讓人很有感覺。」過去在編輯台上,吳繼文看著諸多作者透過書寫進行各式各樣的實驗,放眼繁花處處,自我滿足或許有之,讀者卻不見得都能掌握到其中想傳達的訊息。「年輕時我總認為寫作要帶些文藝腔才有文學性,但吉本用樸素的文筆,說了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如果我寫小說,我希望它是簡單而不空洞的。芭娜娜讓我看到了這樣的可能。」譯也好,寫也好,是吉本芭娜娜給了他信心,「這是真的,不是謙虛。」他又強調了一次。


他的譯筆目前在野々村馨的《雲水一年》後就先打住了,不特別急著要接其他新的翻譯工作。《雲水一年》譯期不過數月,然他與作者修行所在的永平寺,淵源卻可追溯到30幾年前。「我在日本讀大學時,有次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畫面。那是冬天,永平寺外一群年輕的出家人,穿著僧服、草鞋,背著行李,排排站在山門前的雪地裡,等著裡面的人開門讓他們進去。大雪落在他們身上,偶爾有人從裡面將門開個小縫,問門外來者何事,像是一場儀式。」那是永平寺對修行者的第一場考驗,也是吳繼文對永平寺最初的印象。
畢業回台進入出版業,他藉由赴日參加書展之餘前往永平寺參訪,親身感受生活與修行的體會。也是約莫在擔任譯者的那幾年後,吳繼文皈依佛教,因緣際會接觸幾個不同宗派,也透過翻譯,對佛教有了再深一層的了解。從臨濟宗、藏傳佛教(《西藏旅行記》)、南傳佛教到曹洞宗(《雲水一年》《直面生死的告白》),一路走來,他既是譯者,似乎也輾轉成了修行人。

「每一次的翻譯都像爬山,都很辛苦。假如一本書400頁,一開始怎麼譯好像都沒減少,每一頁都好漫長。但過半之後就像下山,會好一點。之後終於剩100頁、剩50頁,好像可以看到光明的盡頭。」說穿了,都是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壓力。
翻譯這麼苦,那有可能一邊翻譯一邊寫作嗎?「修行時,師父給過一個提醒:人的意識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個念頭。常常我們以為自己好像同時在想很多事,事實上,你的意識裡永遠只有一個念頭。」
「工作也是一樣。假設一次接好幾本書,這本卡住就先換到另一本,或那本進行三分之一,就先去寫自己的東西,那你與一本書好不容易培養的某種節奏,突然間就消失了,結果所有的東西都懸而未決,反而不好。」
所以就讓自己一次做一件事,就像《雲水一年》所述,永平寺給予修行者的嚴厲要求──坐姿要保持挺直,不可左歪右斜或前俯後仰。必須讓兩耳對齊雙肩,鼻梁與肚臍保持一直線。舌尖抵著上顎,並以鼻孔呼吸,讓唇齒緊閉……再小的生活瑣事,都視為唯一的生命大事,吳繼文說,「說真的,人的時間也不多。無論寫作或翻譯,都把每本當成是最後一本,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吧。」

吳繼文譯作
延伸閱讀
1.【專訪】用嬰兒的眼睛看世界,用成人的頭腦思考──專訪攝影家藤原新也
2.【書評】體罰、辱罵、挨餓的修煉值得嗎?──王盛弘讀《雲水一年:行住坐臥永平寺》
3.【書評】汪正翔:為何比起真實,我們更想透過照片營造「假的現實」?──讀中平卓馬《為何是植物圖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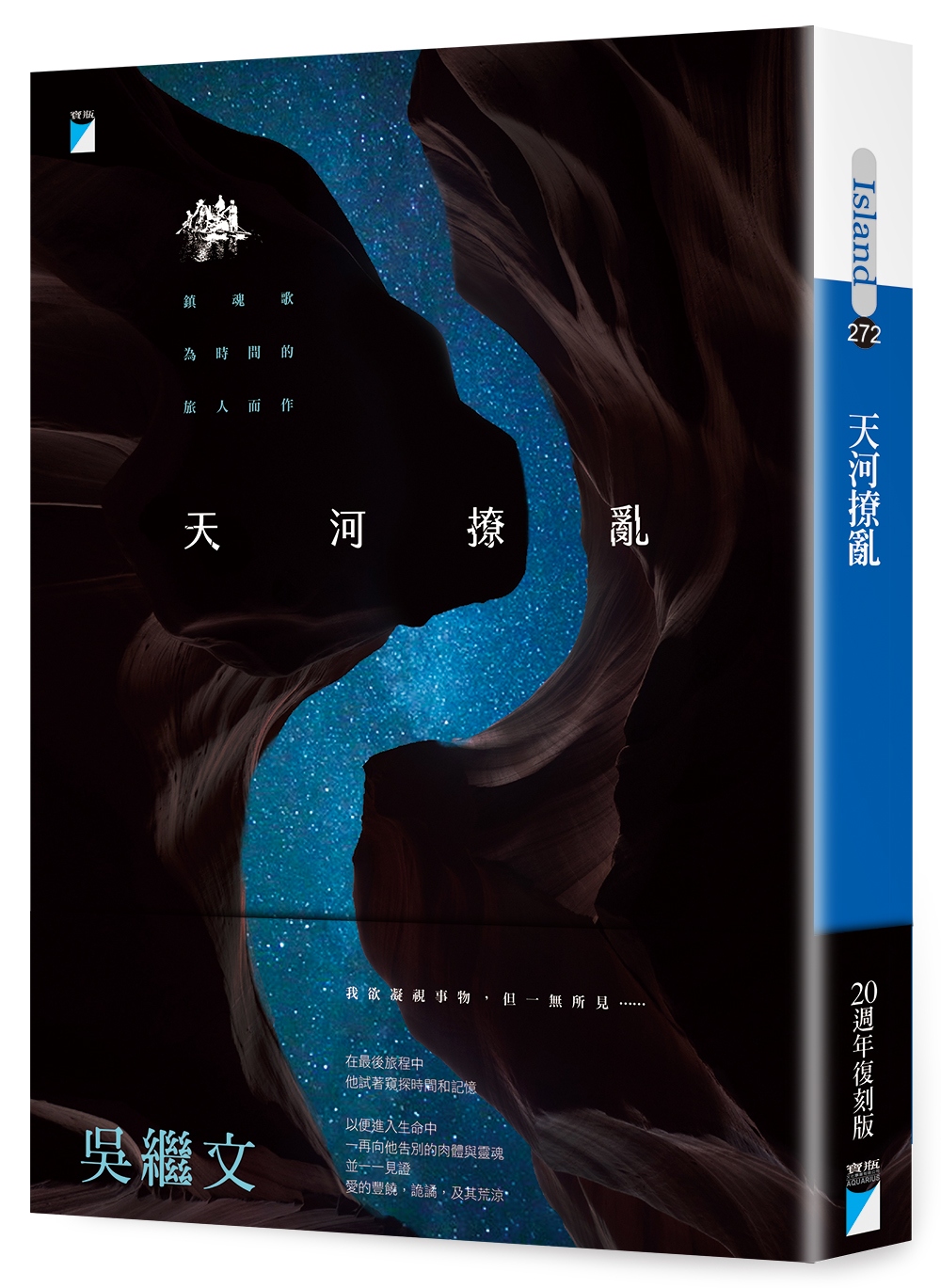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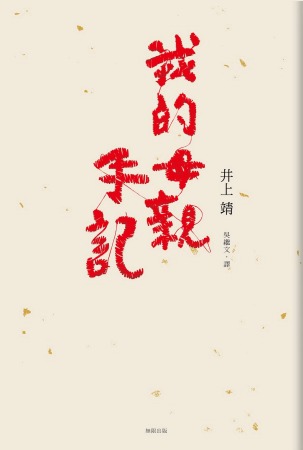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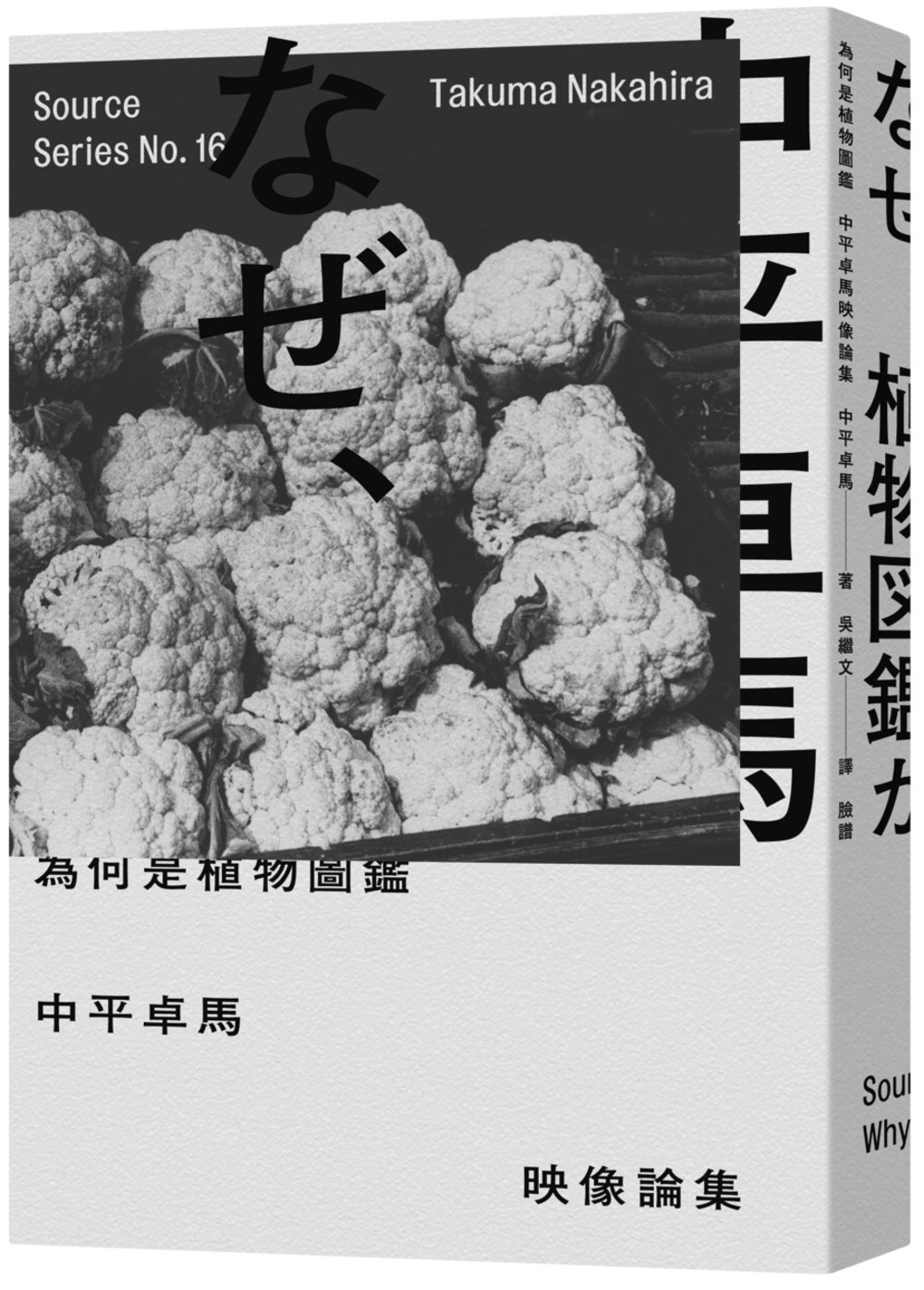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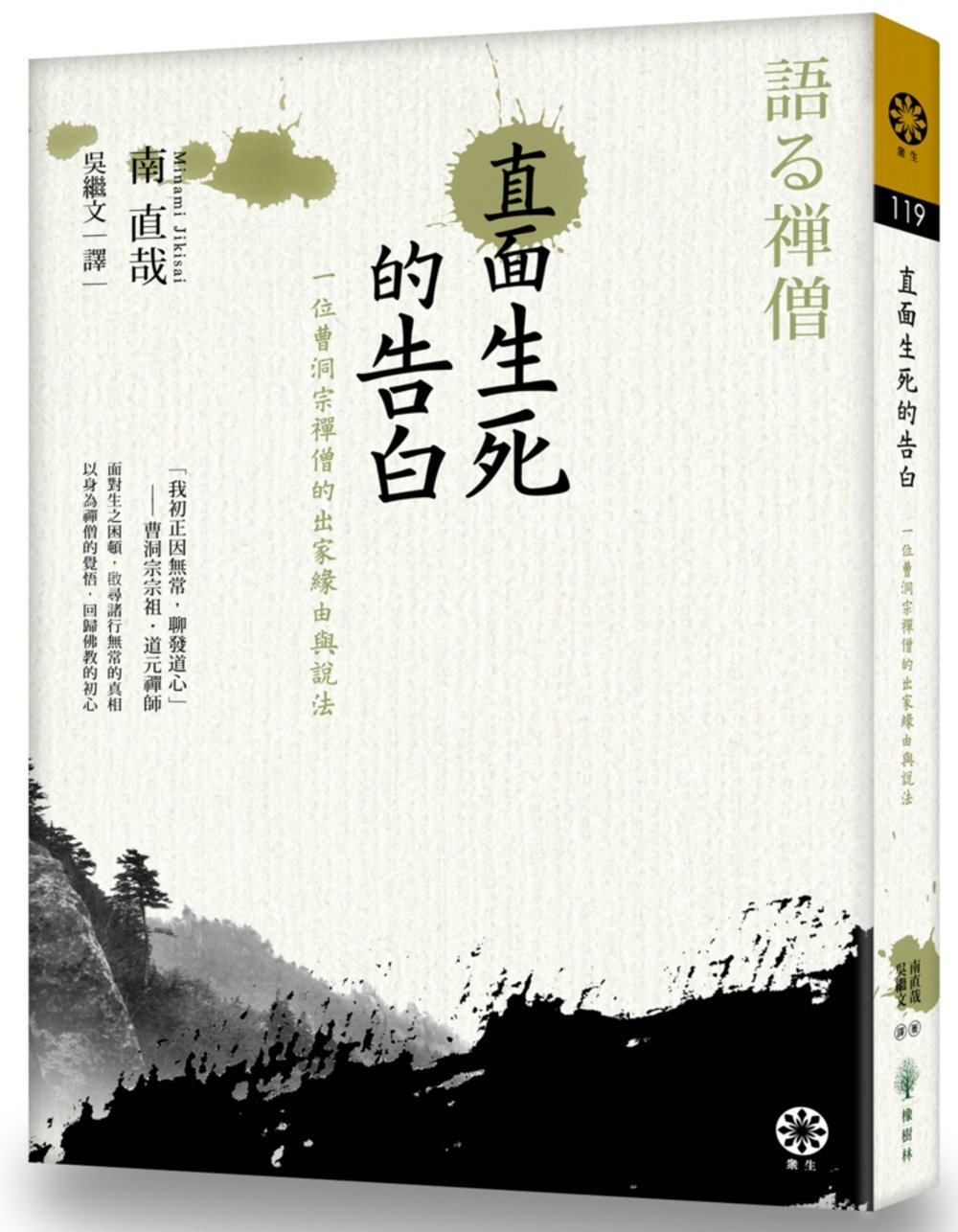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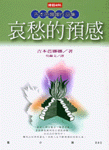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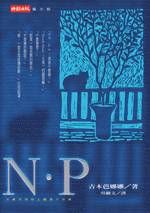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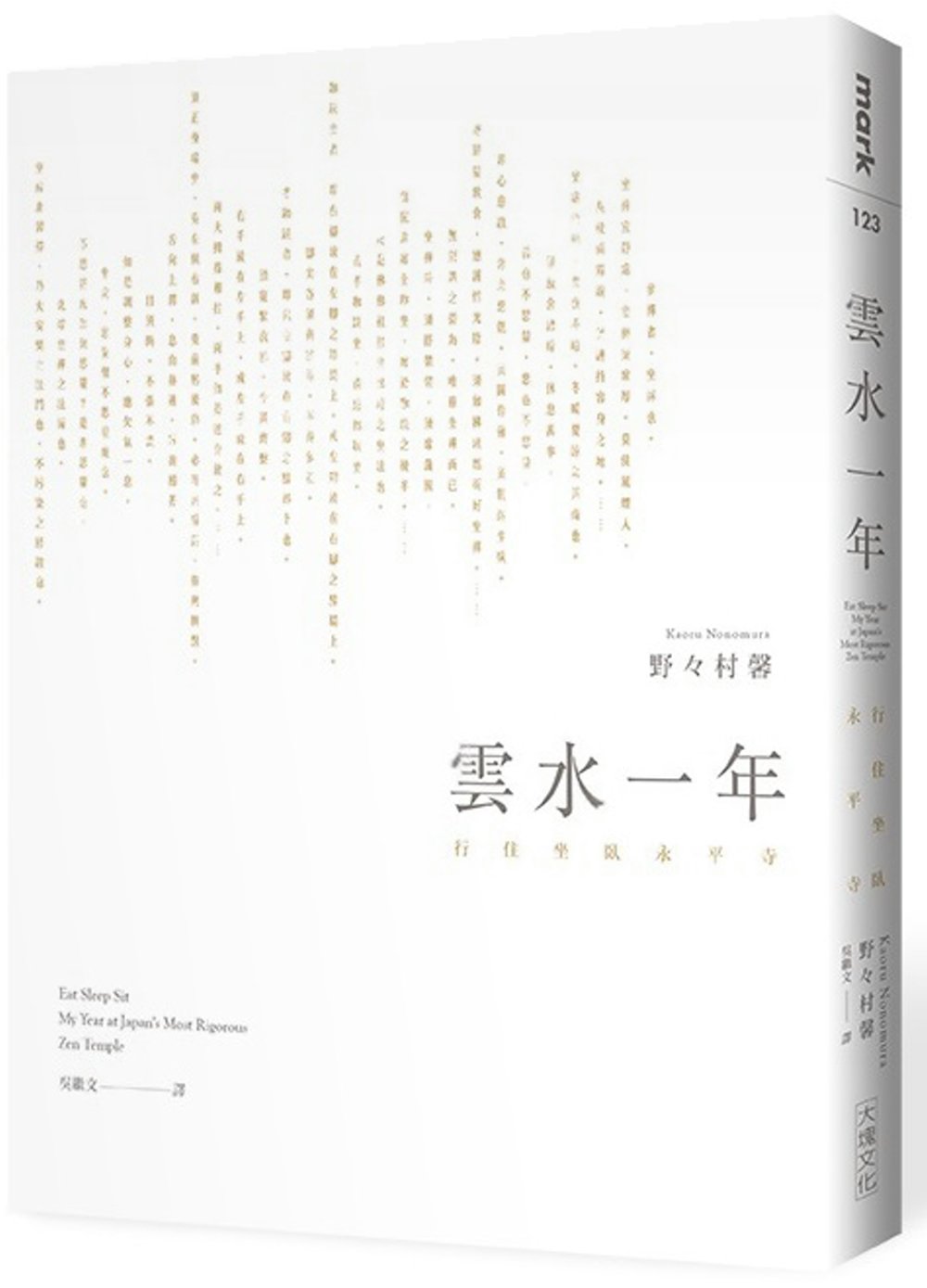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