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嗅覺敏銳的葛奴乙,對他人而言,他沒存在過,只有美認識他,他們彼此都如此孤獨,他遂與它進行一場場戀愛,並且接受它的殘暴統治。美利用他的「不存在」,向眾人最後一次現身,揭露了所有人內心「自認不存在」的真相。
自始至終,他都為了品嚐愛、模擬愛,來證實自己跟這世界的關聯,這場徒勞,千瘡百孔,如同他感受的千萬氣味,每個毛細孔都舒張開來,直到他人體散失,他是這樣地企圖擁抱般地與這世界擦肩而過,這才發現人們與世界正互不相識地共處著,原來還有比他更「寂寞」的,所有人內心的「存在危機」,竟是這一切穿金戴銀的洪荒能運轉至今的核心動力。
《香水》這部電影,最引起話題的一幕是,廣場上所有原本要制裁萬惡葛奴乙的群眾,從憤慨到萬人膜拜與性愛,揭露了美的本質,它已無法仁慈,因它所到之處,眾人的空虛都會湧向它,吻它的腳尖、呼吸它的經過,它無法回應,他們向它乞討著的是永恆。那「永恆」,空虛到慈悲都沒有用。於是,在人統治世界數千年後,由最美的萬物生出一個醜惡的葛奴乙,是美轉身前對這世界的回眸禮。
電影《絕美之城》中,人們迷戀羅馬之美,為其風華而悲嘆,即便是末世,也想向曾青春的羅馬偷點香,醉生而夢死,以一個回憶的守墓人自傲自居。直到某一日,天主教的聖者問男主角捷普:「為何不再寫下一本小說?」作者回答說:「因為我再也沒有看到絕世之美。」年老的聖者回答:「你知道,我為何都吃菜根度日嗎?那是根本。」同樣生活在極美之城,巴黎的葛奴乙該說是不幸嗎?比起電影中富裕的義大利作家,葛奴乙在惡劣的環境生存,卻更接近美的本性,讓「醜」都能猙獰綻放。前者生長在大觀園,景美而人美,不敢揭開表象,後者則是張愛玲一眼就瞧出的華麗袍子下的餓蟲,布一掀,就整個傾巢而出。
被視為奇醜無比的葛奴乙,誕生的地方是在充滿魚鱗飛刮、老鼠橫行的市場,在所有食材被奪去生命的現場,一坨肉(葛奴乙)就這樣被扔置在一攤血水裡,這樣的誕生,集所有人們迴避生活的醜惡之大全,他個人也往醜裡活去,生存得沒有一瞬稱得上是美的,這樣的人,有可能比我們更認識美的存在?
很簡單,因他沒有美的一般性與美的平均值,美在他的世界,不像在我們這裡,終究會迎來令人生膩的加工循環,或被鈔票砸死的命運。美的原形在凡夫俗子的耍弄中,正踩著臭水,揮刀而來。
《香水》其實根本不像驚悚劇,它單純是以美的奴僕身分,在陳述自己主人的難以取悅,你要如何將自己的七魂六魄當成貢品,來求得它一秒的認同。被它選中的人,剎那間就被決定命運。因為以人類身體腐敗速度,來追尋美的永恆,如同借天上的一把清香栽種於自身之中,你必須以恰當的腐化,才能孕育那無可比擬的瞬間,讓它昂揚至天界的高度,本質上就已經按下自毀的快播鍵。
美知道識貨的人少,因此對於認識它的人是霸占且殘酷的。一位天才如何承受美的攻擊性?它那純粹、獨霸、驕傲,且沒有終點的催促,當你一旦見識過且臣服於它,就將成為它的奴隸,沒有二話可說的跟隨至死。這無論在《威尼斯之死》、貝多芬的《快樂頌》、《一代茶聖 千利休之死》,以及米開朗基羅、梵谷留下的書信,都可以看得出來,天才往往是美的奴隸,像場青春的延長賽,終其一生留下殘壘。
而《香水》中的葛奴乙,一個腥臭階級的無味存在,美成為他唯一救贖,有能力以嗅覺建構了美麗的宇宙,當他的肉體已純粹成為勞動工具,精神上會有多飢渴?他被卑賤化到也不知道什麼叫寂寞。一個生來連喜怒哀樂都被奪去的人,那氣味的分子不斷催使著他,上天下地找他人生數得出的「快樂」,連殺人是罪,他都沒有意識到。被視若「蟲子」來養育的他,他如一隻蚊子吸血,人在他眼中,也被氣味給分子化了,他不確知「人」是什麼。
於是,當他避居在山洞時,感到無比暢快,他自覺有家,在那裡自稱是葛奴乙大帝,幻想著蟲子、土壤與他自成一國,但也迎來他這一生第一次的「悲傷」感受:是他襤褸野居多年,發現自己身上除了衣味,甚至連一點體汗味都沒有,這次是徹底被整個世界遺棄,他從被丟在魚攤下、被保母、教會、育幼院遺棄……這都沒什麼,如今連與天地的關聯都沒有,這次是最終的遺棄了。那一刻,他知道他殺人來模擬的愛,終究與他無關,愛常會完成自己本身,卻與當事人沒有關係。
講到這,你或許就知道他完全被寂寞吞噬了。這個個體連稱「寂寞」都過分奢侈,無論在十八世紀的巴黎,或是今日,屬於葛奴乙的「寂寞」是去人化的,如機器,直到腦力身體都無法應付。像葛奴乙的母親,每每在殺完魚後,在攤下生下小孩,連續死胎放水流,下體血水未乾繼續叫賣,而由於葛奴乙的哭聲,讓她的頭被砍下來,一切不足掛齒。於是其他階級更汲汲營營,尋求的不過就是可供人掛齒的份量,最好是比牙縫的菜屑還多一點的份量。
於是乎,當葛奴乙將處女香魂之水灑置眾人時,人們會忘情地膜拜,那不證自明的存在感是多麼難得,此時竟有如此精神上的輕盈,來征服左岸長年以氣味來申明自己的焦慮。所有的階級頓時回歸為一片粉色肉海,流向那形而上的母體胎盤,在那裡終於再也不會有「存在與否」的問題。

於是乎,當葛奴乙將處女香魂之水灑置眾人時,人們會忘情地膜拜。
人們的存在焦慮,葛奴乙以幻術將它們暫時彌平了,但於他,則因此舉更確定了「不存在」的本質。作家徐四金曾表明這故事受到希特勒催眠群眾的影響。只要能讓百姓確認自己是「真正存在」的,就算殺掉異族也無所謂。因此人們也膜拜葛奴乙為王,彷彿藉由香氣被這世界擁抱甚至與其交媾了,虛空中的虛空。所以葛奴乙將自身灑滿香水,讓他們給吃了,說明這極美之城並無異於他的空虛,華麗袍子跟虱子終成為一體,他這才安眠了。
美的殘虐性在於它意外高舉了你,直到你看到一切,世界初始的美與人類為座標自己的競美徹底地分道揚鑣,那是孤絕的開始,這份「四下無人」的孤絕也將陪你到終點。而其他人,眼耳口鼻相牽制,混沌未明,方能响午打盹,夜飽生嗝,不知孤獨大軍片甲不留的臨門前,孤單們在微不足道中晉身,壯大於方寸之中,總還是幸福的。「有人曾被美帶走了嗎?」這大抵是回音吧,醜旋即往另一頭走,那方軍容壯大,它知道寄生比存在實在多了,而事實證明,美正絕種於各代金勢與權力交替中,它的殘虐骨血裡有多悲傷,也不過一個葛奴乙,至今仍無人掛齒。
〔電影簡介〕
《香水》是 2006 年的德國電影,改編自徐四金 1985 年出版的同名經典小說,寫戲本出身的徐四金以魔幻殘酷的筆法現形 18 世紀的巴黎,書中主角葛奴乙為尋香而奪取多名處女生命,被視為「天才與惡魔的混合體」,而書中由葛奴乙鼻中嗅聞出的大千世界與一般人視覺的印象更是大異其趣,因此此書出版時震驚視聽,為擁有27種以上語文譯本的暢銷作品。
電影則由湯姆‧提克威執導,相較於書,電影企圖在葛奴乙惡魔背後的人性面上找尋其犯案動機,因此評價兩極,但滄海之於一粟,與一粟之於滄海,各有不同推演。這故事無論從書或電影中,都有如哈哈鏡的效果,考驗人們潛意識中的氣味既被標籤化卻又難以捉摸,每次閱讀或觀看,幻象與真實都有不同拉距。
作者簡介
多年寫樂評也寫電影,曾當過金曲、金音獎評審,但嗜好是用專欄文偷渡點觀察,有個部落格【我的Live House】,文章看似是憤青寫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說的),但自認是個內心溫暖的少女前輩(咦?)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當代寂寞考》與《長夜之光:電影擁抱千瘡百孔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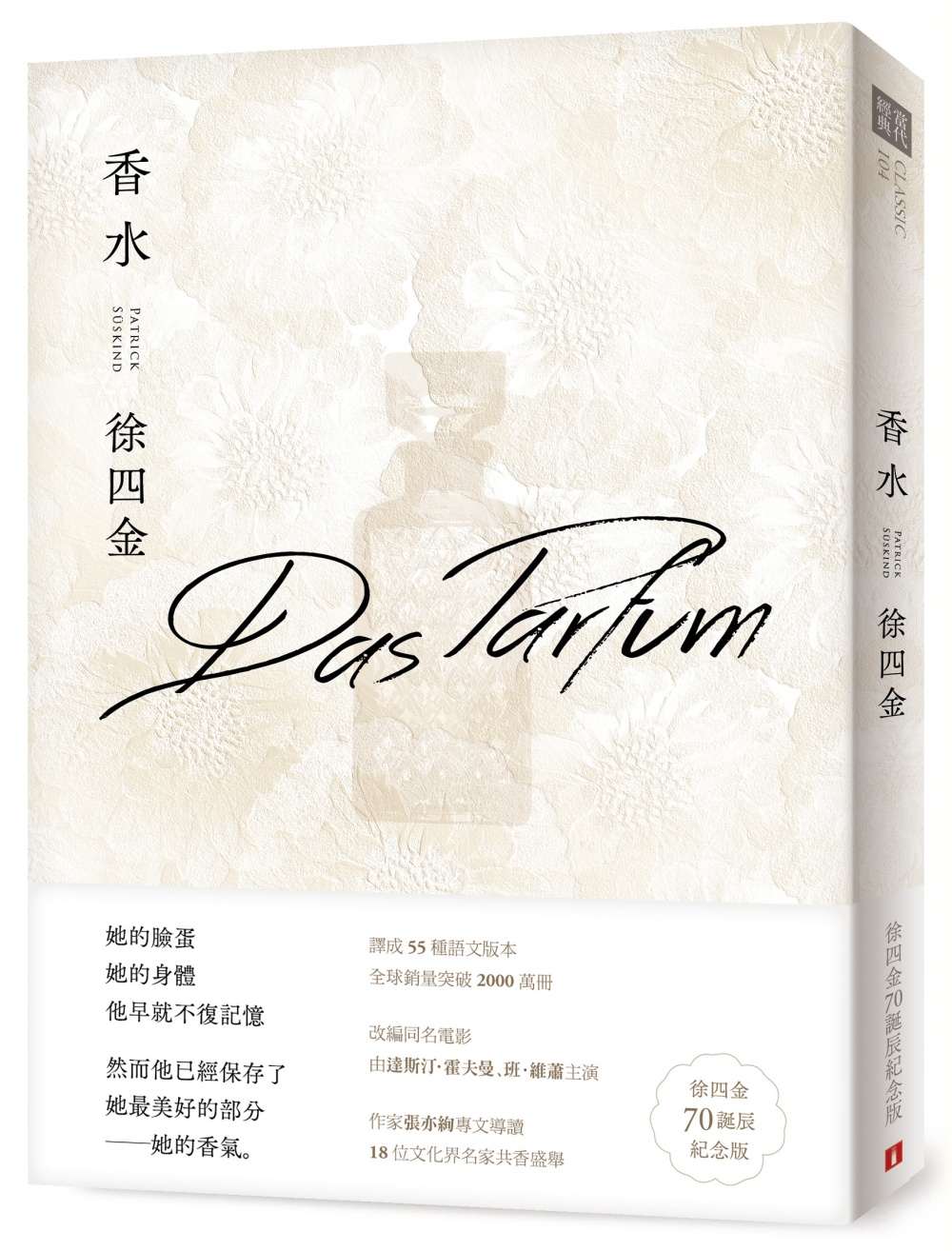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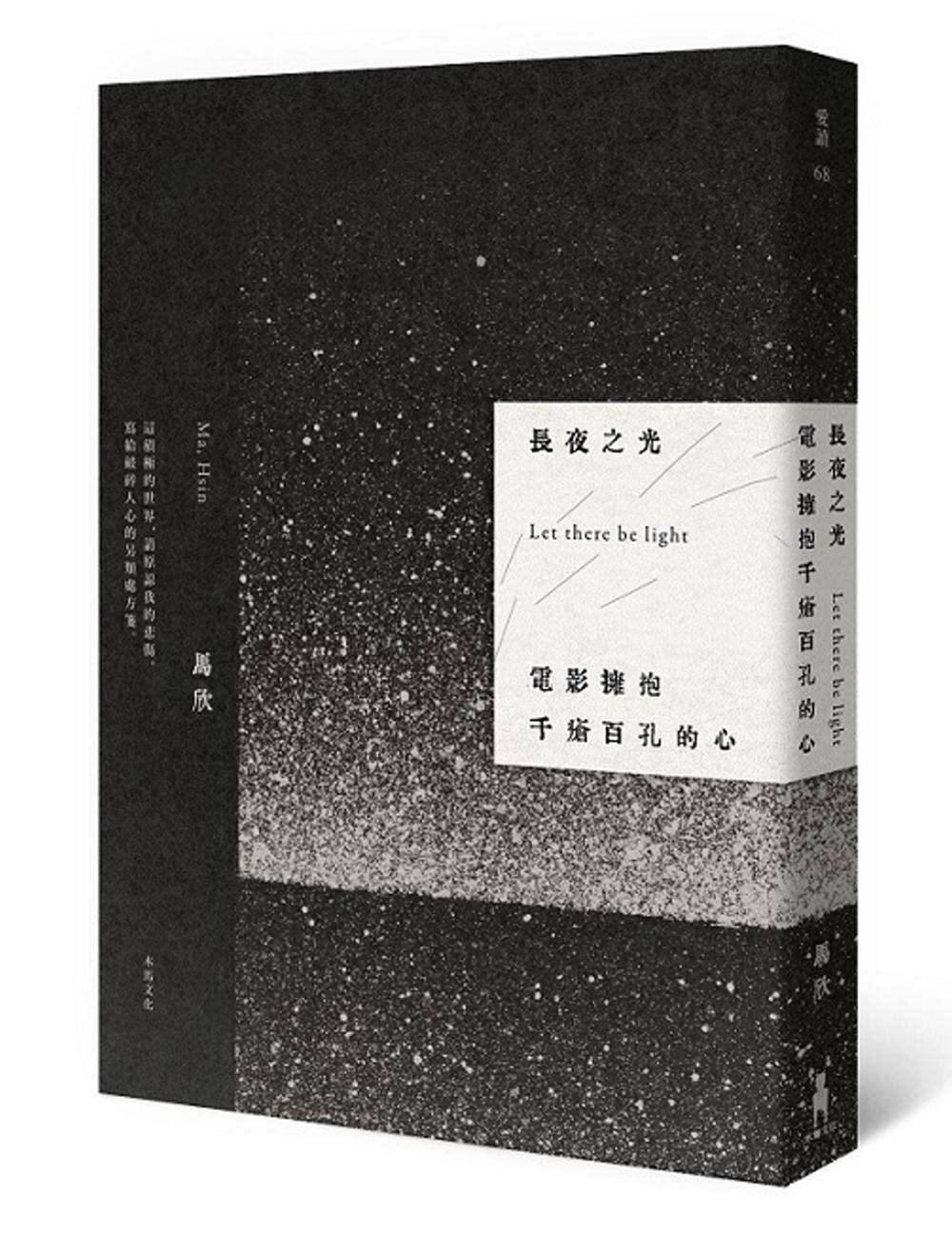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