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劉梓潔說話時有種令人安心的節奏。她會好好地將字一個一個擺放在空氣裡,慢而清晰,打上句點後,遞出微笑,令聽者感到舒心。相較之下,她的文字則波濤洶湧,在俗世塵埃中篩出故事。從《親愛的小孩》到《遇見》,她寫下人生的業力與機遇,人在情感江湖中沉浮,滄桑也達觀。
今年,她交出第一本長篇小說《真的》,書名為「真」,故事卻從一場騙局開始。小說第一個句子便是:「自遇詐騙以來,看什麼皆假。」
詐騙是小說的主軸之一,最早觸動她寫詐騙題材的,是那則「台積電女博士與美國中情局局長網戀」的新聞。然而,小說一路前進,案情卻沒這麼單純,在詐騙之外,還有個寫小說的人,幫小說家代筆的影子寫手,以及,模糊虛構與現實界線的小說人物。
如此複雜卻縝密的世界其實構思已久,她寫完《遇見》便開始構想這本書,但當時在《滾石愛情故事》的編劇工作中,只能先在腦中盤整,也一邊蒐集資料,直至去年九月才開始動筆。因為固定在《皇冠雜誌》連載,讓她每月穩定產出萬字章節。劉梓潔笑說,「連載時,小說往後寫不會有問題,但往前看會出現bug,有點像on檔戲。」集結成書時,她並沒有大幅修改,頂多修去不甚合理的細節。同時,為配合「網路詐騙」的情節,本書在排版設計上也有巧思,試圖發揮紙本和印刷能達到的最大功能,擬仿出電腦或手機裝置上的動態效果。
《真的》的結構彷如電影《全面啟動》,讀者在閱讀中似置身夢境,三組小說人馬在不同次元中互動。劉梓潔出手長篇,也全面啟動構築了極富野心的虛實世界。她解釋,「整部小說的結構是:『故事』、『說故事的人』和『故事之外真實的人』。三個同心圓並非各走各的,他們會彼此穿過虛實兩界之間的薄膜,附身或變身。」
她在這三層世界中放置了愛與不愛、真與假、現實與想像、坦承與欺騙等二元辯證,為對應這些二元性,她在形式上設計了幾層關卡,「首先,我讓讀者讀完第一章就發現:『這章是假的,是小說裡的小說』,有點像對讀者玩遊戲或下戰帖。」層層推演,讀者終會在故事的故事之外發現,小說家要談的,其實是「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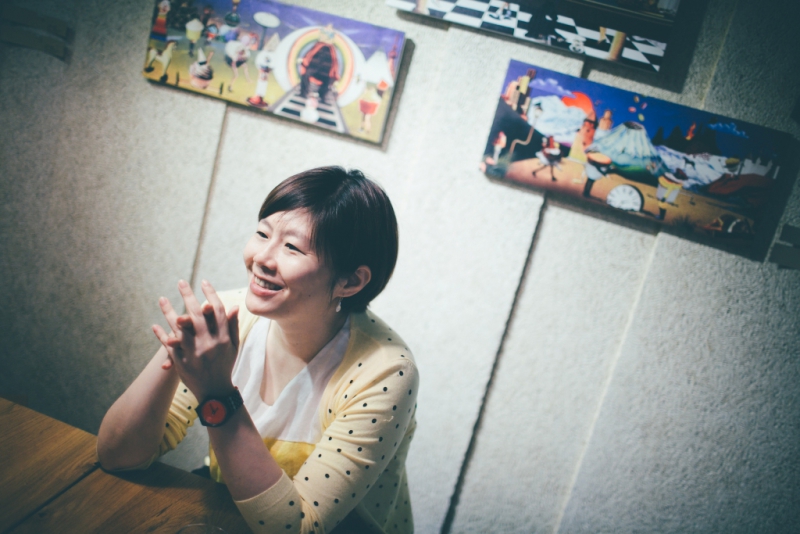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劉梓潔可說是全方位的寫作者,早年從事採訪工作,也做過影子寫手,散文、雜文、評論、小說、劇本等文類幾乎無一不碰,寫作多年,她認為最大的樂趣還是虛構。「寫了兩本短篇後,我想在長篇中處理比較大的問題,也算是整理自己的寫作經驗。」《真的》的女主角是個影子寫手,她如偵探般貫穿全書,探詢「真相」,然而,她創造故事,也被故事「創造」。「她在書中一直在問的是:騙子到底在哪?真相到底是什麼?但整本小說在問的其實是:誰是寫小說的人?小說的故事從哪裡來?誰有交易故事的權力?真實事件如何變成虛構作品?」
於是,小說中人在各種角色中進出,同一個名字在情節的操作下不斷翻轉,皆在回應劉梓潔對於「小說」這個文類的思考。「小說像是一個挖掘和打磨的工具,在虛構中探究真實。」寫小說的人,到底在扮演或紀錄?甚而一人分飾多角?「小說家這個職業對我來說,就像是神的影子寫手。所以各式各樣的身分,不過是透過小說這項技藝用虛構的方式出現而已。」
對她來說,寫作是件愈寫愈清晰的事。「以前可能比較任性,不想寫就去拍個電影,去上班,想寫再回來。後來覺得不能這樣,再回來寫的時候,技術和能力會停在上一本的狀態,我需要慢慢累積,一本一本寫上去。」《父後七日》的成功與暢銷為劉梓潔帶來名聲,也是將她推向創作之途的力量。「《親愛的小孩》之後,我才更確定自己就是要寫小說。」劉梓潔說,「寫作比較接近修行,如果我來這世上有個使命,也許就是寫。」
 (攝影/陳佩芸)
(攝影/陳佩芸)
她曾任《徵婚啟事》《滾石愛情故事》編劇統籌,同樣是創作,編劇比較是個讓她得以溫飽的工作,她認為劇本和小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各有其目的使命。「若可以授權給信任的編劇,我寧可以不要改編自己的作品,我想說的話在寫小說階段已完成。況且寫劇本需要耐性,必須應對整個產業和團隊,最終它會成為影像,不能在文字上面執著。」
小說一啟動,筆下的角色們便是共同生活的夥伴。劉梓潔曾在其他訪問中提過,「小說家就像運動員,我經常覺得自己在做的其實是體力活,工作時以整個身體在應對,身體好像是接收故事的平台,只有在最佳狀態時,才能接收到各式各樣的故事。」以身體與小說相依,她卯足全力投入這個體力活,小說完成,也像與這些親密的夥伴道別。劉梓潔似乎愈說愈往心底去,我們問她,那麼,寫完會失落嗎?原本穩穩訴說的她,突然紅了眼眶。
如此情深義重,約莫不負寫作之神的期待了。
劉梓潔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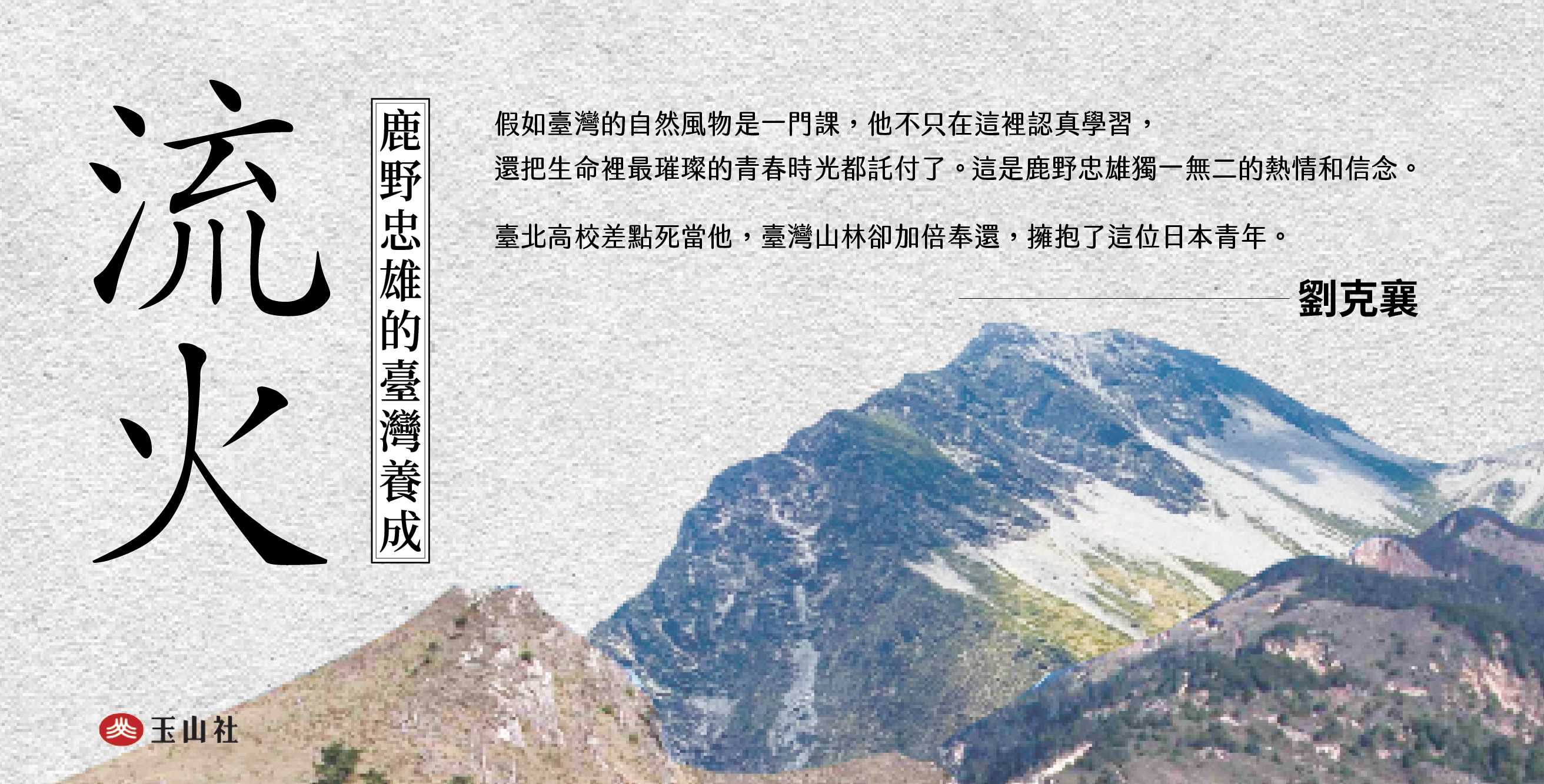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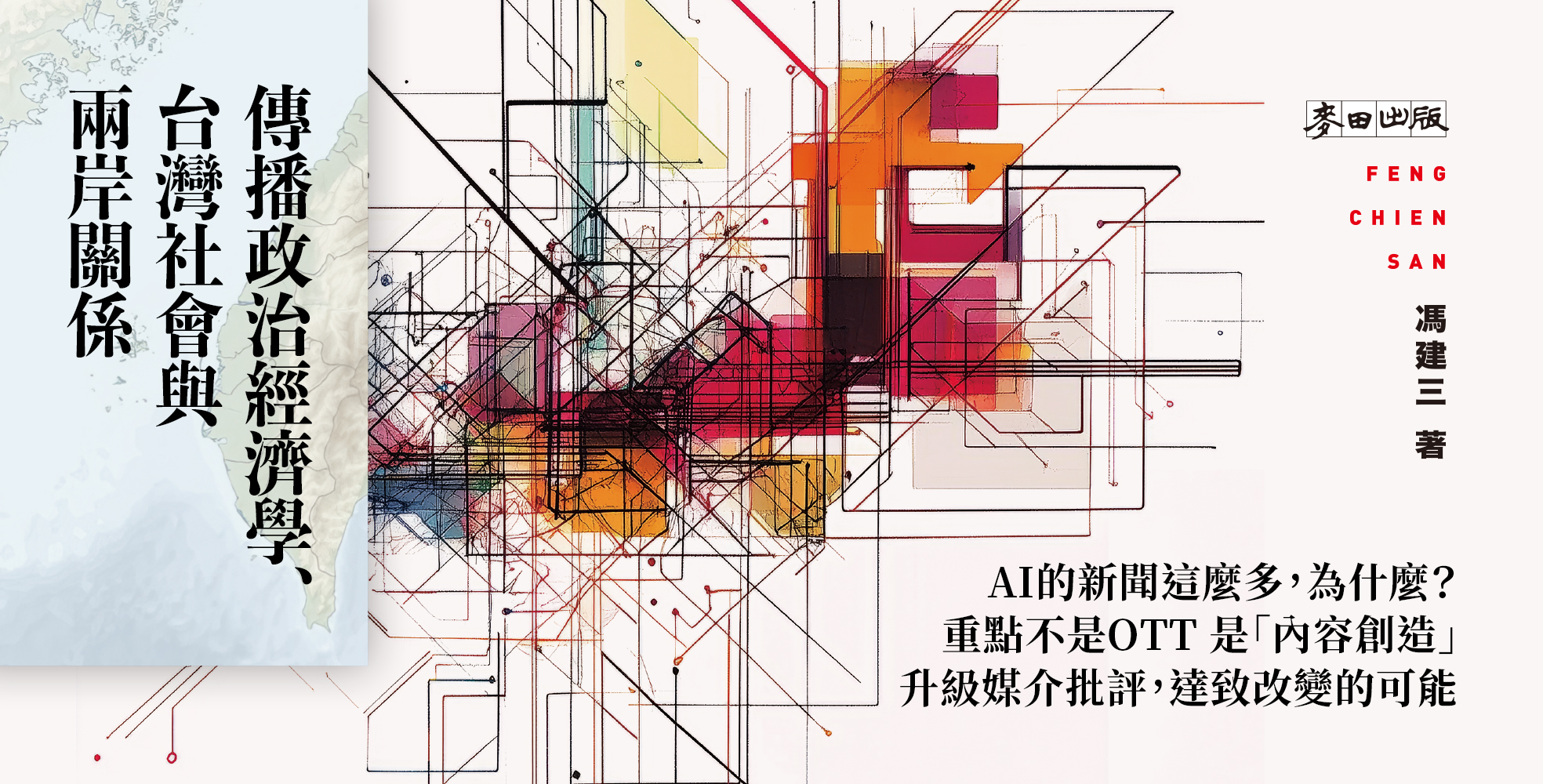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