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對那篇與書同名的散文〈遙遠〉念念不忘,感覺遙遠,卻印象深刻。文章裡面提到一個在香港緊湊行程之中,意外空出來的悠閒下午,坐在陽台上,看見了遠方的山海景色,突然產生迥異於以往的親密感受,又有些茫然飄忽的心境,於是將之坦然命名為「遙遠」的過程。這樣簡單的一種瞬間的體悟,被如許細膩且渾融地寫了出來,自有一種打動人心的魅力。
或許這種遙遠的心境,也跟閱讀寫作或生活相契吧。我甚至覺得這篇散文可以作為林文月總體風格的一種象徵,晴朗美好,使人鬆懈,但分明不是空洞的,那情緒是自內心遠處緩緩接近的。
記得某同事談到我的散文與詩時,曾表示讀我的作品使他感覺跟我很親近,矛盾的是,他又知曉並非全然如此。這種忽遠忽近的感觸,令我想到,他許是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入我的文字之間,使他更理解了自己,因而間接產生了更接近我的感覺;宛如兩面對看的鏡子,不斷重複投射,明明很親近,同時也有無窮多個影像之遙。
我一向喜歡親近的部分,但也不排斥遙遠。因為知道縱使是那些美好幽默的文章,背後也難免有兇殘暴戾的寫作過程。寫作的殘忍與痛楚,往往被作者以巧妙的技藝隱藏於遙遠的深處,不見得讓讀者知道,那些遙遠的存在卻是必要。
每個人的幻想國度裡都應有幾座遙遠的大山:遙遠生出美感,夠帥就會產生距離。戲曲界雖有俗云:「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然而就是此種遙遠,使想像有了品質,記憶有了風格;使人一生甘願勞碌痴迷,甚至免不得有想要夜奔梁山,思凡下山的激情時刻。
仔細想來,我不是那種需要一直變換自己的時空狀態,才可寫作的人;鮮少藉著旅行或流浪,以換取寫作的靈感。雖習慣於生活的規律與恆定,一旦察覺自己並非處於準備寫作的「正向什麼奔馳過去」之狀態,就會感到自卑或自厭。這也是一種來自遠方的驅力吧。
恍若被什麼遙控似的,寫作的動機大概就來自於這些遙遠而痛苦的想像之突襲,使我們在最歡樂的時刻也無法掩飾內心的莫名淒涼。當然,也每每藉此在一些處境情節與自己風馬牛不相干的小說或詩句裡,治癒了切身之痛。
真正不生不滅的事物彷彿都是遙遠的,我們一般人只能跟一些生生滅滅的貼身東西周旋纏鬥。即使是迫近的現實,也要情怯地訴諸各種對「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的興趣與詮釋,以產生一些多愁善感的詩意。
我們其實知道,事實真相往往是菩薩並無所謂菩薩心腸,天才難免有許多白癡之處。
這或許是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寧可飄忽生活著,被一片茫然的事物遙遠催眠,譬如中學時代的美好記憶或者相關的那些年的純愛電影等等,但卻不那麼樂意參加同學會或認真鼓起勇氣去愛戀一場……
唉呀,這篇文章果然也越寫越遠了。
〔林文月作品〕
鯨向海
精神科醫師,著有詩集《通緝犯》《精神病院》《大雄》,散文集《沿海岸線徵友》《銀河系焊接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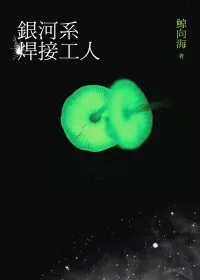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