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與勒嘎.舒米(攝影/ 汪正翔)
《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與勒嘎.舒米(攝影/ 汪正翔)
老人的太陽已接近海平線了,你的身影應加速學習山與海的情緒。──夏曼.藍波安
在《太陽的孩子》裡,那位站在田中央,揮著棕櫚葉,溫柔觸撫稻米的女人就是舒米.如妮(Sumi Dongi),亦是這部電影的起點。她發起復育港口部落的水梯田,奔走四年多,修復水圳,讓休耕30年的梯田再度揚起稻浪。她的兒子勒嘎.舒米(Lekal Sumi)拍下這段歷程,製成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當時,勒嘎.舒米還用著漢名王亞梵。

勒嘎.舒米從小跟著父親在台南生活,退伍後才回到港口部落,雖是返鄉,卻異常陌生,「明明在家裡,卻覺得自己像觀光客。」他是部落裡唯一的年輕人,無業而焦慮,他試了很多方式親近部落,最後的解方,是攝影。「透過鏡頭,拉近了我與部落的距離,算是認識自己和原鄉文化的一個媒介,也因此認識更多人。」同時,母親舒米.如妮正在為海稻米奔忙,他跟拍兩年,從原本玩票性質的紀錄影像,輯剪成《海稻米的願望》。
而對鄭有傑而言,認識港口部落與勒嘎.舒米,進而將紀錄片改編為電影,也像一個返鄉與尋找自我的歷程。他在這部素樸而簡單的紀錄片裡,看見自己的初心。第一次看《海稻米的願望》,他便被族人們堅持復育的精神與勒嘎.舒米的影像感動得淚流不止,「透過觀景窗,勒嘎.舒米其實在找自己,每個鏡頭都是他溫柔的凝視,那是發自內心真誠的愛,並且還在尋覓愛的位置。那就是他,沒有人教他,就這樣從土裡長出來。」
簡單的原味如同一記響鐘,敲醒了鄭有傑逐漸落失的創作初衷。「就像他離開部落,為了得到周圍的認同,漸漸忘記真正的自己。我的創作過程也很類似,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作品最真,而後為了得獎或票房,我漸漸追求更好看或更吸引人的東西,但已經忘記當初創作的姿態。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回去那樣的狀態。」於是,這部以人與土地的關係為主軸的電影,滿載了兩位導演對於自我的尋覓與挑戰,一切故事,從人開始。
 (攝影/ 汪正翔)
(攝影/ 汪正翔)
決定改編拍攝後,自認無法獨立完成此片的鄭有傑視勒嘎.舒米為合作的不二人選。訪談間,他們一人主述一人補充,節奏搭配得天衣無縫。顯然,這部片也在兩人渾然天成的默契下完成。鄭有傑說,「雖然我的經驗比較多,但拍攝過程其實一直在向他學習,一方面找回初衷,另方面,過去在都市拍片的經驗不適用於部落,他指引了這部片一些正確的方向。」鄭有傑不免擔心自己帶著漢人的自以為是詮釋部落的故事,從劇本開始,便不斷與勒嘎.舒米討論修改,「如果我自己拍,這部片可能會變得很悲情或帶點唯美,或為了賦予一些情懷而顯得一廂情願,雖不能說電影裡完全沒有這些元素,但至少,兩個導演可以設法平衡觀點,當我走偏,他可以提醒。」
原本並無明確分工的兩人,隨著工作開展漸漸磨合出各自的角色與定位,鄭有傑注重大格局,勒嘎.舒米則以部落的生活經驗對照電影中的各處細節,二者相輔相成,調理出舒緩的影像節奏。而所謂「生活細節」是什麼?勒嘎.舒米解釋,「例如,夏天的夜晚我們通常會在戶外吃飯和睡覺。我在意的東西看似渺小,但不可或缺,如果這部電影是一道菜,我就是裡頭的鹽巴。」
鄭有傑導的是電影,勒嘎.舒米導的是生活。
此外,片中許多情節來自部落傳統,比如阿公帶著孫子上山,並將獵刀綁在孫子身上,意味傳承。奇拉雅山(Cilangasan)是阿美族的聖山,百年前的族人為躲避清兵追殺在此躲藏。阿美族的年輕人必須在族中長輩的帶領下走一趟聖山。百年的歷史記憶在族人爬山走路、身體勞動的過程裡,一次次被重述傳遞。
勒嘎.舒米回憶起走聖山的經驗:「第一次爬山時有種感覺,也許以後再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走這條路,那根本不是路啊,是記憶。我其實無法獨自找到這條路,要爬過很多次,很熟了,才知道怎麼上山。但若不走,路就沒有了。」離開部落,離開了山與海,為求生計,原住民進入都市接受了漢人的邏輯與價值觀,有幸回到部落的勒嘎.舒米反省了剝離傳統的狀態,「那些對我們而言是『別的東西』,並不是自己的文化,當這個社會要求你去獲得成就,讀更多書,自然而然就會忘了原本的東西。」
《太陽的孩子》除了以復育水梯田為故事主幹,也涉及東部土地開發、主流媒體崩壞、鄉村人口流失、行政體系卸責等議題。然而,面對問題,本片要突顯的並非議題,而是活在其中的人。雖不免有抗爭場景,兩位導演卻拍得謹慎而節制。
面對如此正向且激勵人心的故事,鄭有傑有意識地避免過度激情,儘管他有足夠的元素將這部片拍成主角Panay守護土地、拯救部落的女英雄故事。「我知道大家喜歡看善惡對立、克服困難後幸福美滿的故事,但那是神話,我們想拍比較真實的故事,Panay沒有解救什麼,她只是在一個平凡人能做的事裡,盡力去試。況且,這裡的故事與人本來就很美,我不需要加油添醋。」
熟悉鄭有傑作品的觀眾應該會發現,《太陽的孩子》少了凌厲的技巧,多了些質樸的天真。除了靠勒嘎.舒米把關,「緩慢而鬆散」的拍片氣氛亦是關鍵。由於片中演員多是素人,為了讓大家進入狀況,兩位導演選擇以半紀錄片的方式拍攝,電影裡僅出現30秒的片段,其實都拍了兩個多小時。為了讓演員們更放鬆,拍片現場很輕鬆,直接紀錄,沒有人喊action,「這種拍法,絕對比只拍30秒好。還有一個好處是,會獲得你沒有想過的東西。」看似揮霍,實則必經的過程,這是兩人的堅持,「如果我們在這裡拍片,卻只追求效率與成果,那跟觀光飯店有什麼差別?」
如斯態度不只展現在拍片現場,開拍前三個月,鄭有傑便讓工作人員進部落租房子,過生活,交朋友,「一切要從交朋友開始。我們的確是為了拍片而來,但得先互相認識,講明白自己是誰,來這邊做什麼,認識之後,下一步再說。」

 (圖/牽猴子提供)
(圖/牽猴子提供)
電影最末,水圳修成,泉水流過土地,稻浪翻飛,《太陽的孩子》約莫是近幾年對於土地最為謙虛與虔誠的電影。在部落,所謂入境隨俗不只是跟著族人做幾個簡單的「儀式」,短短幾個月,鄭有傑的身體似乎已留在這塊豐美之地,「拍片過程中,我一直感受到一種對於大自然、祖靈的尊敬,當我們誠心向祖靈報告,祂就是在,那是一種感受,我只能透過身體去學習和體驗,而不是透過腦袋。」
電影完成後,當初仍以漢名發表紀錄片的勒嘎.舒米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在各地宣傳時,他總說:「這部片希望喚起人們對於土地價值的重新思考,復育的不只是梯田,而是人心。」在山河海水之前,除了吶喊與爭奪,我們還有什麼方式成為一個人?或許,這就是《太陽的孩子》最溫柔的提問。
《太陽的孩子》,9/25(五)上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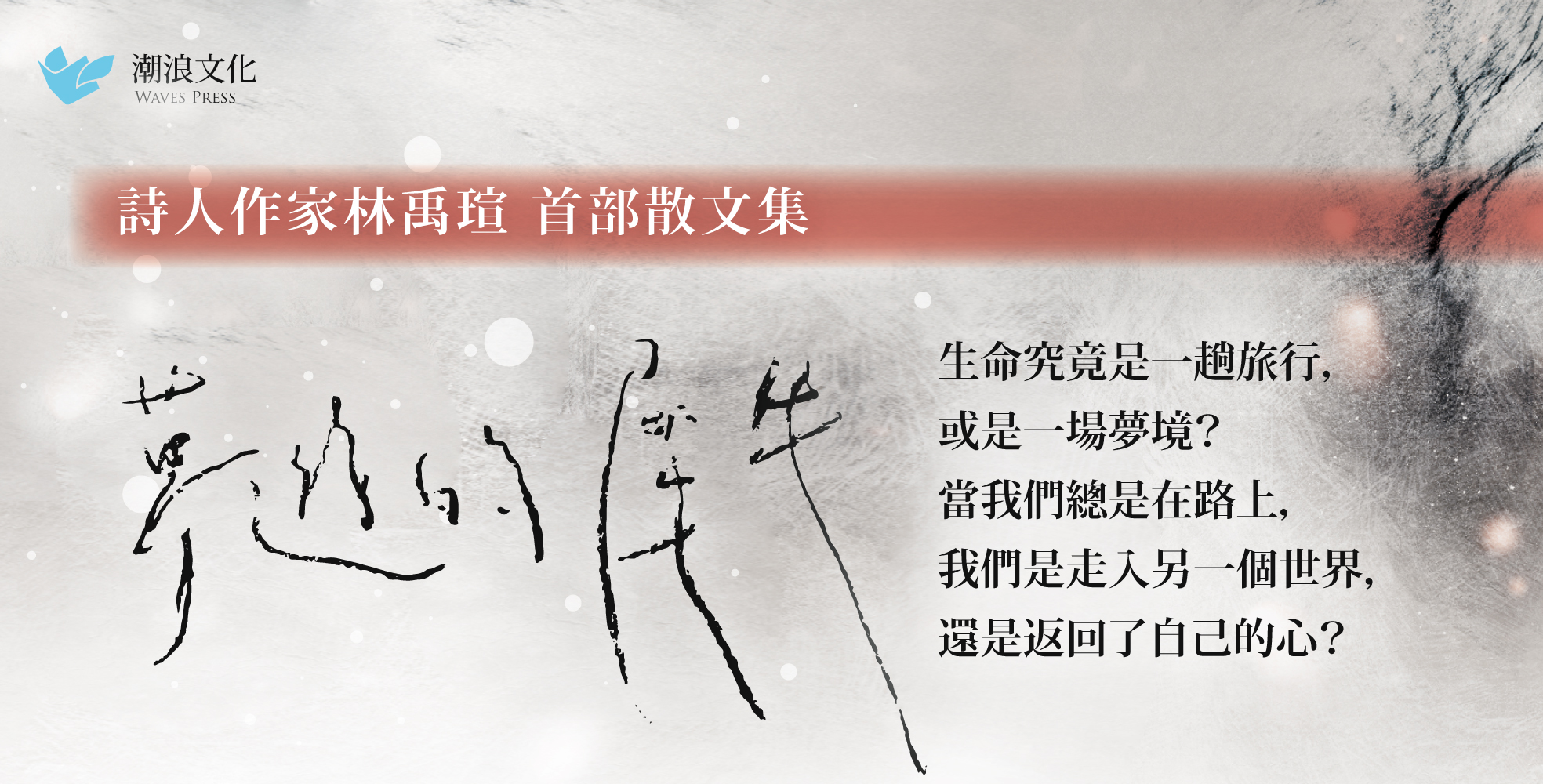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