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蕭如君)
她雙手捧茶,眨著杏眼,談吐溫美,但句句銳利。她是馬欣,吐字維生多年,終於率著一批經典電影中的反派人物,僕僕而來,成書問世。《反派的力量》乍似影評選集,揀擇了一個另類的角度切入經典,實際上是她對於現世的掏心書寫,一篇又一篇反派小傳,實是借他人故事想自己心事。
馬欣是入戲的觀眾,迷而不痴,此書的寫作初衷來自幕中人所勾起的同心共感。《黑暗騎士》的小丑與《嫌疑犯 X 的獻身》的石神哲哉讓她走出影院仍無法釋懷,只能下筆。馬欣說:「我認為小丑不只是一個反派人物或單一角色,而是一個群體的現象,也是目前社會的某種縮影。小丑代表的是一群落單的人,一群被我們以『進步』之名甩掉的人。他們的悲劇沒有娛樂性,也不被關注,我對於這樣的人一直有想寫的欲望。」「另一個角色是石神哲哉,我看完電影後坐在位子上不斷流淚,石神實在太孤獨了,連自殺都像在選擇菜單。這兩個人物讓我動念想寫,也就一個個寫了出來。我希望不被看到的人被看到。」
虛構固然動人,總得以現實為基底,而引動如此反思與觸發的關鍵其實來自馬欣在採訪工作中碰到的年輕人。他們在演藝圈、電影圈、音樂圈努力拚搏,無論幕前幕後,驚人的流動率與淘汰率反映了此輩工作者的挫敗與失落感。而這些觀察讓她升起濃濃的負歉感。「我是五年級後段班的,還接續著四年級的希望,雖然我們可能已是失落的一代,但八、九年級生面對的是一個更失落的情況。他們看到前人的路已走到盡頭,必須轉彎了,但卻沒有任何範本可供指引。其實我們早已預見這樣的結局。我們在一個經濟發燒的時候成長,擁有各種資源,長大後卻發現所有價值都被空泛化,所謂成功的價值都被架空了。」
「面臨這樣的交叉路口,他們面對的是沒有辦法補位的混亂生態,我認為,精神上格格不入的狀態以及失怙感必須被提出來,我們也曾經如此,生存考驗十分嚴苛。我希望讓他們知道自己是不孤單的;另一方面,所謂的幸福和成功不應該是現在被宣傳出來的模樣,如果一直循著前人模式的話,可能沒有辦法建立自己人生的價值,如果可以重新思考幸福和成功的定義,或許可以快樂一點或清醒一點。」於是,馬欣對著年輕人叨叨訴說,說著資本主義的不義,現代社會的土崩瓦解。這或許正是她身後的反派們所能帶來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難得出現的幾位美豔反派也讓馬欣提出了念茲在茲的大哉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美到底是什麼?「女生常用自己的身體來明志,明明已經循著訂單走了,還是沒辦法到達美麗的人生,便把身體廢墟化,對幸福好像有強迫症,把自己的身體變成樣品屋,各種醫美選項那麼多、打扮方式那麼多,女人根本就沒有不美的權利!但『不美』是什麼?美麗早就被限定為那四、五種標籤,妳只是在自己的衣櫥裡角色扮演,以為如此扮演就可以獲得成功或幸福,這只是一個把自己虛構化的過程罷了。」

(攝影/蕭如君)
這本書其實難以歸類,馬欣到底還是在寫人。當這些角色下了戲,她彷彿尾隨在後,觀察他們的生活,觸撫她們的呼吸。「我想寫出他們沒被拍到的生活畫面,想像他們下幕後生活的模樣,一幕幕寫出來。」而如此將人當成文本閱讀的能力或許與她小學時的經驗有關:貴族學校內的階級差異讓她提早見識到人性的微妙反應,馬欣回憶:「我念的是貴族小學,同學和老師間會有一些化學反應。老師好特別,看到黑頭車的表情會很複雜,興奮、猶豫、厭惡。我那時就覺得人很有趣,他們的表情都不是單一的存在。」當時,小馬欣幾乎不和人互動,被學校老師懷疑有自閉症,老師管不動,便要她罰站,「可是我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樂趣──就是觀察校園的生態,其實那時並沒有察覺到自己是在觀察,我看著花草樹木旁的一群螞蟻的行走速度或是群聚的過程,好有趣喔!」如此自顧自地生活,當然免不了被排擠霸凌,度過一兩年悲慘的校園生活,小馬欣竟在《蒼蠅王》中找到解方,「當我看完外公書櫃上的《蒼蠅王》,突然覺得一切都豁然開朗。原來社會入門課程是這樣,我學會跟意見領袖交朋友,讓成績排名在中間,這樣最安全,也能保住『觀眾』的位置,保持獨處。」
獨處、觀察、閱讀一直是她創作的資糧,在《反派的力量》中也常見馬欣信手拈來各類文學電影中的名言佳句,得以想見她龐大的閱讀量,「閱讀是我的生活習慣。在我成長的年代,重慶南路還是一條書街,我很幸運,當時的台北有這個資產,是一個鼓勵閱讀和聽音樂的環境。現在只有商場沒有書店了。」馬欣書寫不輟,樂評、影評、人物專訪散見各類報刊媒體,她嫻熟於文字工作的生產流水線,而這本書是難得可以兼得創作與營生的成果。「我的寫作狀態大概就像一個土撥鼠,搜糧囤食然後窩進地洞開始打字。」挖掘地洞,翻鑿人心,馬欣在穴中寫著人心的暗面,其成果卻也帶出清亮的思考與溫暖的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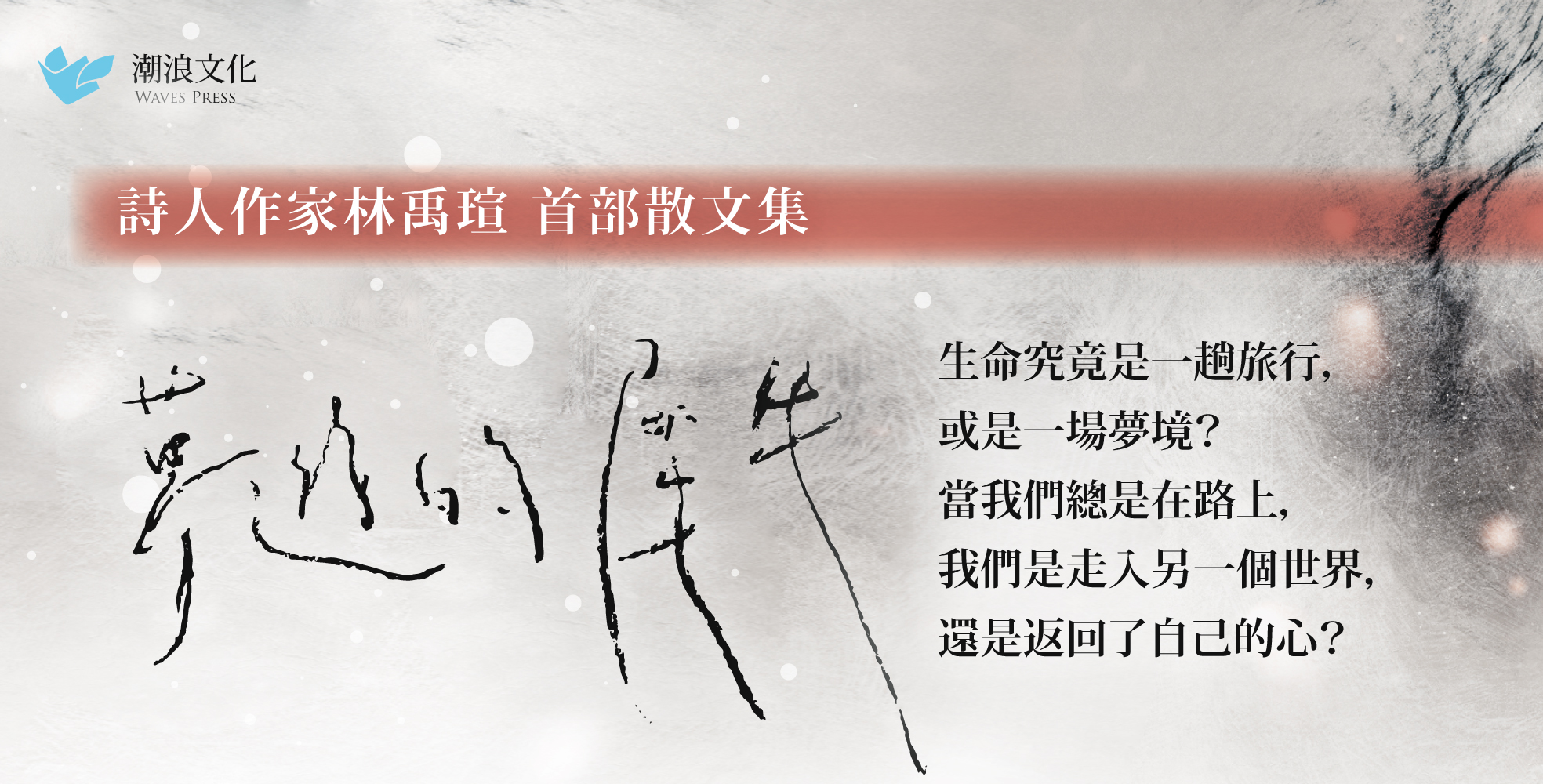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