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開任一本具有30年以上歷史的書本,都可以在紙頁上感受到鉛字印刷留下的獨特壓痕,那是老一輩讀書人指尖最初的記憶。在《活字:記憶鉛與火的時代》中,透過鑄字、檢字、排版、印刷之職人深度訪談,讓我們看見活字印刷術歷史的縮影。
原來,知識的傳遞曾經必須經過這麼多雙手的努力,但是關於活字印刷的故事及回憶,實在少有人談論起。這次特別邀請張嘉行、嚴韻、陳允元、黃哲斌,聊聊他們的活字回憶,希望可以透過文字,一起將那個美好年代慢慢拼湊。
文╱陳允元
詩人、政大台文所博士生、中文系兼任講師
小時候,我的房裡有一架淺綠色的中文打字機。金屬製的,沉穩厚重。領先風潮30年在大學讀韓文系的老媽,婚後為了在家照顧孩子,便把工作辭了,也接些家庭代工補貼家用。其中做得最穩定的一項,便是中文打字。每隔幾天,接我放學時她會順便繞到國小附近的米店兼小印刷行拿稿。老媽偶爾必須在夜間工作。打字機旁的那盞黃色桌燈,便成為我的夜燈。打字的聲音並不吵。聽老媽一個字一個字敲,很快就睡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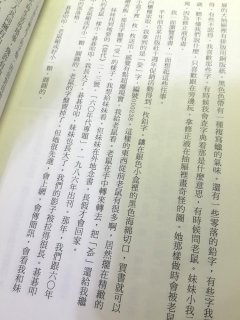

在老媽打字的1980、1990年代,活字印刷已經式微,打字照相印刷也即將走入歷史。房裡的那架打字機,在搬家時賣掉了。當它被時代淘汰之後,或許曾一度還原為金屬的形式,然後被製成另一件東西。
2010年,偶然知道行人與「日星鑄字行」的張介冠先生合作一場鉛字印刷的介紹活動,我便去了。當時我有意將自己十年來的詩出版,看著張先生的印刷示範,心裡震動了起來。儘管有些冒昧,還是向前詢問鉛字印刷詩集的可能。我與行人總編輯周易正大哥談起小時候的鉛字接觸,周大哥有些訝異,說他讀過我那篇文章,便邀我到社裡聊聊,後來也促成了詩集《孔雀獸》的出版。想使用鉛字印刷,固然是為了視覺與觸覺的感受;然而「鉛字」於我而言,更是生命之初對「字」的接觸:它是堅實的、可碰觸的,能夠在指頭上壓出痕跡的。它也是有節奏的。在燈光下一個字、一個字被選取、叩擊在壓紙捲筒,發出爽落的聲音。這樣的節奏,讓我安心。詩集的印製,由於考量了製程與成本,終於沒有採用夢想中的鉛字印刷。然而成書的過程也花了點心思,希望能保留一些有「人」經手的痕跡與溫度。

我研究的現代主義詩,其實相當倚賴印刷技術。有趣的是,出版萩原詩集的龍舍書店並非文學出版社,而是出版獸醫專門書籍的出版社。對於配置許多圖版、運用各種印刷技術的《死刑宣告》而言,這樣的合作是必要的。此外,據說印刷師傅中有相當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由他們來協助製作無政府主義者萩原的詩集,可謂理念與相合;若非如此,我想,面對這麼脫軌破格的視覺設計,排版師傅大概會排到眼睛脫窗、暴躁如富士山噴發吧!
幾天前圖書館通知我取書。興沖沖去,卻發現這個版本的復刻方式,與台大那冊大不相同:由於原版的誤字、誤植相當多,此一復刻僅在排版、圖版上根據原版忠實呈現,文字則經學者勘誤修訂並重新打字。這樣的「準」復刻本,對於閱讀者或許較為友善,然而在1925年印刷師傅拚死製作、隱隱浮現紙張質地的版畫,以及鉛條壓印的罫線之中,配上過於清晰準確(而文弱)的電腦印刷字體,整個畫面有種說不出的違和感。我一面翻閱,皺起了眉頭。
鉛字印刷其實也是版畫的一種。字的鑄造、墨與紙面的接觸、按壓,以及蘊藏於製程中的細節及種種變數,是鉛字印刷最迷人的地方。我們閱讀,並不只是通過文字、得到資訊,以之為橋,過河即拆──事實上,我們經常忘記讓文字成為可見、可流通的物質基礎。文字不過是行駛於橋上的車流。印刷工藝,才是真正負載文字、穿越時空限制,接連人與人心靈甚至共同體想像的堅實橋體。橋的本身是一件工藝品。與周遭的山水、城市、人物,共同構成一面值得被眺望、被記憶的有橋的風景。

★延伸閱讀:
【我的活字回憶|01活字復刻工作流程】張嘉行:讓活版印刷重新回到現代生活
【我的活字回憶|02鉛字組版的時代】黃哲斌:打翻鉛字架
【我的活字回憶|03何謂鉛、字、活、版、印、刷】嚴韻:鉛字活版印刷——解字說文
【我的活字回憶|04活字印刷出版實錄】陳允元:我們經常忘記讓文字成為可見、可流通的物質基礎
鉛與火之歌——專訪日星鑄字行張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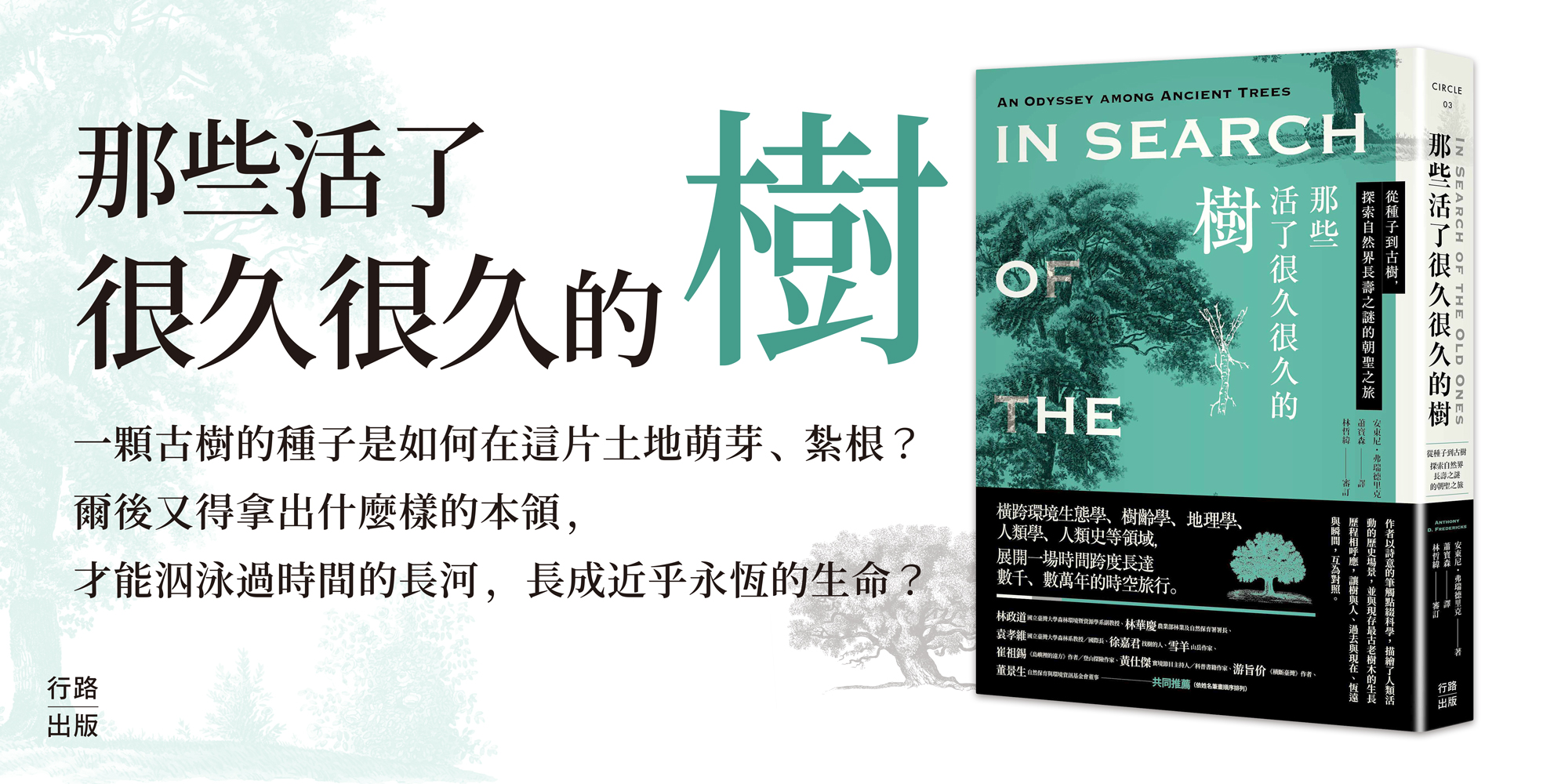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