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黃暐鵬
Q1. 回顧今年的書籍裝幀設計,讓您印象較深刻的3本書是?
王志弘《決鬥寫真論》《1972青春軍艦島》,臉譜出版。
這兩本是我私心認為,王志弘2013年完成度最高的作品。甚至於他其他的封面都無法放在同一個高度來討論(以至於我只能選出兩本來)。基本上,對王志弘這樣嫻熟的老工匠來說(「老」是讚美,意思是經驗豐富、從事這項工作多年。「工匠」也是讚美,我的意思是手作職人,但這四個日文過來的漢字,現在用來有點矯情,工匠是一個更誠懇樸實的形象,彷彿他人就在自家門口打鐵,或巷口的小攤煮麵),技藝已經不太是問題,做到一般所謂的「(世俗)美」或取悅觀看的人(不管是讀者還是客戶)並不難。當然他可以往更純粹的方向發展,譬如,做出「恰如其分」的設計,做出「適可而止」的設計,做出「不過度設計」的設計(這個我們等下再討論)。他也可以往更具表現力的方向發展,像是發展出自己的設計詞彙來。(例如2012年的《幽談》)
但他設計出《決鬥寫真論》。這不是一個「美」的設計(絕對、絕對、絕對不會有人看著這封面說「好美哦」、「美到太犯規了」),但也不是醜。用我自己的感覺,它是讓人困惑的設計。我自己的職業也算平面設計(大概吧),日常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判斷什麼是美、什麼是醜:這字體用在這邊是美還是醜?這顏色是美還是醜?這元素擺這裡是美還是醜?我們看著公家機關做出來的文宣然後爆笑出來的誇張地說噗哧好醜喔,很開心;我們看著別人做得很好看的作品然後說好美喔我怎麼做不出來,很哀傷。用中平卓馬自己的話就是,「影像被放置在語言中間,被語言圍繞,……我們不會因意識的攪拌而感到不安——影像被命名,我們因此感到安心。」
被命名的東西讓人安心,被歸類的東西也讓人安心。意識沒有被攪拌時,也就是我們忙著在幫眼睛看到的東西歸類(或命名)時,「好看」「醜」「好看但不是我的菜」「醜而且醜到爆炸」,我們安心。命名/歸類完之後,就不用再去多看它一眼。(當然,如果是同行的話,大概會再多看兩眼研究琢磨)。但令人困惑的東西,會使得觀者不知所措,「這,到底是什麼?」。令人困惑的影像是難以製造出來的,令人困惑的設計則更困難。但我稱讚它並不是因為成就上的困難,而是因為困惑的東西是好的、挑戰日常的、讓我們稍稍恢復「純真的眼睛」,我們並不是看了一眼把它分類命名之後就丟掉,而是很仔細的打量,這到底是什麼。
但令人困惑,不代表作品本身是曖昧的、模糊的。模糊的影像本身只會立即被歸類,這是模糊的,而不是令人困惑。困惑的影像,得走在那層無法想像(及形容)的薄膜之上。就《決鬥寫真論》的封面而言,它令人困惑,但相反的說,它卻很清晰。書名是(以王志弘的標準而言)罕見的大,非常簡單的幾何線條,繼承了王志弘某條姑且稱之為「我用Word也做得出來(哼哼)」的路線(例如2012年《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2013年《幻城》)。它的元素安排、空間使用,並沒有設計師向來擅常的巨大的、巧妙的留白而製造出一種美感(如2013年《海海人生》),它稱不上刻意留白,也談不上巧妙,就只有……困惑。搭配毫無修改就放上去的電腦字體,完全沒有任何美術字或手作的痕跡。不只字體沒有痕跡,連其他的視覺元素,個性也很薄弱。
沒有痕跡,這又是另一個重點。「去除作者的痕跡」「接近匿名狀態」這些概念,中平卓馬在《決鬥寫真論》中(及其前作《為何是植物圖鑑》,Source書系即將出版)談了很多次,啃不下整本書的人,或可參考張世倫此篇書寫中平卓馬的大作。但我們得思考的是,攝影這項藝術,它在本質上更容易達到中平卓馬所謂「被動」的「接受體」。但什麼是「被動」「接受」的設計呢?設計本身是項「主動」去安排的動作,設計師是無中生有的人,從一片空白中創造出東西來,就平面設計來說,是在一張白紙上把所有的元素安排上去,即使再怎麼單純的設計,還是有著大量的主觀判斷在裡頭:元素擺放的位置、字的字級、字體、顏色、與空間的關係和比例、印刷工法,等等。或許是因為我不懂攝影的關係,總覺得設計這樣的動作,要更難達到中平卓馬追求的境界。事實上,《決鬥寫真論》的封面,並不是一個單純去除作者痕跡的作品,它雖然看似隱藏個人風格,卻又往極為大膽的平庸那方向擺盪過去。也許是設計這行為(相較於攝影)本質上的困難,使得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匿名狀態,反倒自己成了強烈的風格。
在這裡有個很有趣的案例,王志弘設計的《幻城》(2013)英文版內文,原始手稿是王大閎先生於各式各樣的回收廢紙背面空白處打字的。王志弘做了一個極為主觀的設計判斷,他將原始手稿幾乎原封不動的按順序收錄起來。這個極為主觀的決策,卻使得這本內文成為他最不摻雜設計師個人情感和意見在裡頭的作品,也是最接近「被動」「接受」概念的設計作品。
當然大部分的設計案都沒辦法這樣處理,但中平卓馬在評論攝影時所發展的美學觀點並不是單一個案,在20世紀後半的美學(及文學)發展中,不斷可以看到類似的聲音出現。由於全然的匿名、消除作者痕跡、或作為被動的接受體對設計都非常困難,所以設計界自己摸索出來的道路是,「unobtrusive(不顯眼)」、「understandable(可理解)」、「honest(誠實)」,以及「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盡可能不設計)」,以上是工業設計大師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於設計十律中提出的。或者,用另外一個字來說,是「inevitable(無可避免)」,好設計是無可避免的,也就是,當它出現之後,我們會覺得它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以上,是工業設計的看法。(當然,工業設計發展出這些看法有其脈絡和泉源,包括對19世紀以來到20世紀初期強烈裝飾性的反挫,包括30年代包浩斯學派及後來烏爾姆對於設計「經世濟民」的想像,包括20世紀中業建築上國際主義的「普世大同」理想。但這是後話了,姑且按下不表)。
至於平面設計怎麼看待這事?一個可能的答案是王志弘的《1972青春軍艦島》。創作者本人已經花了幾百字說明背後的思索過程。仔細看他的用字,「預設將與軍艦島有關聯的色彩和物質,作為選擇紙材與印刷加工方式的基礎依據」、「軍艦島上的住宅規畫有些雜亂,不禁讓人聯想到舊住宅區裡常見的違章建築,我想透過文字的特殊安排來呈現這一個想像」、「編排與準確度上也盡可能降低設計慣性,更不依靠參考線……心想當文字出現在島上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時,可能會用多麼隨性的態度去擺設」、「將文字的意義直接當成形象來看待,把書中既有的作者手繪地圖、關於軍艦島尺度的標示數字,直接移植到文字上」。不顯眼、可理解、誠實、盡可能不設計、無可避免……是不是有共通性?
從《幻城》(因素材特殊而容忍)的全然被動呈現、不加修飾,到《決鬥寫真論》的曖昧、尋常、匿名(及其帶來的高度風格化反效果),最後是《1972青春軍艦島》的對主題誠實,而造就了理所當然的設計。我覺得這是王志弘在2013年以實踐來思考「設計是什麼」這問題所產生的回答。最後再度引用中平卓馬的話,「……阿特傑(Eugene Atget)的成功,在於沒有創造任何影像,反而能呼應世界與現實;……但是對於『已經知曉』太多的我們而言,是否還有達成這個境界的可能呢?我想除了把自我捨去、從原點再出發以外,別無他法了吧。」
Q2. 您今年設計的書籍裝幀作品中,自己最滿意的3本書是?
1.《藍色的靈魂》,麥田。
2.《幻影之星》,野人。
3.《獵頭遊戲》,漫遊者。
選這三本書並不是因為它們特別突出,突出到可以從我2013年的作品中跳出來、超越其他作品的高度。而是因為這三本之前沒有在OKAPI寫過,但我覺得它們各自還蠻有意思的。
(書籍)設計常做的事就是操弄和組合,譬如,操弄一張圖庫裡買來的照片,讓它變得比較上相一點,然後配上書名等訊息。也不一定要有素材,設計可以無中生有來操弄。這三本各自操弄了不同的東西,《藍色的靈魂》只藉由操弄線條和色彩來創造畫面,或者說,它就是「造形」的過程,我創造出一個形狀來。《幻影之星》是另一個極端,這小說的內容極富哲學性和思辨(應該說,作者白石一文的東西皆如是),含義深遠,很難用單一的形去表達,於是我選擇的作法是,用書名(的文字)來指涉這本書內身,然後去操弄文字,用那個操弄文字的結果來表達書的內容。《獵頭遊戲》則跟前面兩本完全不同,它操弄的是現有的圖像,但跟一般常見的照片不同,它是以插畫為素材,說穿了很簡單,但效果很好,有一定的商業性和討喜,而且極富黑色幽默感。幽默並不是一個台灣設計常見的元素(相對於,譬如,假掰、文創、人文味、手感、溫度、氛圍、等等所有你可以想到的髒字眼),黑色幽默則更少見,它並不是一個可以靠裝腔作勢呈現出來的東西,它需要一些……世故、嘲諷,也就是對世界的理解和無可隱藏的敵意(但又不得不妥協的生存下去),或許這是它難的地方。我很高興我能做到這點。
當然,對於這三本我都很高興,它們在讓案主滿意的同時(喔,這是最難的。特別是我沒有拿刀子架住對方的脖子強迫人家接受我的提案)(嗯,好吧,我其實常常想要做拿刀子架脖子這檔事……),也讓我嘗試了一些新東西和作法,至少2013年過去了,我知道自己有些微的成長和進步。
Q3. 今年的設計工作,您遇過最慘最瞎的事情是?
其實我沒遇到什麼很慘或很瞎的事。(好吧,其實有,但我不會在這裡說出來的)。但如果這個問題拿去問我的案主們(包括,呃,OKAPI在內?),他們可能會把我的拖稿列為年度最慘最瞎的事吧……(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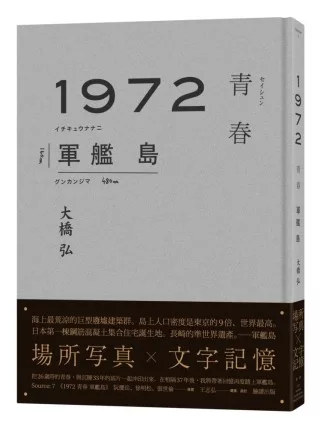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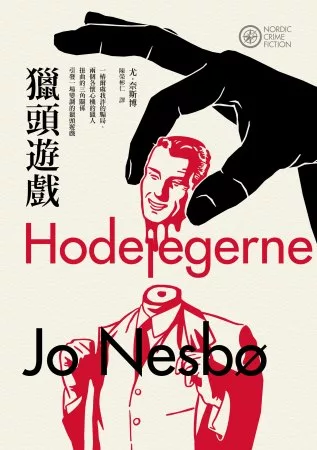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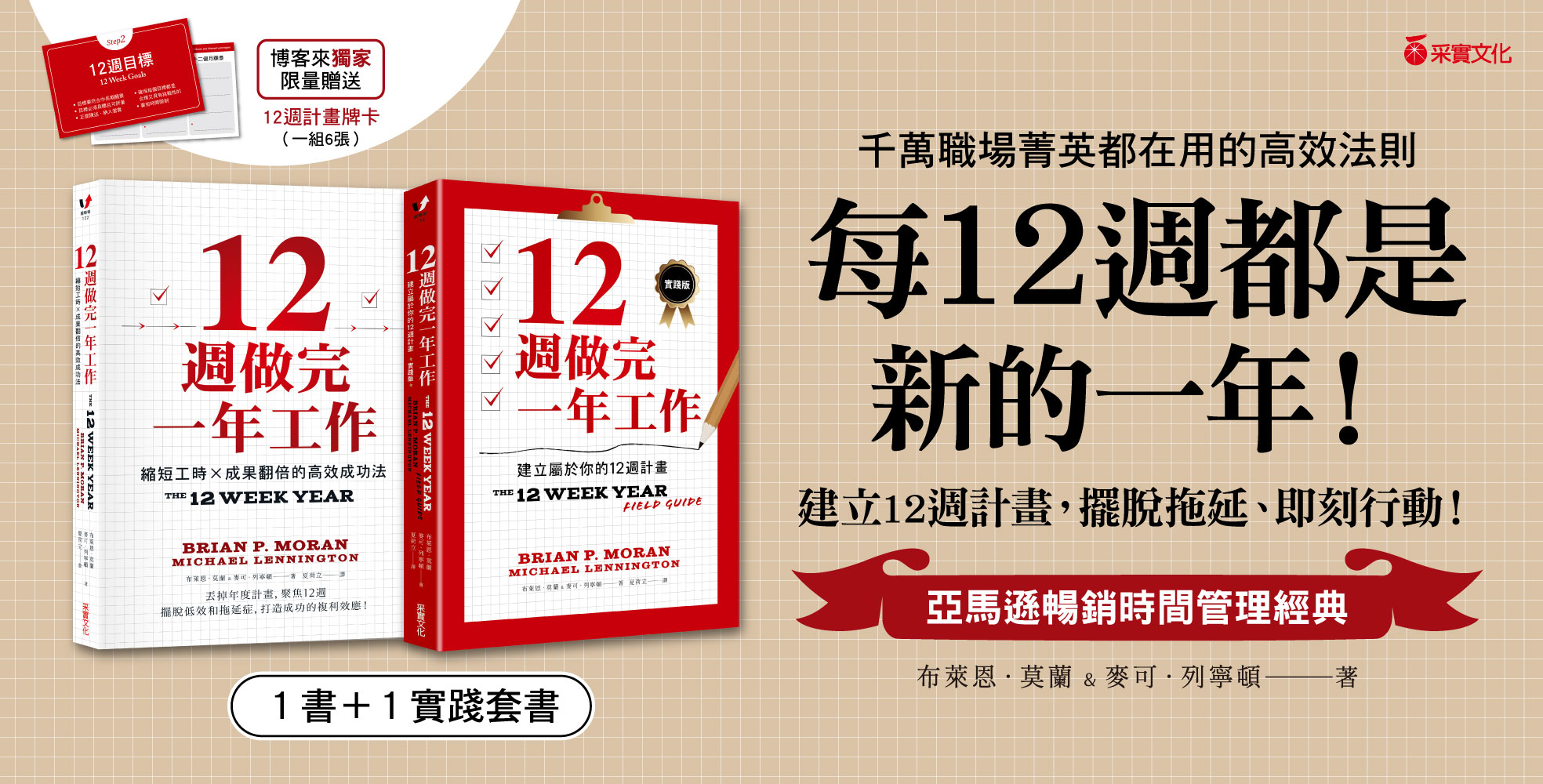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