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站在柏林「Tierpark」動物園深處一個室內獸欄前,籠子的格紋異常的細密,可以看出這裡是猛獸區。但即便必須穿過那麼密麻的籠網,我依舊能清楚分辨出籠子裡動物的斑紋,那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又脆弱無比的美麗毛皮,在野外已經滅絕的台灣雲豹,在這裡竟是帶著新生兒的一家三口。
雲豹新生兒完全是一隻頑皮小貓,牠野心勃勃地要媽媽看著他爬上最高的樹幹,伸出短小前腳往上攀,懸空的後腳揮了兩下,又掉落回媽媽的懷中,迷惑不解為何自己不會飛呢?雲豹媽媽看起來非常睏,但那孩子似乎沒有罷休的趨勢,依舊上下左右探索著這小場地的無限可能,孩子的爸早已占了一個舒服的角落熟睡去了。

(攝影/何曼莊)
我站在那裡不知道過了多久。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對來自法國的少年情侶、一個坐在輪椅上的柏林市民與陪同他的動物園志工,過了一會我發現其中一個人正在流淚。來自世界不同角落毫不相干的幾個人類,在這幾分鐘之內,同時不由自主地看著豹的小動作出神,沒人說話,怕一點點聲音便破壞了這份安詳。也許在無可測量的自然力量中,這只是平凡無奇的居家景象,但對於物種本身來說,生命的延續竟是那麼困難。
「Tierpark 」(德語:動物公園),是在前東柏林占領時代建立的動物公園,是歐洲占地面積最大的市區動物園,也是一個美麗的景觀公園。在設計當時已經20世紀中期,柵欄和圍籬等讓觀眾覺得「於心不忍」的設備已經過時了,所以在Tierpark裡,動物能悠閒地享受當今世上最奢侈的東西--空間。
電影《再見列寧》的故事發生在東西德統一的那一年。
醫生:以你母親的病情,她不能承受任何刺激。科納先生,任何刺激都不行,我告訴你。
Alex::任何刺激都不行。
醫生:對,否則會要了她的命。
Alex:像是東西德統一嗎? (拿起報紙頭條)你管這叫做「刺激」嗎?
Alex的母親將一生奉獻給東德黨國,為了不讓昏迷後甦醒的母親知道熱愛的祖國已經不復存在,Alex和夢想成為導演的好友費盡心思搬演一套東德日常生活大戲:製作假電視新聞、雇用小孩演唱「少年先鋒隊」之歌、製作假批文讓母親審閱……,而現實世界裡,倒下的柏林圍牆成為世界最大的紀念品供應站,東西德人民對於久別重逢無不歡欣雀躍,言論自由降臨,人手一瓶可口可樂、半倒公社和廢棄舊樓怎麼拍照都有氣氛,自由市場機制席捲全歐洲,所有城市土地價格都在翻倍,團結德意志的花綵開始褪色,失去文化根基的東柏林人開始緬懷過去。
才不過幾年前,我到過柏林,那個時候,柏林是居住成本最低的「西方」都市,來自歐洲各國的年輕創作者蜂湧而至,每個人都口袋扁塌,卻又精力旺盛,在廢棄的哥德式教堂裡徹夜狂舞,到了早上,用啤酒解伏特加的宿醉。那個時候的柏林,慷慨的給予窮酸青年寬敞的空間,居住、遊樂、戀愛、以及偶一為之的--創作。
那時的租房仲介會告訴你:從事創意工作,具有藝術氣息的你,應該住在生活機能良好、居民品質整齊的西柏林,而遊玩、吸取養分、與朋友相聚,則到充滿強烈性格的東柏林,在柏林圍牆將城市一分為兩個世界的年代,東柏林的形象深沉而憂鬱、悲傷又陰暗,而在圍牆倒下後,歷史包袱成了渾然天成的藝術景片,輝煌與創傷隱藏在那些史達林式建築中庭的角落。柏林的衰敗之美毫不保留、喜怒帶有血肉、這裡崇尚冷酷的性感、石板路面的間隙中總有尖銳的碎玻璃,住在現代東柏林,每一次夜歸,走上樓梯迴廊之時,你會不禁背脊一涼,站在轉角那片摸不著底的黑暗中的,究竟是《慾望之翼》那個穿著黑大衣的天使大叔,還是皮笑肉不笑的情報密探呢?
不久以前告別人世全球緬懷的搖滾巨星Lou Reed在1973年也發行了一張叫做《Berlin》的專輯,這是一張陰沉又實驗性強的概念專輯,暗黑搖滾歌劇的每個小節都在考驗聽著的精神強度,內容則是一對毒蟲鴛鴦的絕望宿命,既浪漫又暴力,歌迷無不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應,只好含淚痛斥。
那時的Lou Reed,才不怎麼好看地離開了樂團「Velvet Underground」,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參與的黃香蕉封面專輯將成為史上最重要的搖滾作品,還將會有某位歌迷聽了那張專輯,以後一路崛起成為捷克總統。那時的他只是酗酒又吸毒,剛與第一任老婆結婚,夫妻倆經常互揍,他沒選擇地帶一票菜鳥樂團上路巡演,直到他在途中fire整個樂團,然後他還跟David Bowie吵架。
而且,其實那個時候,他根本還沒去過柏林。「Berlin」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概念,像藝術家不得不面對自身的陰暗面,柏林,它能吃掉一個人,也能讓一個人重生。《Berlin》這張專輯不但賣得差,樂評也不支持。〈滾石〉雜誌將之評為「一場災難」,不過六年之後,同一本雜誌則修正評語為「浮誇、頹廢」、「史上最令人沮喪的專輯之一,以一種可怕的姿態展現奇異之美」,可能是因為那一年Lou Reed發行的爵士專輯《The Bells》太棒了,於是樂評也突然理解了《Berlin》的好。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的成立,是東西柏林正式走上政治分裂45年的開始,火車站旁的百年老柏林動物園劃入了西柏林。那一年在東柏林,軍警人民一體地展開「全面清掃普魯士封建主義」的工作,第一條社會主義道路,卡爾馬克斯大道恢宏橫越東柏林,1953年,蘇聯坦克大隊駛過這條馬路,平息了第一波大規模德國工人運動。兩年之後,在這條路東向的盡頭,「Tierpark」動物公園開張了,作為與西方對抗的象徵,它別具意義。不像百年老柏林動物園那樣帶有許多封建建築成分,東德建築師在人去樓空的皇家園林裡為全體人民設計休憩場所,「Tierpark」的動物住在人造岩石和瀑布等界為貼近自然的環境中,中央大圍場上綠草如茵,取代鐵絲網的是運河和樹木,所幸那些從帝制時期就生長著的樹木存活了下來,經過學者研究,蹄類動物與鳥類混合散養在大圍場的草地上,奔跑起來通體舒暢,看的人也開心。就像東柏林人民在團體生活中實踐共同理想與信念,「Tierpark」裡的動物們也過著很有紀律的團體生活,在人造的自然景觀中遵照飼養員的時間表進餐,為了避免失去天生野性,在科學家規劃設計之下從事行為豐富化的訓練。

(攝影/何曼莊)
在2012年的一個六月早晨,我睜開眼睛,直視著窗沿一絲不苟的九十度直角,提醒我已經來到嚴謹與務實的國度,如果可以跟神借來一組三角板,相信他們會連雲層的形狀都規定好。在柏林公寓裡暫住,即使初夏已經到來,兩尺半高的天花板令人望之生寒,和高聳筆直的四面大窗擺出冷冽氣勢,懸掛而下的燈飾簡約而輕盈,用的是省電燈泡;裝設在房內廁浴分離的洗浴設施潔白如新,聞不到一點異味,轉開已被數十年指紋撫摸溫潤的黃銅門把,行經綠色、棕色、透明玻璃瓶分類收集的酒瓶回收區,對街餐廳裡穿著圍裙的男性侍者將餐具水杯對準了桌布的格紋。公車行經「Tacheles」,這個曾經在富豪、軍人、納粹手中流轉,最後被龐克藝術家占領了20年的公社,也終於完成了「和平轉移」,正靜默地準備脫胎換骨,成為提升城市土地價值的重大功臣,我環顧四周,書店、攝影概念館、藝廊、設計工作室、創意商品店、咖啡館,一一睜開眼睛迎接美好的一日,過去的傷痛與陰影似乎從未存在過。回望那些現在已經斑駁的黑白影像,那些破敗的樓宇和整齊劃一的閱兵場面都成為一種距離以外的異國風景,明信片三張5歐元,超過則必須殺價。
「Tierpark地鐵站」是現存唯一由東德政府建造的車站,走上地面時,嚴整四方的大型集合樓房上,緊密排列的數百扇窗戶,在這周間白天的壓倒性寧靜之下,顯得十分寂寥,超市前方廣場上有半歇半起的市集,麥當勞餐廳裡老人和青少年都顯得有點無聊。橫越清潔平坦的大馬路,就是「Tierpark」的正門,它的面積是老柏林動物園的兩倍大,門票卻還比較便宜(全票,Tierpark:12歐,Zoo Berlin:13歐),乾淨簡約的公廁,附帶一位清掃大媽,會用英文對你說:「30分錢」,能找零。坐在企業認養的嶄新深綠色長椅上,這個距離下,邊看假山上午睡的北極熊,邊嚼著手中的三明治正好。感情融洽的一家四口人類,正牽家犬散步經過,「噗通」一聲,我四處張望尋找聲音來源,原來是大白熊跳進水中,開心地游著水。
《滾石》雜誌在千禧年之後突然茅塞頓開,Lou Reed《Berlin》這個曾被評為災難的作品,獲選為搖滾史上500大最佳專輯的第344名,經典獲得平反,但搖滾樂,以及我們看待搖滾樂之心,還像從前一樣嗎?青少年總覺得自己會永遠熱愛搖滾樂,就像在圍牆倒下的瞬間,人們都激昂地相信自己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刻。
僅存的柏林圍牆還有幾片,被藝術家畫上了各種充滿強烈政治批判意味的畫作,留了下來,叫作「East Side Gallery」,是當下柏林最重要的觀光景點,施普雷河水流過腳下、前方的奧伯鮑姆橋將曾經的東西邊界重新連結暢通。幾年以前,East Side Gallery讓出了40公尺左右的河景給那座歐洲電信巨頭O2新建的大型體育館,今年度,似乎還得讓位給一組計畫在此興建的高級公寓,幾幅藝術作品會被銷毀,但還沒人通知作畫的藝術家。

(攝影/何曼莊)
我知道沒有什麼事情會停止不變,當我坐在「Tierpark」附設餐廳的戶外餐桌前,隔著一絡淺水、一道遮住鐵籬的樹叢,看著駱駝成群陶醉在南風之中,他們的室友則是一大群長腿的紅鶴。關於「Tierpark」易主的消息已經確定,將此地全面重新規劃的風聲不斷,眼前的風景也許很快就要消逝,但我相信在「Tierpark」甫落成的東德時代,必定有許多人真心懷抱理想,誓將東德打造成美麗的家園,否則他們怎會率先建好一個這麼好的動物園呢,一直到了「Tierpark」開園後五年,東西柏林之間才築起了高牆。
柏林分裂期間,「Tierpark」的園長一直都是同一個科學家Heinrich Dathe,1990年1月6日,柏林圍牆倒下後第58天,這位納粹黨員、萬年園長與世長辭,冷戰結束了。
在那之後,轉眼22年已經過去,我心中的這份後冷戰時期憂鬱,也像東柏林一樣,逐漸變得透明而清新。
作者簡介
曾任《換日線》英語頻道Crossing.NYC 特約主筆。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以及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和散文集《有時跳舞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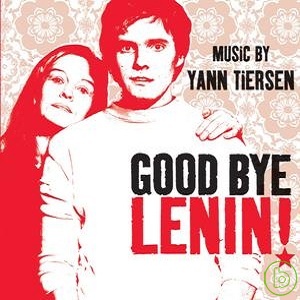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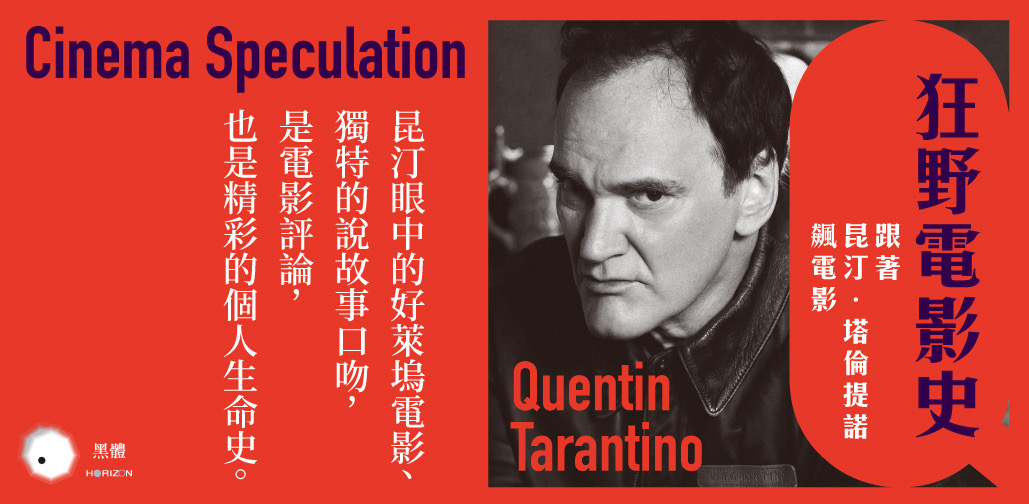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